醫者的體會
王浩威
慈悲。什麼是慈悲?
冬天到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省旅行。雖然是二月,但熱帶地區從不寒冷,幸虧有印度洋的海風,才勉強可以繼續這趟旅程。直到有一天,整日的陰鬱,沒落雨但也沒任何溫度稍減,最後一絲海風也甚至不見了,幾乎是悶熱到極點。我們待在克欽市舊港古堡改建的高級旅館,昔日大英帝國殖民地貿易商的家族住居。亞熱帶的住民如我們,竟然也承受不住大自然的溫度。「不曉得這些印度人民,是怎麼看我們這樣的旅客?」一位朋友,同樣是躲在旅館冷氣房裡,啜著啤酒,看著窗外擁擠騷動的渡口,忽然問起這話。
我們,同樣是來自亞洲的黃皮膚生物,卻站在百年以前白膚神祇矗立的位置上:不必習慣任何燠熱,也不必懷疑任何謙卑的服侍。在旅館外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民,沒有一個人嫌棄神明給予他們這樣的氣候,而我們卻有資格在昂貴的旅館裡悠哉的放慢腳步,甚至只是躺下來,只是翻翻書。
從書上,我第一次讀到耆那教的介紹。這個和佛教幾乎同時期崛起的宗教,慈悲的心情比佛教還激進。信徒們走在路上要小心,以免踩到任何生物;要面戴紗罩,以防吸進任何浮塵生物;要過濾所喝的飲水,避開水中微生物。只是,資料沒寫到,耆那教的信徒們要如何面對種姓制度呢?如何去面對成千上萬所謂的賤民呢?釋迦牟尼是反對了,但佛教也逐漸在這塊大陸上式微了。不知道現在依然少數但活躍的耆那教信徒,又如何去看待窗外的眾生為著生計搶搭擁擠不堪的渡輪?
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也許,神蹟故事裡充滿血腥和暴力的印度教因為更貼近這句話,而從佛教思想裡再度奪回這土地人民的信仰吧。
如果天地不仁,萬物淪為芻狗,人們又如何慈悲呢?
如果一個人承受著不可能治癒的、任何人都同意十分痛苦的狀況,真正的慈悲究竟是鼓勵他活下去,還是幫助他結束痛苦呢?
在我還擔任精神科住院醫師時,一位朋友年紀輕輕就罹患癌症了。他樂觀地接受放射治療和各種另類療法,樂觀地接受這些治療終於宣告無效的事實。直到有一天,逐漸衰弱的身體,不堪負擔任何心智活動了。身體的稍稍移動已不可能,最後連看一段影片也變得疲憊不堪。直到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在許多朋友的遺憾和哀悼中,悄悄的耳語在少數朋友之間傳開,原來有一位摯友協助他完成早早就自行安排好的死亡計畫。
這樣的過程,如果用現在的名詞,他是安排了自己的安樂死,而他的摯友則是協助死亡。
那是安樂死還很少被討論的時代,連生死學也才開始有傅偉勳教授的第一本書《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然而,知道這真實過程的朋友們,也不約而同地保持沈沉默,帶著莫名的罪惡感但又理直氣壯。
多年以後,《潛水鐘與蝴蝶》變成另一種傳奇,作者尚-多明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能在頸椎麻痺而全身癱瘓的情況下,努力享受著活下去的任何感覺,是很偉大的。只是,即使像他這樣,面對死亡最後一刻的真實感受,誰也沒法知道了。
如果天地讓萬物淪為芻狗是為了給眾生有所頓悟的機會,那麼,眾生是否有權利選擇不要頓悟呢?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似乎不是進入什麼寶瓶時代。比起上一世紀的九○年代,那個開始討論生死問題的時代,現在的我們好像更畏懼去思考任何陌生或藏在黑暗的思想了。特別是自殺問題日益增見的現今,防治自殺是應該好好思考的。但是,對防治自殺的迫切需要,似乎讓每個人都不敢談論:人是否有自殺的權利。愈是慌亂的時代,我們愈不敢去看真正的問題。
《我不是殺人犯》那位執行死亡計畫的醫生兼作者,才是真正的道德者。愈是眾人忌諱不談的,愈願意去面對。像書中文生?昂貝爾那樣的痛苦,也許有人真如佛陀般可以承受,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選擇結束。這時,身為醫生,如何去體會?
無國界醫師組織創辦人伯納?庫希內說得好:「一個人的所作所為,端視他所面臨的危機而定。」太多嚷嚷的聲音,乍看是仁慈的,其實是站在遙遠而安全的距離之外。
離開印度那一天,我們搭乘小巴士前往機場搭午夜飛機。路上擠滿入夜涼爽後出來逛街的民眾。我忽然想到自己的幸福:幸虧是出生在台灣。我想,如果我誕生為印度低賤的種姓,或是出生在更多年以前去過的肯亞奈洛比貧民窟,還有可能思索這一切問題嗎?也許,我是在想如何為了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如何踩到另一個人的肩上,甚至是傷害對方呢。
天地不仁。這樣的事實才是教人沮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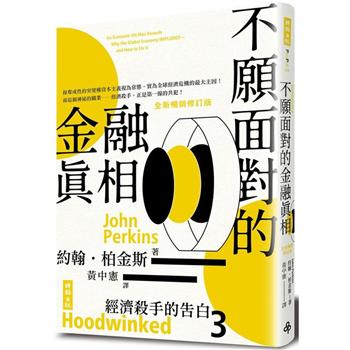











2003年9月26日蕭索瓦醫師以病患的意願及病患的最大利益考量為前提下,毅然地協助病患完成其最終的願望--死亡。然而此舉也將其事業與人生陷入到一大危機之中。 一個人需要有多麼大的愛心才能夠面對死亡這件事。從蕭索瓦醫師的所作所為就足以詮釋品格、操守與責任。醫生是以救人為職志,唯有體會死亡是生存的一部分的醫生,才能夠以慈悲人道的心以病人為重,而不是加諸一些無濟於事的醫療行為。 現今的醫療體系漸趨於”案例管理”、”病床管理”,以數值化分析資料來創造病床的最大利益。這種缺乏人文關懷的醫療照護,將使更多中下階級的大眾蒙受荼害。本書闡明了醫師用其一生對抗疾病與死亡,更應該尊重生命的本體,以人性的角度來對待每一個將其生命託付給醫師的病患。 本書完整的記載文生‧昂貝爾事件的始末。有那位醫師會像蕭索瓦醫師一樣自省反問--”明天早上,當我醒來時,我還敢張開眼睛看一看鏡中的自己,不會覺得眼前所見的那個人很噁心。”? 有那位醫師會像蕭索瓦醫師一樣在行醫多年後仍然記得希波克拉底誓詞? 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走到無以為繼的時候,我希望我的醫生也能夠擁有像蕭索瓦醫師的慈悲與勇氣。讓我在毫無痛苦而備感尊榮的情況下離去,而不是強行將我扣留在病床上,日復一日形銷骨毁的等死。 這本書我看了四次,其中三次是為了找尋一句讓我深深感動郤不復記憶的文字。 『太多嚷嚷的聲音,乍看是仁慈的,其實是站在遙遠而安全的距離之外。』 --- 摘自 王浩威先生的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