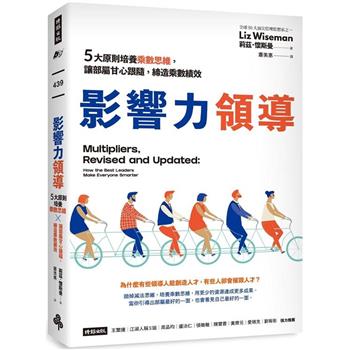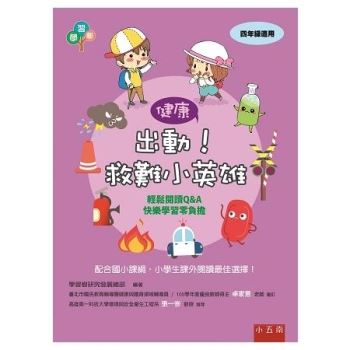顛覆死亡觀念,找到真我
想不到,我會在初來乍到印度的第三天,就被躺在街角沒有眼珠的屍體絆倒,還整個人就這樣趴在上面……
身邊的印度人熙來攘往,有人輕輕避開,也有妙齡的美麗女子拉起優雅紗麗的裙擺,毫不以為意的越過去。我雖驚訝意外,卻也奇妙的悟及──「這就是進入印度的洗禮」。
☆《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經新聞》《產經新聞》……日本15大報刊好評推薦!
☆日本圖書館協會選定圖書!
☆附精采特別訪談〈達賴喇嘛談死亡〉
印度,一個對生命極其嚴苛,卻又異常寬大的驚人國度
在印度遇見無數的「死」,使我更清楚遇見自己,也體悟到什麼是「生」。
活著的人真的能與死對話嗎?這本書漂亮的、而且或許是全世界最確實的回答了這個問題。書末所附與達賴喇嘛的對談,真箇是壓軸之作!
日本名作家,森村誠一
人人皆有一死。這件事我們心知肚明,但自從人類有歷史以來,不拘男女老少,人人皆為死愁煩,原因就在,大家都怯於真實的面對死亡。看了這本書,我終於有勇氣去接受這個事實了。
日本名演員,三國連太郎
對不輕言死亡的我來說,這本書的讀後感真是複雜難以描述。人活著,其實必須了悟我們乃是「必死之身」,因此而懂得尊愛生命。
書評家,神谷惠
當我們靠近一個悠久時間的長河時,或許會讓今天的生命更見光輝。透過印度,我們能學到的,就是「遇見自己」。
《每日新聞》(信濃版)
本書作者所寫的,不是抽象的死亡概念,而是「屍體」這個死亡的見證、死亡的殘渣。……其中和達賴喇嘛針對「自殺」所做的探討,更是意義深遠。
《產經新聞》(北海道某修道院長,高橋重幸)
在印度,死者不過是單純的物體,魂會經過輪迴轉世再生。……全書讓我深受感動,原來「死」就是「生」。
《朝日週刊》
作者透過親眼目睹無數的屍體,而達到「性命尚存的人,也只是在活出今天、活出明天罷了」的境界。這樣的過程充滿極大的張力。
《讀賣新聞》
本書受到各大傳播媒體的熱烈稱讚與推薦,也被選為日本圖書館協會選書。身為責任編輯,我認為這會是一本經歷漫長歲月也不致褪色的長銷書。
名編輯,芝田曉
火車即將從德里車站出發之前,有一群人急急忙忙跳上車。
他們各自帶了二到三個巨大的行李箱,和好幾個滿到眼看著就要破掉的麻袋。
最誇張的是他們四個人一起吆喝著搬進車廂裡的巨大木箱。
「喂!這個箱子,不能再想想辦法嗎?要不至少不要橫放,豎起來靠在牆上,用繩子綁好固定避免倒下來,不是比較妥當嗎?」
「真對不起,我們本來也想選一班空一點的火車的,可是不搭今天這班車運走的話,裡面就會壞掉。但要是把箱子豎起來,恐怕我父親會生氣……」
「你說裡面會壞掉……箱子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啊?」
男人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說:
「箱子裡面是我父親。」
「你父親在這箱子裡?」
「是啊!裡面是我已經過世的父親。」
之後的三十個小時,我度過了從未經歷的忐忑時光。
由德里出發的列車,越接近喜馬拉雅,車廂也左右搖晃得越厲害。
每次列車只要經過大轉彎便會劇烈晃動,讓我不由得提心吊膽,擔心腳下的木箱是不是就要打開了……
(摘自〈與棺財同行的火車之旅〉)
作者簡介:
山田真美(Yamada Mami)
日印藝術研究所語言中心所長(印度政府認可之法人機構)。一九六○年生於長野市,明治學院大學畢業後,赴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進行抹香鯨洄游研究。其後應印度文化交流廳之邀,進行印度神話之調查與研究,並自一九九六年起旅居新德里六年,為日本知名「印度達人」,對印度生活、文化的引介推廣極受歡迎,亦曾參與廣告、戲劇節目演出。主要著作有以古事記之謎為主題的小說《在黎明的夜晚》、暢銷英文學習書《豬太郎與貓熊的英文間諜大作戰》。翻譯著作有論及二次世界大戰祕史的《不苟活受囚虜之辱》等。關於本書,作者自述:「我想寫一本到最後都能為人留下希望的書。」
個人網站:http://www.yamadas.jp/mami/
章節試閱
行腳屍山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這一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近郊發生的事,我想我終此一生都不可能忘記。
散布在廣大棉花田的三百五十一具屍體,猶如一座屍山。焦黑的、支離破碎的,強烈的惡臭令人不禁掩鼻。才剛斷氣不久、尚有柔軟觸感的人體,就這樣橫躺在腳邊。不斷傳來的聲音,聲音,聲音,呼喊著親友的名字,在暗夜中狂泣。那簡直就是煉獄圖,也是我至今看過的所有景象中,最殘酷,也最血腥、最非人的光景。
當時,我為了研究印度神話而與家人住在新德里。這當然不是第一次到印度,自一九九○年首次踏入印度以來,我已經到過這個國家幾次,北從喜馬拉雅山,南至科摩林角(Comorin Cape),我走遍印度,幾乎可以說沒有我足跡未及之處。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就已正式開始在新德里生活,提到印度,我當然也有自信不會因為一點小事就大驚小怪。至少,在那天目睹超乎想像的慘狀之前是這樣。
那天,吃過晚飯正在休息時,看到跳進電視畫面的新聞。一開始,我不禁懷疑自己的耳朵。「兩架客機在空中正面衝撞,墜落於新德里人口密集地帶,估計死傷相當慘重。」飛機跟飛機正面衝撞!而且墜落在新德里?怎麼可能?我不禁喃喃自語。因為眼前我身處的地方,哪兒都不是,正是新德里的市中心。要是頭上掉下兩架飛機之類的巨物,就算有點距離,我也不可能毫無感覺。
若非出處是以新聞正確度備受好評的BBC(英國廣播公司),我搞不好還會一笑置之也說不定。半信半疑的轉台,除了BBC之外,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也以臨時新聞的方式大幅報導同樣的內容。當時在新德里,包含有線電視在內,已經有三十家以上的電視台可供收視,但播出這起意外事件的卻只有BBC和CNN兩家。其他電視台只是如常播著悠閒的印度電影,甚至看不到臨時新聞的流動字幕。
我馬上主動打電話給當地擔任新聞記者的友人詢問詳細的狀況。不多久,得知事情的始末是:剛由甘地國際機場起飛的阿拉伯航空,不知道那裡出了錯,竟跟正準備降落該機場的哈薩克航空在空中正面衝撞。另外也得知飛機墜落的地點似乎不是新德里人口密集的地方,而是位於由市內往西直走約六十五公里的查基達里村的棉花田。當時,我在日本的報紙和雜誌都各有一個連載的專欄。「這起意外,我非去親眼看看不可。」有了這樣的直覺,我便隨手抓了一些東西,決定親自前往查基達里村看看。
在未經開發的道路上搖晃約兩小時半,穿過據說偶有山賊出沒的荒野,好不容易才抵達的查基達里村瀰漫著一股異樣的氛圍。朦朧月光照耀的,看起來像是一片廣大的棉花田。可能是村裡還沒有接電,要不就是停電,周遭封鎖在一片闇夜當中,其中並充斥著令人作嘔的臭氣。我事先設想到意外現場禁止閒人進入的狀況,就隨身帶了前不久大使為我寫的介紹信和證明身分的證件,但一到現場才發現那裡不僅沒有圍起封條,連警察也沒來檢視,說穿了根本如入無人之境。
事實上,當場還有許多腰間纏著印度圍裙前來看熱鬧的男人,看起來也並不像特別有什麼事似的在周圍走來走去。這時候,我的腳碰到軟趴趴不明所以的物體。取出從家裡帶來的手電筒,急急往腳邊一照,瞬間,卻差點沒窒息。我穿著涼鞋的腳碰到的,柔軟而餘溫猶存的東西,無庸置疑,是人的手腕。仔細一看,視線所及,竟全都是支解的屍塊。
長如繩索狀的東西(後來想想,總覺得應該是大腸)、血肉模糊虛軟的肉片、支解的手腳,甚至眼珠似的東西,只要是人體有的器官,都慘不忍睹的凌亂落在不知道是不是下過雨導致整個泥濘不堪的棉花田四處。那真是第一次見到的「屍山」。看著眼前慘絕人寰的景象,我的反應略過驚嚇和噁心,只是呆掉了。或許在面對超越常理的慘狀時,人類反而一點都不會動搖。
這時有個剛好路過來看熱鬧的人,指著棉花田的反方向說:「你要不要看更多的屍體啊?要的話,就得去棉花田的另一端,那裡才有更多屍體,這邊的屍體,我們已經都大概整理過了。不過,今天還真是個大日子啊,竟然世界上所有的電視公司都聚集到查基達里村來了!那裡有英國的電視公司,還有美國的電視公司。美國的電視台還採訪我們唷!美國喔!」
男人很明顯的難掩興奮之情。在這個貧窮村落發生的事,對眼前的男人而言,感覺就跟婚禮或豐年祭之類的重大慶典沒什麼兩樣。而前來報導意外事件的記者,在他眼裡也與娛樂電影的攝影班差不多。其實,不能笑這個男人無知。印度的農民大多缺乏教養,天性單純而窮得可憐。他們大多數人不知真正的娛樂為何物,連在家裡擺台電視都不能如願,卻受到家族戒律的嚴密束縛,只能在不自由且絕望的情況下窮其一生。
很可能,就像眼前這個男人一樣。或許對日常生活毫無樂趣而且還捉襟見肘的男人而言,將空難墜機這麼悲慘的重大災難視為令人血脈賁張的娛樂,根本就是無可厚非的事。畢竟,即便是年屆中年,他的精神狀態還像個三歲小孩似的單純而無憂。「妳也是電視台的人嗎?」對於男人無邪的詢問,我簡短的回答: 「我是日本報社派來採訪的。」聽到我這麼說,男人隨即堆滿一臉笑意,有如幼兒般又蹦又跳的不斷喃喃說著:「日本報紙……日本報紙……」。
也許這之後他會逢人便像是展現英勇事蹟般不斷的吹噓他遇到「美國電視台」、「英國電視台」還有「日本報社」吧!就罹難者家屬而言有如人間煉獄的這一天,對這個男人來說,或許將成為讓他興奮到畢生難以忘懷的日子。我留意著不踩到屍體──儘管如此,屍塊早已經被那些看熱鬧的人們踩得稀巴爛,殘缺破損到跟地表無從分辨──但我還是向男人告訴我的「有更多屍體的那一邊」走去。
那個角落,在警察當局的指揮下,屍體已經陸續的清理。但那卻又是一幅令人不忍卒睹的景象。他們竟然用挖土機接二連三鏟起屍體,並且有如處理垃圾似的,粗暴的將屍體丟落到大卡車的載物台上。難道這就是印度人對死的看法……?毫不尊重死者的尊嚴。這,就是印度式的弔唁嗎?
在這一刻之前,我都還相信發生諸如此類的意外事件時,就「常理」而言,至少要用毛毯悉心包覆遺體,並安置在看不到的地方。儘管屍體數量龐大,但用挖土機鏟起屍體,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竟然就這麼咚咚咚的丟到大卡車上,怎麼想都是「反常」,不是嗎?然而再細細思量,便覺得或許所謂「普通的弔唁」或「反常的弔唁」一開始就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
試想:要這個在一九九六年都還無法順利使用電力的窮鄉僻壤準備包覆三百五十一具屍體的毛毯,是多麼不切實際的要求?別說是包覆屍體的毛毯,村民們恐怕連自己禦寒的毛毯都不敷使用。想當然爾,在意外發生一小時過後才終於抵達現場的警察或消防人員,根本不可能準備毛毯!一言以蔽之,這裡一開始就是什麼都匱乏的。終於,罹難者的家屬或朋友接二連三來到現場。悲傷至極的吶喊與痛哭,迴盪在生靈塗炭的大地。
發生意外的飛機都是隸屬於中東國家的航空公司,因此罹難者也多是回教徒。面對撕裂、焦黑潰爛到連原形都無從辨識的屍山,不知道家屬的悲痛與嘆息有多沉重。我會這麼說是因為,與猶太教或基督教相仿,對回教徒而言「遺體」本身就很神聖而寶貴,有燒傷或缺損,就表示遭遇重大的不幸。這就是為什麼自古以來回教不採火葬而使用土葬的原因。
經過徹夜採訪和長時間車馬勞頓,我頭昏腦脹的在翌日太陽已然高掛的時間才返回新德里的住處。攤開送來的報紙,驚見報上「不該出現的內容」,我不由得再次懷疑我的眼睛。不可思議的,報紙上竟大幅報導並刊登散落在查基達里村的屍體照片。而且刊登照片的還不只一家報社。那一天,我所翻過堪稱為報紙的報紙,全都刊載了怵目驚心的屍體照片。
幾天後發行的雜誌,甚至不僅誇張的用長達好幾頁的篇幅刊載這起意外事故罹難者的彩色照片,猶有甚者,還親切的在已經確認身分的屍體旁,附註全名和檔案資料。更嚴重的是,竟然有週刊將頭被扯斷、腹部腸子幾乎全部露出體外的女童屍體,與可能是女童隨身帶著的洋娃娃並排的照片拿來當作封面。試想,衝擊性這麼大的照片就這樣擺在印度全國的書店、報攤以及車站商店,供人們實際取閱購買,甚或帶到家裡客廳或臥房翻閱,會是什麼情景?
諸如此類的報導和照片有好一段時間獨占了整個城市的話題,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既沒有人認為刊登照片是對罹難者的褻瀆或是對人權的侵犯,更不曾聽聞要求雜誌停止出版的聲音,甚至連這類問題的提出或討論,也完全沒有。最令我吃驚的是:購買這些雜誌,並一張張翻閱罹難者照片、拿來當話題討論的,既不是變態也不是異類,而全是過著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城裡自詡為「評論家」者,不斷的針對意外的原因交換意見。從「可能是機場電腦系統有根本性缺陷」等煞有其事的見解,到「似乎是哈薩克航空的駕駛員英文有問題」、「誤將表示飛機高度的公尺當成英尺」、「原本當作貨機的哈薩克航空飛機在既定搭乘人數的十一人之外多載了二十四個人,令人費解」,甚至還有「據說哈薩克航空載了大量的紙鈔」等,彷彿目擊現場似的謠言四處亂飛。
另一個謠言則是說,在飛機墜落之後,原本有幾個罹難者存活下來,只不過聚集而來看熱鬧的人,不僅沒有對瀕死的罹難者伸出援手,反而從他們的口袋中取出錢包,或將罹難者身上所有的貴金屬或財物搜刮一空,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斷氣。真假無從判定,但是這個傳言馬上傳遍大街小巷。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人在聽到這個傳言之後憤而反駁:「印度人不會做這麼殘忍的事!」我的朋友竟然都一派正經的說:「是啊!這種事當然有可能。」
後來我才知道,在發生空難或大地震等大型災難之後,事故現場附近或路過的人聚集偷取罹難者(屍體或傷者)身上的貴重物品的案例,在印度一點都不足為奇。舉死傷慘重的印度航空墜機事件來說,由新加坡起飛的班機墜毀在孟買附近的竹湖海灘(Juhu Beach)時,機上空服員之一的羅莎琳在半生半死的狀態下活了下來。雖然傷勢嚴重,但她的意識卻很清楚。不久之後她證實說:「意外發生之後,不知從哪湧來了大批的人潮,看起來雖然貧窮卻不兇惡,感覺就像是很平常的村民。但這些人不僅沒有救我,反而將我身上的首飾或值錢的東西拿得一個都不剩。」
據說經過九死一生幸運活了下來的羅莎琳,事後依然在同一家航空公司服務很長的一段時間,但就她的同事而言,這種狀況(從罹難的屍體或傷者身上竊取貴重物品的野蠻行為),「在印度其實很常見」。看著將這一切講得理所當然的她們,我不禁茫茫然不知所以。印度,以佛陀開示不殺生戒和甘地非暴力主義的慈悲之國而聞名。但在同一個印度,卻發生從瀕死的人們身上盜取首飾錢財,或用挖土機處置屍體猶如處理垃圾般不近人情的事實。
到底該怎麼解釋這些矛盾?為了理解這個國家,未來是不是還要跨越好幾座屍山才行?這個疑問突然在我心中反覆出現。而這個預感也巧妙命中,讓我在那之後走遍印度各個角落,並幾近厭煩的跟眾多屍體結下不解之緣。
行腳屍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二。這一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近郊發生的事,我想我終此一生都不可能忘記。散布在廣大棉花田的三百五十一具屍體,猶如一座屍山。焦黑的、支離破碎的,強烈的惡臭令人不禁掩鼻。才剛斷氣不久、尚有柔軟觸感的人體,就這樣橫躺在腳邊。不斷傳來的聲音,聲音,聲音,呼喊著親友的名字,在暗夜中狂泣。那簡直就是煉獄圖,也是我至今看過的所有景象中,最殘酷,也最血腥、最非人的光景。當時,我為了研究印度神話而與家人住在新德里。這當然不是第一次到印度,自一九九○年首次踏入印度以來,我已經到過這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