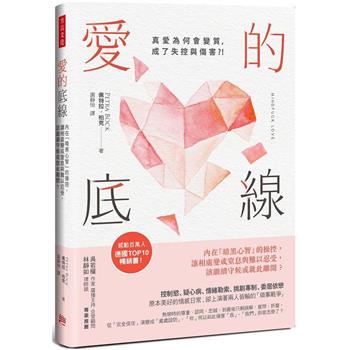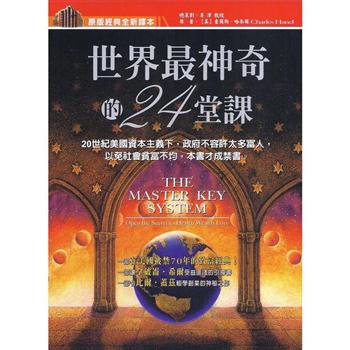Chapter 3 我獨有的咖啡和咖啡館
義大利人對咖啡的堅持
靠近羅馬的萬神殿,有個鹿角廣場(Piazza Sant’ Eustchio)。偶然路過這個三角形小廣場的觀光客,對於眼前所見,一定會感到疑惑。
這個廣場的名稱,來自於廣場一角的聖鹿角教堂。傳說,這個教堂是為了一個被關在火燒的青銅牛裡殉教的聖人所建。而廣場也泛著不遜於這個傳說的異樣熱氣。在同名的「鹿角咖啡館」(Sant' Eustachio)裡,人潮熙熙攘攘,我第一次經過時,也大吃一驚,不免詢問同行的羅馬友人。
「啊,這是羅馬很受歡迎的咖啡館喔。他們的招牌咖啡,是上頭有著生奶油的康寶藍(Café con panna),你也來一杯吧。」
我還沒答應,就被擠入人潮中。雖然店裡不大,但光是擠到收銀台就是個問題。有個高舉兩杯濃縮咖啡的紳士,一邊高喊「安娜瑪麗亞,我在這,在這啊!」邊以圓滾肚子擠開群聚聊天的學生;然後再從啜飲著咖啡的三位紳士面前走過,這才總算走進收銀台前呈放射狀排列的群眾裡。
這個國家本來就沒有排隊的習慣,所以當食物擺在面前時,就得趕快搶,如果膽怯,可能什麼也吃不到。所以,我也只得厚著臉皮擠到收銀台前,然後大叫「康寶藍咖啡」。之後又是一陣推擠,就擠到了義大利濃縮咖啡機前。我對著煮咖啡的三位男士高舉收據,拚命請他們給我咖啡。
像是配合牆上中美洲異國風味的浮雕,男士們的動作像搖著沙鈴般,將咖啡一杯接一杯倒入杯裡。這時,朋友在我耳邊低聲說:
「你應該知道,在義大利,義式咖啡館的濃縮咖啡價格是法律公訂的。若內用還要再加錢,而在櫃台站著喝的話,濃縮咖啡一杯要一千二百里拉(約新台幣十八點五元),卡布奇諾一千五百里拉(約新台幣二十三元)。從阿爾卑斯地方到西西里島,不論哪裡都是一樣的。如果不這麼做,就不可能使用藍山這樣高級的咖啡豆。大公司的商品和小店堅持的咖啡豆雖各有不同,但勝負就在於烘焙的方法和泡法。所以,你看,裡面正烘焙著自家的豆。且煮法可是企業機密,不會讓客人看的。」
就在談話中,生奶油堆得高高的康寶藍咖啡好了,我將它抱在胸前,往門口走去,混入大街上正站著聊天的客人中。
康寶藍是這個店的人氣商品,味道非常甜,感覺可以取代甜點。不過我認為,若是要享受咖啡風味,還是不要加生奶油比較好。
為什麼義大利人對飯後的咖啡那麼堅持呢?
幾天前,我和幾位神父在鄉下的小餐館吃午餐時,因為覺得再去其他地方很麻,便提議在餐館內喝咖啡。結果,一位修道院院長兩手往桌面一撐,站了起來,向靜悄悄的廚房內部、餐廳入口望去,然後像發現什麼重要機密般小小聲說:「不,先結帳,然後到附近的義大利咖啡館喝吧。我看過了,這邊好像沒有機器。」
如果是用家庭用的義式濃縮咖啡機器煮的咖啡,在自己家,不,在修道院隨時都可喝到。所以,怎麼都想喝那種會咻咻冒出蒸氣、飄散著挑逗人香味的機器所煮的咖啡。這些義大利人對這點可是很固執的。如果我是那機器的發明人,一定會喜極而泣吧!這機器煮出的濃縮咖啡,雖然只有黏在小杯咖啡杯底部這樣的量,但因為萃取了最美味的精華,所以香味四溢;雖然它有點苦,但據說喝了後,可讓飯後睡意從頭頂完全散去。
當我開始慢食生活時,總是會想到旅居義大利時,每天必定前往的義式咖啡館。它究竟是速食生活的朋友,還是慢食生活的夥伴?
說來,義式咖啡館(Italian bar)到底是什麼?
若要追溯起源,在龐貝城遺跡中,也可看到古羅馬人去餐飲店喝杯酒的情景。不過,同樣使用「bar」這個字,它和日本所稱的酒吧是不一樣的。與其說是蒐羅各種酒的地方,不如說是飄散著咖啡芳香的店。
十六世紀,土耳其人將咖啡傳入義大利。而最早期的咖啡館之一,是位在威尼斯聖馬可廣場(Pizza San Marco)的「佛羅倫」(Florian),誕生在十八世紀。但那時服務的對象是少數上流階級,具有強烈的沙龍性格,因此嚴格來說,是「咖啡館」,而不能算是現在所謂的「義式咖啡館」。至於現在滿街的義式咖啡館的經營形態,是源自一間食材店老闆的構想。
一八九八年,這位男士在自己的店,闢置可讓顧客站著喝咖啡的空間。當時咖啡是高級品,因為新奇,所以生意興隆。之後店主人為了吸引客人,便開始在櫃台擺上各式餅乾、橄欖、甜點麵包等。可惜的是,這家店好像不存在了,而這就是義式咖啡館初期的原貌。咖啡的大眾化也隨之一口氣蔓延到各處。
快速的濃縮咖啡
現在,早上的通勤時間或午餐後,城中的任何義式咖啡館都很擁擠。儘管不像鹿角咖啡館那麼誇張,但櫃台裡的店員,都猶如千手觀音般手腳俐落、很有氣勢地工作著。光是這令人眼花撩亂的動作,就不能說義大利人是懶惰鬼。而義式咖啡館的客人,也都拿著報紙,邊打招呼邊進入店裡,然後說「普通的濃縮咖啡」,服務人員便咻地倒上咖啡。客人舉起小杯子咕嚕喝乾,說聲「謝謝」,就又消失了。每天到義式咖啡館吃早餐的人差不多都如此,喊了聲「卡布奇諾」,點了卡士達奶油麵包,交給店員用紙巾打包後,就抱著它,不是看著天花板吃,就是和朋友邊吃邊聊,不到五分鐘就解決,然後離開。
這看起來,根本是速食。
速度不只展現在店員的動作和客人的吃法上,濃縮咖啡的起源,也和速度有關。濃縮咖啡的義大利文「Espresso」,原本就是從「快車」這個詞演變而來的。濃縮咖啡誕生於十九世紀,那時,它的宣傳海報上是這樣的畫面:衣領翻起的時髦紳士,手拿冒著煙、剛煮好的濃縮咖啡的小杯子,從快車上跳下來。雖然不必得用這麼危險的方式喝咖啡,但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喝才會好喝,這就是濃縮咖啡。
幾年前曾得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地中海樂園」(Mediterraneo)中,有段希臘離島的義大利駐兵拒絕土耳其咖啡的劇情。劇中,中尉解釋說,土耳其咖啡要在離火後,等咖啡粒子慢慢完全沉下才喝。結果,他保守的部下卻像小孩般鬧情緒地說:「這東西不是咖啡!所謂的咖啡要快速地倒進去,很快地喝光!」
快速倒進去,很快地喝光,儘管是嶄新的風味,卻將東方土耳其傳來的咖啡的緩慢步調,變成急性子的東西。就義大利的濃縮咖啡看來,義式咖啡館果然是速食生活的殿堂,然而為什麼被認為是慢食呢?
這麼想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認為義大利大部分的義式咖啡館,是站在慢食這邊的。雖然說,不可否認,義大利半島每天大量消費的咖啡豆,是壓榨非洲或中美洲人所得,但義式咖啡館仍然是慢食者的朋友。我認為,慢食性格的義式咖啡館,應該具備下列三個條件:
第一、店裡,有各式各樣的餐點。
第二、是人們聊天、交流的場所。
第三、在店裡工作的人,能發揮自己獨特的本性。
我獨有的咖啡和咖啡館
有天,一位住在佛羅倫斯郊外的朋友邀我共進午餐。在開車送我回城的途中,我們決定去喝杯飯後咖啡。
「我曾經和朋友說過,有天,我要寫一本有關義式咖啡館點餐方法的書。在義大利的義式咖啡館裡,光是點咖啡的方法就沒完沒了喔,少說也有兩百種!」在當地報社當記者的朋友說。
兩百種?未免誇張了吧!當他露出義大利人得意時的誇張表情,我偷偷地苦笑著。他將外套脫下放在櫃台邊,然後對著認識的店員說了像是咒文般的句子:「Caffe‧Normale‧Doppio、Pelog、Con‧Acqua‧Corretto‧Anapte」。
他的意思是:「濃縮咖啡要雙倍的,並請另外給我水。」也就是說,他想要夠份量的濃縮咖啡,不想喝像美式咖啡一樣淡而無味的咖啡。但因為想要圓潤的口感,所以想加熱水,但如果太稀又很麻煩,所以水的份量想自己決定。也因為這樣,點杯咖啡就要說這麼一長串。原來如此,我深感佩服。看來,朋友不說一百種,而是說兩百種,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根據的。
不論去什麼樣的義式咖啡館,義大利人這種對「我獨有的咖啡」的態度,讓詩人安森伯格(Hance Magnus Enzensberger)在裡頭嗅到人生哲學。他在著作《歐洲半島》中提到:
「所有的義大利人,就算是窮困潦倒,也都擁有某種特權。冷靜的觀察者會認為,構成這個特權的,多半是他們的空想;但我主觀上認為,這個特權,是讓義大利人之所以是義大利人的天生智慧。……在安德里亞(Andria)市的某間義式咖啡館,有五位長途卡車司機各自點咖啡。第一位點了純麥咖啡(malt straight),第二位點了瑪琪朵(Macchiato),第三位點卡瑞托(Corretto),第四位想要卡布奇諾,而最後一位,則得意地大聲喊著:『雙倍濃縮咖啡,特別加入牛奶』。」
純麥咖啡是非常濃的咖啡。瑪琪朵是從義大利文「斑點」(macchia)一詞而來,也就是在濃縮咖啡裡加入少許牛奶;而卡瑞托則是加入大量熱牛奶。至於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卡布奇諾,則是用蒸氣加熱並加入奶泡。
光是在咖啡裡加牛奶,就有很多方式,此外還有咖啡、牛奶各半的拿鐵咖啡。在克難旅行時,我每天的早餐都是牛奶為主,再加入一些咖啡,也就是拿鐵瑪琪朵。牛奶依季節不同,可以用熱牛奶或冰牛奶,依個人喜歡。但有一次,我被某位紳士糾正說,至少該點個卡布奇諾什麼的。為什麼他這麼多事,那是因為拿鐵瑪琪雅朵通常不是咖啡店的重點,很多店再會將咖啡壺裡倒剩的咖啡收集起來,再加入牛奶,並不是那麼堅持濃縮咖啡的味道。
把咖啡的可能性拓展到極致的,是義式咖啡館裡的酒。天氣一冷,就常可看到有人點在咖啡中加入格拉巴酒(grappa)的格拉巴酒咖啡,又或是在咖啡中加入白蘭地、萊姆酒等,客人可以自己決定各種組合。而用製作雞尾酒的雪克杯所做的霜凍咖啡,或是夏天限定的雪克羅多咖啡(caffe shakerato),最近也很受歡迎。
嗯,如此一來,就算是門外漢的我,也知道五十幾種義式咖啡的變化,再過十年或許就能知道兩百多種了,不過先在此打住。
在義式咖啡館,因為時間不同,客人所點的咖啡也會不同。早晨,通勤的上班族或學生,多是以濃縮咖啡或卡布奇諾,搭配點心麵包當早餐。中午時,小孩子會來挑選冰淇淋,獨居老人在店裡拿著電視遙控器打發時間。而在午餐後,便盡是想喝濃縮咖啡的人。傍晚時,同一批客人又來喝金巴利(Campari)或是氣泡酒做為飯前酒。至於鄉下的義式咖啡館,則被打牌的老人所占據,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地方,他們才能點杯酒就坐很久。
就像這樣,在義式咖啡館裡的點餐,伴隨無限樂趣。不論客人點的咖啡怎麼囉嗦,店裡的人也絕不會皺一下眉頭,這就是義式咖啡館。
這和看著照片、手一指就能點餐的速食店,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在速食店說:「大漢堡,不要番茄醬,對了,請多給我點醃黃瓜。」便會得到鄭重其事的拒絕:「我們不接受這樣的點餐。」或者是被領時薪的打工小姐投以冷漠的眼光。
速食和義式咖啡館的第二個不同點,是對話。在高度制度化的連鎖店,可能連談話的餘地都沒有。很多人一進去,不必說話就能點餐、付錢、吃東西,然後離開店家。只要懂得規則,之後完全不受干涉,想做什麼都可以,這的確可說是速食唯一的優點。但是在義大利的義式咖啡館裡,客人是以聊天的方式點餐,因此,很多義式咖啡館的老闆,都是從八卦到股票投資都知道的情報通。實際上,在義大利一些較封閉的村子裡,若想打探什麼祕密,最好的管道就是去找祭司、村長,或是義式咖啡館的老闆。
優秀的義式咖啡館店員,對於昨晚憲兵隊逮捕的罪犯名單、玩牌老人們的嘟噥、推著娃娃車的媽媽抱怨照顧小孩的壓力,以及鄰近的八卦等,他們都全盤傾聽,並在傾聽時,一邊應和,一邊制式地倒入濃縮咖啡,享受各式各樣的對話方式。
再者是,義式咖啡館有各式各樣的面貌。就算是乍看之下到處可見、感覺上都差不多的鄉間義式咖啡館,仔細觀察後,也能發現店主人冷淡外表下隱藏的個人風格。
在有很多虔誠基督徒的南部義式咖啡館裡,比奧(Pio)神父的照片得到壓倒性的支持。據說這位手部出現聖痕、普利亞州(Puglia)出身的神父,因為治療了無數的病人,成為宗教界的偶像。另外,在綠意盎然田園地帶的義式咖啡館的老闆中,單車迷的比率相當驚人。他們年輕時的英姿和獎盃,與布滿塵埃的巧克力箱子一起放在展示櫃裡。
另外,也有一些咖啡館老闆會張揚自己對足球的狂熱,在牆上貼滿喜愛隊伍的旗子、選手的海報等,也不在乎其他球隊的球迷看了可能不高興。反正如果咖啡還不錯的話,平常時候,其他隊的球迷還是會光顧。不過如果是在義大利盃球賽時,敵隊球迷當然就離得遠遠的。
城市裡有些義式咖啡館,過去曾有畫家或詩人常來店裡坐,這種店的主人通常很隨興,就算你是一個人泡在店裡讀書,他也不在意。另外,也有在店裡貼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海報打上聚光燈,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咖啡館。像這樣,這些義式咖啡館表現出主人的強烈個性,客人也會自己尋找適合的咖啡館,因此,任何人都能擁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咖啡館」。
這樣的慢式義式咖啡館,就像無數各自閃著獨特光芒的星星,給予在這個國家生活中的每個人活力。
今天輪到樵夫看店
當我正對義式咖啡館的本質感到興趣時,有一天,邂逅了一家店。
那時正值盛暑,我和朋友前往托斯卡尼的亞平寧山脈健行。我們將車停在山腳,正想在登山前喝點礦泉水補充水分,且來杯濃縮咖啡時,路旁剛好就有一家不起眼的義式咖啡館。
走入咖啡館裡,眼前實在沒有值得大書特書之處。展示櫃中既無自製的別緻麵包,且放在棚架上的洋芋片或點心,袋子上頭都覆蓋著薄薄的灰塵;店內擺著四張木桌。我想,下午時,應該會有靠年金生活的老人來店裡玩撲克牌,直到打烊吧。這就是那種看似沒有幹勁的典型鄉村義式咖啡館。至少表面上給人這樣的感覺。
我點了水和濃縮咖啡,又加點檸檬冰沙。當邊喝邊環視店內時,發現老闆身後牆上的月曆,寫了密密麻麻的字。靠近一看,原來是人名:一號馬迪奧,二號法蘭西斯,三號安娜瑪莉亞,四號但丁,五號朱塞佩……。
一開始,我以為老闆是位虔誠的基督徒,而月曆上寫的名字,是每天的守護聖人,不過,連但丁的名字都有,似乎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囉。那這些名字代表什麼意義呢?店主人看來似乎不是會閒聊的人,而我也唯恐問到什麼不好說的祕密。但如果就這樣空手而回,實在讓人不甘心,所以決定單刀直入問清楚。
捲髮混著點白髮、體格健壯的店主人,露出非常不可思議的表情嘀咕著:「這裡是『circolo』。」
「circolo?」這是義大利語中「社團」、「俱樂部」的意思,但我更加困惑了。
「不知道『社團』啊……那也沒辦法。」言下之意,似乎這是一般常識,就連小孩子也知道吧。
「『社團』是上個世紀中葉興起的組織。那時,正是義大利受到法國革命的影響,傳奇人物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致力於統一國家的時候。這是以老百姓生活的互助為目的而建、這個國家最早的互助組織……」店主人認真謹慎地解釋著「社團」的來由。
組織裡的成員,在工作結束或週日時,都會來到「社團」。而在急速工業化下,更成為從鄉下到都市工作的人休憩和交流的重要地方。因為人們對這個場所的需求,二十世紀初,以托斯卡尼、埃米利亞-羅曼尼亞州中心,誕生了很多的「社團」。
不過,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時代,所有集會活動都被禁止,相關組織受到迫害。戰後,成員修復遭到轟炸,以及被法西斯主義者或美軍破壞的社團,開始新的活動。此後,這些場所不單是人們相互援助的據點,也成為反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主義左派人士常駐留的場所。戰後大選中,基督教民主黨在與共產黨激烈爭戰的結果下,總算獲得勝利。不過,差點變成共產國家的義大利政府,因此強烈地反對共產黨,而「社團」由於是共產主義者經常集會的場所,也備感壓力。在如此艱辛的狀況下,成員在一九五七年於佛羅倫斯成立了ARCI組織。
我大吃一驚。ARCI不就是慢食協會的母體嗎?
雖然完全是偶然,但是這個稱作「社團」的義式咖啡館和慢食協會,源頭竟然是相同的。這有什麼象徵意義嗎?
ARCI設立後,「社團」因為成為反對越戰等的學生運動的根據地而興盛,會員大幅增加。在一九七○年代,它在全國的據點有三千處以上,會員達到六十萬名。但是七○年代中葉,當義大利全國國民有六成是左翼份子之後,原本強烈的政治色彩也隨之淡化,戲劇、音樂、電影等文化活動成為ARCI的主軸。並在一九八七年,改名為「新ARCI」,除了文化活動之外,也致力於人種或性差別的新問題。
另一方面,ARCI裡也誕生兩個團體。一個是雷加‧安比恩提的環保團體,這個團體裡出了羅馬市長和很多政治家,現在也繼續成長中。另一個則是由卡羅所創立的「ARCI-GOLA」慢食協會。
值得一提的是,ARCI在一九九七年擁有全國一百二十萬名會員,成為義大利最大的文化社團。
但是儘管店主人如此仔細解釋,但是月曆上一串名字的謎還是未解開,當我這麼嘀咕時,他不斷用手示意要我不要那麼急,最後總算進入了主題。
「總而言之,這是值班表。村子裡,是需要義式咖啡館的。」
村裡的義式咖啡館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它,義大利的早上就不會天亮,即使沒有雜貨店或麵包店,就是不能沒有義式咖啡館,所以必須建個讓村人每天至少能見一次面的地方。但是,在人口稀少的這個村莊,即使可以經營義式咖啡館,使用的人也很少,也不會有什麼觀光客。所以村人就各自貢獻一點心力,ARCI也做為它的後援。但是,因為欠缺雇用工作者的資金,村人就自己輪班,輪流當店長。而這個地方是所謂的「社團」,所以會員能享有折扣,而一般人也可以當它是普通義式咖啡館般使用。
「我們平均一個月輪班一次,今天十四號,是馬克當班,也就是我。」
我問今天的店主人馬克,平時從事什麼工作,他說是林業。他這一說,我才注意到他脖子處都曬得通紅。原來,這位用熟練手藝倒濃縮咖啡、身穿黑色背心的馬克大叔是位樵夫……在義大利的義式咖啡館裡,真是充滿驚奇。
而透過馬克對「社團」的解釋,可以知道,義大利的義式咖啡館在本質上,是聚會場所。
對義大利人來說,義式咖啡館是不可欠缺的,將它看做是義大利生活的縮影,一點也不為過。這是個被咖啡香包圍,能治療孤獨、消解不安的聚會場所。
里茲教授曾提問:慢食協會到底能否成為「世界麥當勞化」的阻力?我想,無論怎麼努力,要讓速食消失無蹤是不可能的。不過,對我而言,如果有個地方消失了,我會覺得很可惜,那就是義大利的義式咖啡館。
慢食協會的會員、社會學者蒙大拿里曾說過:「在慢食的餐桌上,不盡然都是讓人心情愉快的,反之,速食也不盡然是不愉快、劣質的。」
因此,他思索著,有沒有什麼其他可做為判斷標準的準則,而提出了「草率食物」(careless food)這個詞。「這是關乎有沒有注意、用心的問題。像是素材的選擇、品味食物、注意吃法、關心食物所傳達的訊息,以及與誰分享食物……,專注這一切,才會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環境……如果不選擇、不評論、不想理解,對食物毫不注意,不假思索就丟進嘴裡,這才是真正的速食。」
義大利多數的義式咖啡館,果然是允許進入慢食的殿堂。
(摘自本書第三章)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慢食,在義大利的圖書 |
 |
慢食,在義大利 作者:島村菜津 / 譯者:陳美枝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5 |
二手中文書 |
$ 298 |
社會人文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飲食烹調 |
$ 31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慢食,在義大利
慢食不是慢慢吃;慢食不是速食的相反詞,慢食,是一種生活態度。
在創造了慢食的義大利--
每一個人都能在咖啡館裡,找到自己專屬的咖啡,因為他們瞭解,在食物的多樣化裡,孕育了個人的獨特性。
有大學教授每天開三十分鐘的車回家,和家人共享午餐, 因為他們深知,餐桌,不只是填飽肚子的地方,還是維繫情感的聖殿。
有一群人在森林中尋找香草、花長時間製作乳酪,因為他們體會到,培育美味必須投下的時間,也能讓人在其中得到力量。
有釀酒人放棄大量生產,合力鑽研每個細節,因為他們相信,在大自然的恩賜中,藏有每個地方的自豪。
拜訪過這些製作慢食、實踐慢食生活的人,你發現的,將不只是「慢食」的真正精神,還有,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作者簡介:
島村菜津 著
1963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縣。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藝術學科,專攻義大利美術史;之後,赴義大利留學。現為自由作家,領域包括飲食、旅行、美術、電影等。著作有:《慢食的日本》(スローフードな日本!) 、《佛羅倫斯連續殺人》(フィレンツェ連続殺人,共著)、《與驅邪法師的對話》(エクソシストとの対話,獲小學館非小說類大賞優秀賞)、《義大利的魔力》(イアリアの魔力)等,並以日本東京慢食協會會員的身分,持續推廣慢食運動。
章節試閱
Chapter 3 我獨有的咖啡和咖啡館
義大利人對咖啡的堅持
靠近羅馬的萬神殿,有個鹿角廣場(Piazza Sant’ Eustchio)。偶然路過這個三角形小廣場的觀光客,對於眼前所見,一定會感到疑惑。
這個廣場的名稱,來自於廣場一角的聖鹿角教堂。傳說,這個教堂是為了一個被關在火燒的青銅牛裡殉教的聖人所建。而廣場也泛著不遜於這個傳說的異樣熱氣。在同名的「鹿角咖啡館」(Sant' Eustachio)裡,人潮熙熙攘攘,我第一次經過時,也大吃一驚,不免詢問同行的羅馬友人。
「啊,這是羅馬很受歡迎的咖啡館喔。他們的招牌咖啡,是上頭有著生奶油...
義大利人對咖啡的堅持
靠近羅馬的萬神殿,有個鹿角廣場(Piazza Sant’ Eustchio)。偶然路過這個三角形小廣場的觀光客,對於眼前所見,一定會感到疑惑。
這個廣場的名稱,來自於廣場一角的聖鹿角教堂。傳說,這個教堂是為了一個被關在火燒的青銅牛裡殉教的聖人所建。而廣場也泛著不遜於這個傳說的異樣熱氣。在同名的「鹿角咖啡館」(Sant' Eustachio)裡,人潮熙熙攘攘,我第一次經過時,也大吃一驚,不免詢問同行的羅馬友人。
「啊,這是羅馬很受歡迎的咖啡館喔。他們的招牌咖啡,是上頭有著生奶油...
»看全部
目錄
源起: 另一種生活的可能1. 慢食不只是慢慢吃2. 堅持人與人的親密接觸3. 我獨有的咖啡和咖啡館4. 讓村落復甦的葡萄酒5. 療癒的森林6. 都一樣,不是很乏味嗎?7. 回歸鳥鳴果香的生活8. 小學教室的味覺遊戲9.在自己熱愛的土地上挖掘寶藏10.美食界的諾亞方舟終章 偉大長老的嘆息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島村菜津 譯者: 陳美枝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30 ISBN/ISSN:9789862161555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39頁
- 類別: 中文書> 生活風格> 飲食烹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