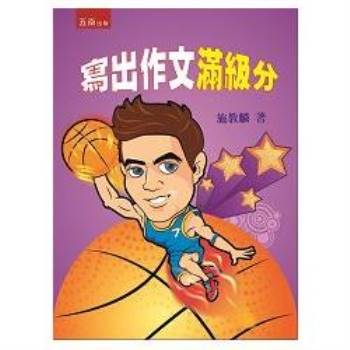烤爐邊的故事
我唯一的拿手專技是烘焙西式糕點。自嘆一生不善烹飪,做起飯來張張皇皇,雖然有時尚能差強人意。可事倍功半,好不吃力。當年為了面臨廚房的重擔,急著要應付吃飯的問題,大凡本地中西名師傅開班,我就趨前求教。豈料所學菜譜,都只有一面之雅,試做過一次,就恝然置之。缺乏興趣乎?沒有稟賦乎?自己百思不解,為何對烹飪之技如此不出息。我不是不覺察到與生俱來有一雙特別笨拙的手。學了五年鋼琴,手指頭在琴鍵上動彈,既無力又不伶俐。寫起書法,東歪西倒,自憐亦復自笑。小學時代的勞作才把我折騰得厲害,做紙花、塑黏土、剪色紙……都要同學助我一臂才能過關。長大後,更視女紅為苦事,隨著嫁妝來的一架縫紉機,冷藏了幾近廿年,常有內疚之感。十個手指天生就那麼不靈活,舉凡要動手去摸,去捏,去揉的技藝,全非我所長。十年來能常在廚房裡篩麵粉,打雞蛋,樂於烘焙西點蛋糕,自視為奇蹟。 烹調食物與烘焙蛋糕的方式全然廻異。前者不必斤斤計量,愈老練者,原料的份量愈靠直覺,幾根蔥,一撮鹽,一把米粉……後者卻要有很準確的衡量,一杯麵粉,一匙醱粉,不但是以平面為準,且要篩散過的;四個雞蛋,大小要分明;兩匙牛油、固體或液體要說明……粗心大意是我個性中的瑕疵;奇怪的是在烘焙蛋糕時卻很耐性子,絲毫不討厭樣樣要細心計量的程序,反而覺得那種拘謹的做法是約束我放肆的個性的好機會。 特別的蛋糕,蛋黃與蛋白,都是分開打的。烤爐出來的蛋糕,成敗全在蛋白之打得是否夠濃硬。所以在把蛋白與蛋黃分開時,我總是全神貫注,小心翼翼的不要使蛋白滲與半滴蛋黃,否則就會大勢已去,蛋白再打也不會濃硬起來,到時候蛋糕必硬如石頭。我常常取笑自己,讀書寫字若亦持有分開蛋白與蛋黃時那種「全神貫注,小心翼翼」的態度,今天必能出人頭地! 西班牙甜食中有純蛋白製成的如「佳綸尼糕」(canonigo),原來的意思是天主教修道院中之教士,此道雪白高潔的蛋糕乃被喻為教士;西班牙民族是篤誠虔敬的天主教徒,甜品裡竟亦含有宗教味道;亦有純蛋黃製成的如「天肉」(tocino del cielo)。兩者均要外潑甜汁,才能食出名堂來;否則就味同嚼蠟,單調乏味。我並不太欣賞這種「孤男寡女」的甜食。蛋白與蛋黃本是形影不離的,食譜裡只是要它們分開打,最終仍要攪拌在一起,才算是天作之合。 歐美甜品,多款多樣,有蛋糕,派(pie),蛋捲(crepe),「慕斯」(mousse,口感類似布丁),泡芙(puff),含有酵母的甜糕(yeast cake)……,我學了不少,惟對蛋糕情有獨鍾。西式糕餅店裡所陳列的成品,原料與做法,我常是一目瞭然。濃脂矯飾的蛋糕不一定就是上乘的蛋糕,那要看其原料與配料。外塗「梅郎」(merengue,蛋白與糖混成的糖衣),花枝招展的生日糕是最凡俗的蛋糕。蛋糕本身所施用的麵粉有兩種:普通麵粉與蛋糕麵粉。細膩的蛋糕一般都是用蛋糕麵粉做成的。糕質之優劣更與所採用的奶油的品質切切相關。配料中,我最喜歡菓子。較常使用的菓子有蘋果、芒果、香蕉、草莓、罐頭桃子、罐頭櫻桃、乾梅子、乾棗子……等等。其中以蘋果最常用,其食譜花樣繽紛,我學過的就有六、七種,包括數種歐、美不同的蘋果糕、蘋果派。蛋糕之「貴」在於所塗用的乳脂。乳脂有若干種,以鮮乳脂(fresh cream)最棒,亦最昂貴,敷有鮮乳脂的菓子蛋糕是西式糕點中的佼佼者。 麵粉是蛋糕的命脈,其份量之多寡決定蛋糕本身的性質。美國蛋糕慣用較多麵粉,兩杯至三杯,糕質因而緊密不鬆;歐洲蛋糕通常只用一杯麵粉,所以糕質既鬆且軟。我學過的「匈牙利糕」,只用兩大匙麵粉,味道與眾不同,是我家老大特別喜歡的蛋糕。 孩子們十歲左右是我最勤於烘焙糕點的時期,因為她們下午四點放學回家後,每個禮拜要趕赴兩次的芭蕾舞課,以及兩次的鋼琴課。每天早上,我要在廚房裡摸索個不停,預備孩子們下午的點心。學校下課歸途中,姊妹倆在車上老愛猜測媽媽當天烘焙的是甚麼糕、甚麼派。每天吃不同的糕點是她們一天內固定的歡樂。記得當時也正是我橋牌打得最熾熱的時期,邀請朋友來家裡打橋牌,時款以親自做的甜點,橋牌桌上常得到許多謬讚。偶爾遇到知音,那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曾經異想天開,想開設一家歐式的咖啡館,地方小巧,裝璜高雅,且播有柔情的音樂,而主題乃在於每天供給不同五顏六色的糕點,客人一定有走上門的雅興。那要捨棄其他一切活動,鎮日窮忙於烤爐邊,在麵粉、雞蛋與奶油之間打轉,緊張得不知何去何從,是為了貪博一百八十元的盈利,抑或是為了滿足以雕蟲小技炫耀於世的虛榮心?兩者吾皆不與焉!夢幻中的小咖啡館乃像肥皂泡沫破滅在空中。 一九八四年 註: 最近老二參加學校舉行的糕點比賽,我幫她做了一個用橙汁做的派,上面飾有一團一團的鮮乳脂,橙色配白色,清鮮奪人,單是外型就夠吸引力,結果被錄取第一名,因而引起我撰寫這篇拙作的靈感。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紅塵中的美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24 |
散文 |
$ 240 |
中文書 |
$ 25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82 |
現代散文 |
$ 288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2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紅塵中的美絕
研究中國古陶瓷乃莊良有生活的主軸,她也酷愛文藝,本書是她的散文集。作者除了描繪貼切的親情、友情和紛擾的紅塵事態外,並涉及題材不凡的中西文化藝術,如中國古陶瓷、巴蕾舞、意大利歌劇、烘焙糕點、乳酪鍋、巴黎女人……等等,文字真情真性,令人神往。
作者簡介:
莊良有,字淇芸,原籍福建晉江,生長於馬尼拉。留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獲得考古與藝術系碩士學位。歷年來苦心鑽研在菲出土十至十七世紀中國外銷瓷,多次為菲東方陶瓷學會舉辦瓷展並出版展錄。平生愛好文藝,熱心支持菲華文藝活動,為菲華文藝協會常務理事,作品多發表於該協會之文藝月刊《菲華文藝》上。
章節試閱
烤爐邊的故事
我唯一的拿手專技是烘焙西式糕點。自嘆一生不善烹飪,做起飯來張張皇皇,雖然有時尚能差強人意。可事倍功半,好不吃力。當年為了面臨廚房的重擔,急著要應付吃飯的問題,大凡本地中西名師傅開班,我就趨前求教。豈料所學菜譜,都只有一面之雅,試做過一次,就恝然置之。缺乏興趣乎?沒有稟賦乎?自己百思不解,為何對烹飪之技如此不出息。我不是不覺察到與生俱來有一雙特別笨拙的手。學了五年鋼琴,手指頭在琴鍵上動彈,既無力又不伶俐。寫起書法,東歪西倒,自憐亦復自笑。小學時代的勞作才把我折騰得厲害,做紙花、塑黏土...
我唯一的拿手專技是烘焙西式糕點。自嘆一生不善烹飪,做起飯來張張皇皇,雖然有時尚能差強人意。可事倍功半,好不吃力。當年為了面臨廚房的重擔,急著要應付吃飯的問題,大凡本地中西名師傅開班,我就趨前求教。豈料所學菜譜,都只有一面之雅,試做過一次,就恝然置之。缺乏興趣乎?沒有稟賦乎?自己百思不解,為何對烹飪之技如此不出息。我不是不覺察到與生俱來有一雙特別笨拙的手。學了五年鋼琴,手指頭在琴鍵上動彈,既無力又不伶俐。寫起書法,東歪西倒,自憐亦復自笑。小學時代的勞作才把我折騰得厲害,做紙花、塑黏土...
»看全部
作者序
自序
七十年代是我的浪蕩時期,日子打發在橋牌上的多。結交很多朋友,也玩得很痛快,可腦子空蕩蕩,有說不出的空虛感。幸有施穎洲先生把我從荒山裡找出來,鼓勵我參與文藝活動。在二十多年漫長歲月裡,有勇氣執筆塗塗寫寫,全拜施穎洲先生之賜,感謝他的提攜與顧愛,作品儘管不成熟,總算沒有交白卷。這份恩情將永遠銘記我心。
這些遣懷的文章,明知火候不夠,但都是動了真情寫的。早期的舊作、文字尤稚嫩,因留有生命鱗爪,仍然把它視作褪色泛黃的照片保存下來。
許多作品是為抒暢生活裡零零星星的際會所激起的感觸。享受到如夢似幻的...
七十年代是我的浪蕩時期,日子打發在橋牌上的多。結交很多朋友,也玩得很痛快,可腦子空蕩蕩,有說不出的空虛感。幸有施穎洲先生把我從荒山裡找出來,鼓勵我參與文藝活動。在二十多年漫長歲月裡,有勇氣執筆塗塗寫寫,全拜施穎洲先生之賜,感謝他的提攜與顧愛,作品儘管不成熟,總算沒有交白卷。這份恩情將永遠銘記我心。
這些遣懷的文章,明知火候不夠,但都是動了真情寫的。早期的舊作、文字尤稚嫩,因留有生命鱗爪,仍然把它視作褪色泛黃的照片保存下來。
許多作品是為抒暢生活裡零零星星的際會所激起的感觸。享受到如夢似幻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莊良有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2-03-22 ISBN/ISSN:978986221884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