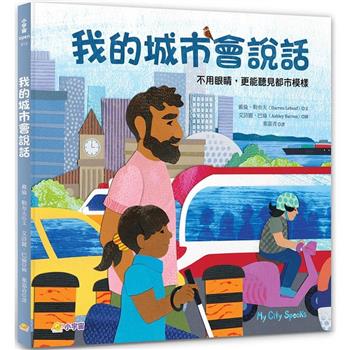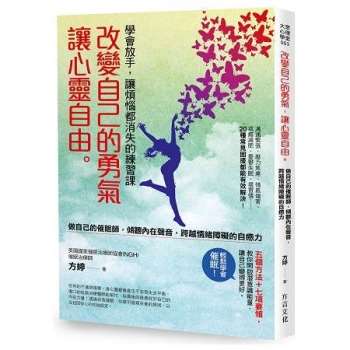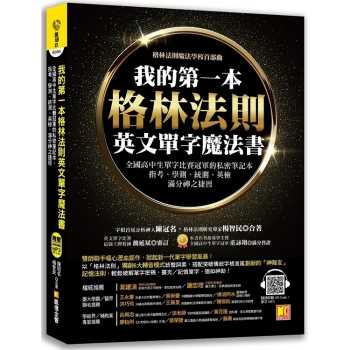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科幻小說
第二節 中西科幻小說的比較探討
第三章 科幻小說的文化性
第一節 文化性界定
第二節 科幻小說文化性的涵蓋範圍
第三節 世界觀作為科幻小說深層文化性的標誌
第四章 中西科幻小說文化性中的世界觀差異
第一節 世界觀差異的差異性
第二節 西方科幻小說源自深具馳騁想像力的創造觀
第三節 中方科幻小說源自但憑內感外應的氣化觀
第五章 西方科幻小說的文化性舉隅
第一節 英雄歷險的系統內部差異
第二節 艾西莫夫《正子人》的變身歷險
第三節 海萊因《4=71》的穿梭太空歷險
第四節 威爾斯《時間機器》的未來歷險
第五節 凡爾納《海底兩萬里》的海底歷險
第六章 中方科幻小說的文化性舉隅
第一節 困境糾纏的系統內部差異
第二節 張系國《星雲組曲》的愛情糾纏
第三節 倪匡《後備》的命限糾纏
第四節 葉李華〈戲〉的虛擬世界糾纏
第五節 黃海《鼠城記》的毀滅糾纏
第七章 中西方科幻小說文化性差異的運用途徑
第一節 在閱讀教學上的運用途徑
第二節 在科幻小說寫作教學上的運用途徑
第三節 在相關傳播教學上的運用途徑
第八章 結論
第一節 要點回顧
第二節 未來研究與展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