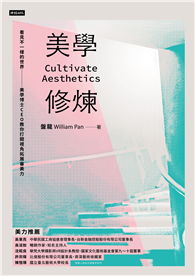光華流轉,烈焰狂舞,如此絢麗的劍法,配上繁花一樣的女子。她不見得是將棲霞劍使得最好的一個,但無疑是使得最美的一個。
所有弟子的體內,全埋了沉睡之蠱「焦明」。
一旦掌門人離開,焦明就會醒來,每個人都得死
學武之人一生追求的,除了絕世武功,就是長生不老了……
蠱派武俠小說家 薛西斯 卻顛覆了這個古老的命題
「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評審、武俠小說家 喬靖夫 讚道:
「此作最大特色,是採取了武俠小說一個很常見但並不常主打的題材──蠱毒為故事重心……單以故事結構嚴謹程度,《不死鳥》是最強的一部,甚至比今屆(第九屆)首、次名作品猶有優勝處。」
「丹陽派」百年來死守著一份經卷,幾乎是其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所有弟子信仰的價值。據聞經卷裡記載著長生不死藥「不死鳥」的煉製方法。
但這一切,從掌門人殯天之時全變了──
每隔二十年,青竹、棲霞、隱松三派舉辦「三寒會」,為的是輪轉信物。一來以明心志,表示絕無侵吞信物之意;二來又能常交流三派感情,永結友好之盟。聽說那個信物,叫作「百年身」,眾人只聞其名、不見其形,只好就著這名字胡亂揣測,其中傳得最凶的一種,就是不死藥。
真正的不死藥,到底是「不死鳥」,還是「百年身」?
或是這世上,從不曾出現過不死藥……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不死鳥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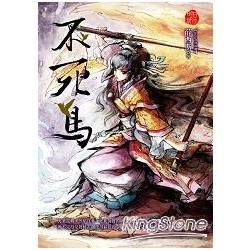 |
不死鳥 作者:薛西斯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1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4 |
二手中文書 |
$ 266 |
小說/文學 |
$ 280 |
武俠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不死鳥
內容簡介
目錄
自序
一、流棺葬
二、陸長生
三、畫中身
四、銀火花
五、驚鴻影
六、火燒雲
七、子母蠱
八、飲鴆局
九、代桃僵
十、火琉璃
十一、斫紫荊
十二、暴風雪
十三、百年身
十四、三寒會
十五、一鶴歸
十六、鳳還巢
尾聲、不死鳥
一、流棺葬
二、陸長生
三、畫中身
四、銀火花
五、驚鴻影
六、火燒雲
七、子母蠱
八、飲鴆局
九、代桃僵
十、火琉璃
十一、斫紫荊
十二、暴風雪
十三、百年身
十四、三寒會
十五、一鶴歸
十六、鳳還巢
尾聲、不死鳥
序
自序
既然這是自序,就容我聊得瑣碎一些。
我寫故事的習慣比較隨意(可能寫自序也是),通常我不為一個特定主題書寫,只是腦中朦朦朧朧有個「我想寫個類似……這樣的故事」的想法,接著就依輪廓蓋起毛坯屋,讓居民慢慢搬進來。
寫作《不死鳥》的時候我常在想,這是一棟俠義新成屋,搬進我屋裡來的這些人誰稱得上俠?也許誰都算,也許誰都不算,在空間中畫一道直線,沒有一種畫法能把所有點永遠都歸到同一邊。武俠這兩個字常連在一起,看上去鐵打一樣的剛硬,但我想硬的是武,不是俠,俠是一個很溫柔的字,出發點都是來自對人的憐愛與關懷,只是這種心情因時因地、或近或遠,也許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太近了叫偏私,太遠了成聖人,有時候試圖去定義這些遠近之分是徒勞無功的。我的寫作初衷從來不是為了描繪任何一種形式的俠,反倒是常寫著寫著生了些感慨。
再回過頭來說我怎麼蓋房子這件事。
我時常覺得小說是極狡詐的一種文體。有人說最厲害的說謊方法叫九實一虛,九句實話裡摻上一句假話,叫你真假難分。而小說給我的感覺則正好相反,一個虛幻的故事說到底就是謊話連篇,但在作者無數的謊言裡,一定能找到幾句他真實的心情。
寫小說最大的樂趣就在這裡,你架構一個世界,在裡面盡情嘶喊,寄託你所有的理想或悔恨,並且不必在現實層面為之負責,因為大多數時候你都在說謊,鍾子期不是那麼多,沒有人會知道你真心想說什麼的。
讀小說最大的樂趣──好吧,部分樂趣也在這裡,在讀一個人的不同作品時,我喜歡留意他每個故事裡反覆出現的元素。(當然不是每個作者的元素都很明顯,有些人技巧高妙,把自己藏得很深。)我們拿曲子來做比喻,或許他每首曲子的主旋律都天差地別,但仔細聽,你總能聽見一些熟悉的小節。
這些熟悉的小節有時源於作者的懶惰,有時則更像他微弱的呼救──觀察到後者時尤其令人驚喜,一個人反覆書寫的主題,常常是他最在意、或讓他最痛苦的事。因為很難受,所以只好一直說。
聽見那呼救的瞬間,我總覺得我的手彷彿能穿過冰冷的書頁,碰觸作者的血肉之軀(當然也極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誤判)。前面提到我先蓋房子,再請居民自己搬進來,我想這些居民裡也許就藏了些我的元素。房子蓋久了,總是會見到些老面孔。
我不為居民蓋房子,這種做法缺點很多,因為故事的主題容易鬆散,缺乏一個一以貫之的強力水柱來炮擊讀者,好像就少了點文以載道的高貴情操。
可是這樣做卻會讓我說比較多實話,對我來說,吐實的過程或許就是寫作最大的意義。我其實不那麼擅長說話,大抵我說得最好的是假話,該真誠說出口的那些卻總說得支離破碎,這就是我喜歡編故事的一個原因,故事永遠是謊言,讓我得以安心地在裡面說真話。
偶爾我想,或許這故事只是一封寫了二十萬字的情書,寄託我永遠說不出口的歉意與謝意。
既然這是自序,就容我聊得瑣碎一些。
我寫故事的習慣比較隨意(可能寫自序也是),通常我不為一個特定主題書寫,只是腦中朦朦朧朧有個「我想寫個類似……這樣的故事」的想法,接著就依輪廓蓋起毛坯屋,讓居民慢慢搬進來。
寫作《不死鳥》的時候我常在想,這是一棟俠義新成屋,搬進我屋裡來的這些人誰稱得上俠?也許誰都算,也許誰都不算,在空間中畫一道直線,沒有一種畫法能把所有點永遠都歸到同一邊。武俠這兩個字常連在一起,看上去鐵打一樣的剛硬,但我想硬的是武,不是俠,俠是一個很溫柔的字,出發點都是來自對人的憐愛與關懷,只是這種心情因時因地、或近或遠,也許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太近了叫偏私,太遠了成聖人,有時候試圖去定義這些遠近之分是徒勞無功的。我的寫作初衷從來不是為了描繪任何一種形式的俠,反倒是常寫著寫著生了些感慨。
再回過頭來說我怎麼蓋房子這件事。
我時常覺得小說是極狡詐的一種文體。有人說最厲害的說謊方法叫九實一虛,九句實話裡摻上一句假話,叫你真假難分。而小說給我的感覺則正好相反,一個虛幻的故事說到底就是謊話連篇,但在作者無數的謊言裡,一定能找到幾句他真實的心情。
寫小說最大的樂趣就在這裡,你架構一個世界,在裡面盡情嘶喊,寄託你所有的理想或悔恨,並且不必在現實層面為之負責,因為大多數時候你都在說謊,鍾子期不是那麼多,沒有人會知道你真心想說什麼的。
讀小說最大的樂趣──好吧,部分樂趣也在這裡,在讀一個人的不同作品時,我喜歡留意他每個故事裡反覆出現的元素。(當然不是每個作者的元素都很明顯,有些人技巧高妙,把自己藏得很深。)我們拿曲子來做比喻,或許他每首曲子的主旋律都天差地別,但仔細聽,你總能聽見一些熟悉的小節。
這些熟悉的小節有時源於作者的懶惰,有時則更像他微弱的呼救──觀察到後者時尤其令人驚喜,一個人反覆書寫的主題,常常是他最在意、或讓他最痛苦的事。因為很難受,所以只好一直說。
聽見那呼救的瞬間,我總覺得我的手彷彿能穿過冰冷的書頁,碰觸作者的血肉之軀(當然也極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誤判)。前面提到我先蓋房子,再請居民自己搬進來,我想這些居民裡也許就藏了些我的元素。房子蓋久了,總是會見到些老面孔。
我不為居民蓋房子,這種做法缺點很多,因為故事的主題容易鬆散,缺乏一個一以貫之的強力水柱來炮擊讀者,好像就少了點文以載道的高貴情操。
可是這樣做卻會讓我說比較多實話,對我來說,吐實的過程或許就是寫作最大的意義。我其實不那麼擅長說話,大抵我說得最好的是假話,該真誠說出口的那些卻總說得支離破碎,這就是我喜歡編故事的一個原因,故事永遠是謊言,讓我得以安心地在裡面說真話。
偶爾我想,或許這故事只是一封寫了二十萬字的情書,寄託我永遠說不出口的歉意與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