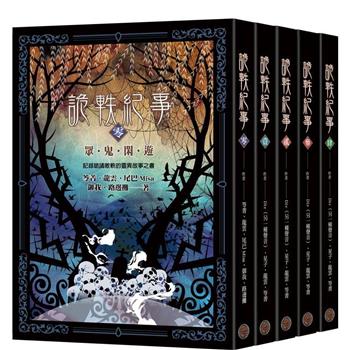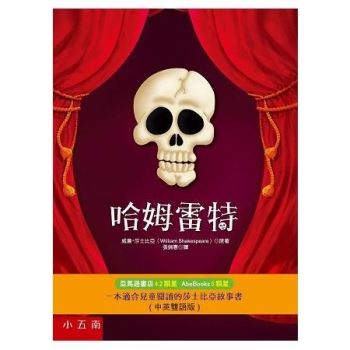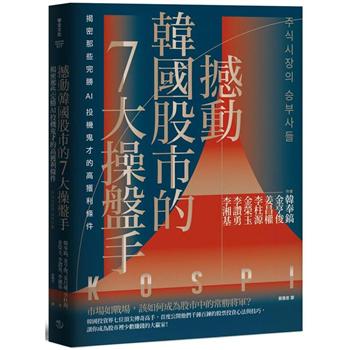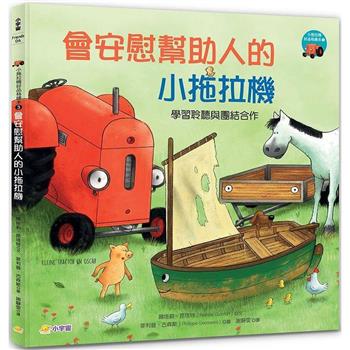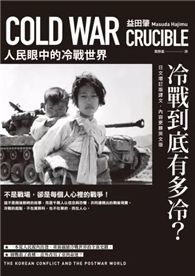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比利時年度最佳青少年圖書獎
圍牆上的那段夏日時光,讓三個孩子體認到生命的無常和親情的可貴
整個暑假,奧斯卡和哥哥波西,以及他們的好朋友喜兒,總是坐在行動總部——銀河路的一堵牆上——等待著。
他們在等待兄弟倆離家的媽媽回來、喜兒生病的姑姑好起來,還有一位老太太和她那條很老很老的臘腸狗,每天傍晚六點都會經過這堵牆。然而,有一天,老太太和狗卻不再出現。波西和喜兒打賭:老太太和老狗誰會先死?這個賭注,讓看似平靜的夏天起了波瀾……
一個不平凡的親情故事
比利時荷語作家巴特.慕亞特以詩意、充滿電影感的文字,透過小男孩奧斯卡來述說暑假尾聲的夏日時光。三個孩子總是坐在廢鐵工廠外圍的一堵牆上,那是他們的行動總部,沒有屋頂、沒有牆壁,也沒有任何行動總部該有的東西。他們每天在牆上彎身往下看,並沒有迎面而來的奇遇或等著他們啟程的冒險,時間彷彿靜止,夏天將永久停留。
三個孩子看似成天無所事事、嬉笑玩鬧,其實各有心事。作者以簡約、特殊的優美文筆描寫了孩子的日常生活:兄弟打架、與好朋友冷戰、對異性的好奇、擔心被父母拋下,以及對死亡的恐懼和不安,而最後溫暖的結局不禁讓人嘴角上揚。
佛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游鎮維 專文導讀
書籍重點
★比利時年度最佳青少年圖書獎★
宛如電影的詩意筆觸,寫出三個孩子最純真的想望
一堵空盪盪的圍牆,是三個孩子夏日時光的全世界,
他們各懷心事,迎接生命成長的洗禮……
圍牆上的那段夏日時光,讓三個孩子體認到生命的無常和親情的可貴
作者簡介:
巴特.慕亞特
比利時知名荷語作家,以少年小說和詩作聞名。生於1964年,是家裡的第七個兒子,從小就喜愛瑞典作家林格倫的《長襪皮皮》,曾在布魯塞爾求學,畢業後當過編輯、譯者,1995年開始成為全職作家,1996年以《赤手》(Blote Handen)獲得德國兒童青少年文學獎,評論家認為他擅長營造氣氛、文字充滿電影感。除了寫書和詩,他也創作劇本,偶爾會登臺演出舞臺劇。
2011年第四次獲國際安徒生大獎提名,2012年連續第十次獲林格倫兒童文學獎提名。寫作至今得過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文學獎項,作品已被翻譯成19種語言。
慕亞特作品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同時吸引孩子和大人。他創作的故事對孩子來說易懂好讀,但又有很多空間能讓大人進一步探討。
2006和2007年獲選為安特衛普城市詩人,並受邀擔任2016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的藝術總監,目前住在安特衛普。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慕亞特以簡約的寫作風格,說出一個不平凡的親情故事,全書行文清清淡淡,文字意味深長雋永,值得令人推敲再三。
——佛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游鎮維
國外書評推薦
慕亞特是編織故事的高手,總是以精巧又不著痕跡的方式,創造出完美、成熟又充滿張力的文學作品,這在青少年文學中並不常見。
——《荷蘭忠誠報(TROUW)》
為何一本書能夠從第一個句子開始就如此扣人心弦,讓人佩服。
——《荷蘭商報(NRC HANDELSBLAD)》
透過精密的構思、質樸的文字及其隱藏在背後的不可思議力量,從一個簡單的故事,發展成一篇充滿難以言喻的情感而且令人著迷的史詩,可以說是一顆文學珍珠。
——《比利時日報清晨(DE MORGEN)》
美好的故事結局,但是不同於其他青少年小說那種令人難以消化的浪漫方式。
——Coen Peppelenbos(文學部落格Tzum)
這本書的強大力量來自於「平常」,慕亞特以優美、特殊的文筆描寫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物。
——Vertel Eens(童書部落格)
銀河是一條在宇宙兩極間延伸的光帶,由光度強弱不同的星星組成,所散發的光亮讓人不由得沉思。
——但丁(義大利中世紀詩人)
靴子,準備好了嗎?走吧!(Are you ready, boots? Start walking!)
——南希‧辛納屈(Nancy Sinatra)
名人推薦:名人推薦:
慕亞特以簡約的寫作風格,說出一個不平凡的親情故事,全書行文清清淡淡,文字意味深長雋永,值得令人推敲再三。
——佛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游鎮維
國外書評推薦
慕亞特是編織故事的高手,總是以精巧又不著痕跡的方式,創造出完美、成熟又充滿張力的文學作品,這在青少年文學中並不常見。
——《荷蘭忠誠報(TROUW)》
為何一本書能夠從第一個句子開始就如此扣人心弦,讓人佩服。
——《荷蘭商報(NRC HANDELSBLAD)》
透過精密的構思、質樸的文字及其隱藏在背後的不可思議力量,從一個簡單的故事,發展成...
章節試閱
提議
我哥每講兩句話,就一定要穿插一句「狗屎」,無論如何他就是改不掉。他一直踢喜兒的腳,但喜兒懶得理他。第一,因為她很聰明,帶了一本很厚的書來,夠她看很久;第二,因為她不容易被惹毛,即使像波西那樣愈踢愈起勁,她還是愛理不理。
我看不下去了,替她出聲。
「波西,別鬧了!」
他停下來大大的歎了一口氣,一句狗屎不夠,接二連三的狗屎脫口而出,好像那是他的專屬詞似的。但你還是可以聽得出來,那字眼不曾屬於他,以後也不會屬於他。那是他從報紙上看來的,報上說有個愛爾蘭人有一天突然開始罵髒話,然後就再也改不了了。
「怎麼樣?就把這地方當作我們的行動總部?」波西突然開口。
喜兒抬頭看他,翻了翻白眼,不可置信的問:「我們的行動總部?這地方?這是我第一次從裡面看出去,我看不到總部的屋頂。」
「在義大利,有的房子本來就沒有屋頂。」
他竟然提到義大利,嚇了我一跳,媽媽現在人就在義大利。
「那裡的房子至少有牆壁吧!」喜兒說。
波西裝作沒聽見。
這我辦不到,我向來什麼都聽得見,也大都記得。
波西再說了一遍他的提議:現在,我們三個人組成團隊,必須想像此刻我們就身在行動總部裡。
喜兒和我看看四周,試著想像一間完整的行動總部,這可不容易。沒有可以掛海報的牆壁,沒有飛鏢盤,沒有桌子、椅子,沒有可以冰飲料的冰箱,沒有領養來的貓,沒有專屬的徽章,沒有隊名,沒有收音機,也不能大聲高唱屬於我們自己的歌。
我們的行動總部就只是廢鐵工廠外圍的一堵牆。
牆的一邊是工廠倉庫的平頂屋簷,這倉庫是珮特拉和皮特工作的地方,工廠的院子裡堆滿各式各樣分類好的廢鐵。
牆的另一邊是銀河路,當我們彎身往下看,看到的不是迎面而來的奇遇,而是靠著牆邊生長的稀疏灌木叢,還有樹叢旁的灰色人行道。
「好吧。」我說。
「很好。」喜兒簡短回答後又埋頭看書了。
「嘿,我們這麼無聊沒事做,難道是我的責任嗎?」波西兩手抱在胸前沒好氣的說。
「你是我們當中年紀最大的,你要做決定。」我說。
「小弟弟。」波西對著我說。
「哥哥。」我回敬他。
我察覺到喜兒往我們的方向瞄,仍面不改色,她原本可以大笑的。她看看波西,再看看我,然後目光又回到波西身上。令我驚訝的是,過了一會兒她又繼續低頭看書,不再理會我們。
波西很洩氣。
「嘿,」他伸出雙臂說:「難道這裡是王宮,而我是弄臣嗎?」
我和喜兒抬頭看著他。我們同時皺起眉頭,想到頭頂上的豔陽,也許波西喝太少水了,才會說這麼奇怪的話。
「我必須幫你們找事做嗎?」
「你什麼也不必做。」我說:「但是如果你想要……嗯……成立我們的行動總部,那就得想辦法找點新鮮有趣的事情讓我們嘗試、見識一下。」
「呸!」喜兒不以為然,她有書就夠了。
「呸什麼?」我對喜兒說:「妳到底要不要跟我們一起?」
喜兒眨眨眼,她在想該怎麼回答。這幾個星期來,她已經不再整天跟著我們混了,因為她有時必須去探望姑姑,她姑姑可能快死了。
她慢慢闔上書後說:「我當然是跟你們一夥的。」
「所以啦。」我說,然後看著波西。
「所以什麼?」波西問。
我回答:「如果這裡是我們的行動總部,從現在起我們就要像個團隊一樣行動。」
喜兒皺起眉頭,差點又把書打開。
「要怎樣才算像個團隊一樣行動?」她指著自己說:「一個團隊?我不屬於團隊,我獨來獨往。」
傑克爾
波西彎身探頭往下看,然後用下巴示意我們看南希‧辛納屈的狗,牠正從我們下面經過。
「嘿,臘腸狗傑克爾!」他大聲叫喚。
我們每天在同一時間看著牠從下面經過。現在經過的這隻雖然和昨天那隻顏色一樣,卻好像換了一顆頭和四條腿。
「嘿,臘腸狗傑克爾!」我們三個人一起叫。
那隻狗根本沒有抬頭看我們。牠喘著氣,邁著短腿搖搖擺擺的繼續往前走。牠的爪子刮著人行道上的地磚,走路的樣子好像在學溜冰。
波西、喜兒,還有我,我們就這樣目送牠走過,想看看牠是不是有辦法走到銀河路的盡頭。
傑克爾沿路緊挨著樹叢走。我在心裡替牠加油,好像牠在參加什麼比賽似的。當牠在街角轉彎時,我的肩膀也跟著轉,好像這樣就可以借力給牠。
那隻狗的前半身已經到了另一條街,牠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讓屁股也跟著轉彎。
當牠整個身體都成功轉彎了的時候,我為牠拍手叫好。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沒有站起來沿著牆壁跑到轉角去,看牠是不是真的像我看見的一樣成功轉彎。
轉角有一塊屬於教會的空地,我們從來不去那裡。傑克爾在那裡每次都是先繞一圈,然後再往回走。
「那隻狗真是的。」我說。
「你還真關心那隻狗。」喜兒說。
「我甚至用念力把能量傳給牠。」我說。
喜兒點點頭。「我看到了。」她說:「而且真的有用。」
「是啊。」波西說,他一邊伸舌頭,一邊用手指敲敲頭同時還做鬥雞眼。
喜兒和我同時轉頭盯著波西看。
她說:「你到底幾歲了?」
我發出噓聲,然後學媽媽用一模一樣的口氣喊了聲:「波西!」
南希
差不多過了一分鐘後,南希.辛納屈也從下面慢吞吞的經過。她每次都是離她的狗有點遠之後才出現,因為她的腿常常沒力。
波西、喜兒,還有我,我們整個夏天每天都在觀察她和她的狗,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拿她當笑話說,雖然她腳上的靴子短得可笑,我們也從來沒有嘲笑過。
我總是靜靜的看南希從下面走過,我實在沒辦法想像,像她這麼老了還能遛狗。
「你們看!」波西說。
「到底是誰在遛誰?」
南希和她的狗一樣像在學溜冰。
好幾次都是一樣的場景:她突然不敢再往前走,就站在那裡不動超過一分鐘,彷彿碰到了太高而跨不過去的障礙。她從領子伸出的頭,就像烏龜從龜殼伸出的頭,小心翼翼的像是怕被汽車或腳踏車撞上,其實沒什麼車子會經過銀河路,她應該知道這點。
她費力的抬起一隻腳,然後小心的往前踏出一步。
波西彎身看著她,張開嘴似乎想說什麼,但是沒說出口。他看著南希的背影,就像我之前看著傑克爾那樣,他轉動上半身,像是自己要轉過街角似的,肩膀也跟著轉。
南希一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中,我們三個人就同時歎了一口氣。
幸好她又辦到了。
打賭
在教堂前面的空地上,南希每次都會停下來看傑克爾沿著空地跑一圈,再讓牠到草地上跑一會兒,然後一同往回走。
「嗯。」波西哼了一聲,嘴角往下垂。
「怎麼了?」我問。
「再過幾天,南希大概就一步也走不動,然後就永遠安息了。」
「住嘴!」喜兒說:「你不可以詛咒還沒死的人。」
波西咂嘴表示不耐煩,好像喜兒打斷他的思路,讓他沒法繼續。他說他根本沒用到死這個字。
「安息跟死是一樣的意思。」她把書放在旁邊,兩條腿垂在銀河路這一側懸空搖晃。她往後仰,雙手撐在倉庫的屋頂上。
她說:「臘腸狗傑克爾已經八十歲了。」
「南希也差不多。」波西說。
「將狗的年紀換算成人的歲數,對一隻狗來說,八十歲已經是老態龍鍾了。」喜兒說。
「對人類來說就不是嗎?我認識的人中,沒有人八十歲了。」
喜兒沉默了一下,故意看往別的地方。
「波西,你的話有點蠢。」她說:「一隻八十歲的狗比一個八十歲的人容易死掉。」
「這世界上最長壽的狗活到一百四十歲,我是說換算成人的歲數。」
「那又怎樣?」喜兒說,她拂了拂臉上的汗珠。「狗比人容易死。你看看傑克爾,肚子都快拖地了,牠一定很想躺下來,過不久牠的腿就會因為累壞了再也站不起來。」
「累壞了?」波西不以為然的說:「沒那麼嚴重吧!如果累壞了就會怎麼樣,那我們到週末都會死。」
我忍不住大笑。
「沒錯,」我說:「如果一累壞了就會死,那我現在就得進棺材了。」
「閉上你們的烏鴉嘴!」喜兒說。她認為事情有可能比想像的來得快。
波西露出興奮的表情。
「聽我說,」他說,同時對喜兒伸出手,「我們來打個賭怎麼樣?」
「打什麼賭?」
「看誰會先死。」
喜兒猛搖頭說:「不行,不行,不行。」
「什麼不行,不行,不行?」
「在我剛剛讀的書裡,有個人承諾他再也不去做某件事,結果最後他還是沒有遵守諾言。」
「承諾和打賭不一樣。」波西說:「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誰會先死?南希還是她的狗?」
我笑得很小心。我問:「贏的獎品是什麼?」
「好問題。」 波西考慮了一下子。
「贏的人可以有決定一整天所有事情的大權。」
「哇!」喜兒驚呼。「那這裡就是王宮,我就是女王。就這麼說定了。贏的人有一整天決定一切的大權。」
「我是見證人。」我說。
我們三個人同時屏住呼吸,因為我們聽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傳來喘氣聲。
那是南希和傑克爾同時在喘。
他們正在回家的路上,一同慢吞吞的走著,但是慢慢的傑克爾又走在前面了。
喜兒往下看,然後說:「傑克爾會先死。」
「我認為南希。」波西肯定的說:「百分之百是南希。」
他們兩個人高舉雙手,互相擊掌。這一掌的聲音很響亮,而且可能很痛,但是他們兩個都面不改色。
南希嚇了一大跳,她小心翼翼的抬頭看我們,當她看見我們的頭時,她把手放在胸前。
「小男孩,你們好。」她聲音顫抖的說。
我們互相對望。
「小男孩,你們好?」我們齊聲說。
喜兒皺起眉頭,她向前彎身,對著南希點頭。
「您好,辛納屈先生!」她說。
我們三個忍不住大笑。
謎
第二天,教堂的鐘敲了六下時,我們都在等南希和傑克爾的出現。我們踮著腳尖站在倉庫屋簷的邊緣張望,喜兒提議我們一起大喊。
「傑克爾!南希!」
其實沒什麼用,畢竟這又不是他們真正的名字。
傑克爾和南希沒有出現。
我們告訴自己這只是碰巧,明天他們就會再經過這裡。
我們設想各種可能性:南希帶著臘腸狗度假去了;南希生病了所以沒辦法遛狗;傑克爾生病了所以也不能出門;他們改變習慣,現在換了另一條路線,不知道怎樣才能走到銀河路來;他們搬家了;傑克爾發現了新的、可以繞著跑的空地。
波西撞了喜兒一下,然後說這樣一來有兩個贏家。
「為什麼有兩個?」喜兒不服氣的問。
「因為他們兩個都死了。」波西說:「他們兩個同時死了。」他高舉拳頭歡呼,我摀住他的嘴。
「住嘴!」我說。
「沒錯。」喜兒說:「你不應該當面嘲笑死亡。」
我們從牆上跳下來,沿著人行道走到轉角,也就是每次看著南希和傑克爾消失不見的地方。這時喜兒突然想到可以問一個剛好從斯多福街過來的路人,看他有沒有看見一個老太太帶著一隻狗經過。
「一個老太太帶著一隻狗?」那人問。
「沒錯。」喜兒說:「一隻老狗跟一個穿著紅靴子的老太太。您知道他們從哪裡來嗎?」
「妳是說靴子從哪裡來嗎?」那人故意說笑。
「不是。」喜兒邊說邊翻白眼,轉身不再理會那個人。
她又問了另一個路過的人同樣的問題,那人沒有開玩笑,但是很可惜的也沒看到老太太和狗。有些人馬上就知道我們問的是誰。
有些人像我們一樣也幫傑克爾或南希取了名字,他們也是每天看見他們從斯多福街經過。有個太太說:「一個人一旦有了名字,就真的存在。」有人叫傑克爾鏟子、拖把或小歪狗,叫南希拖鞋或駝子。
我們沒說我們叫她南希.辛納屈,這是一個女歌手的名字。我們家有她的唱片,就在媽媽的唱片收藏當中。那個女歌手已經唱很久了,唱了很多歌,其中有一首很受歡迎的歌就跟靴子有關。
那些人說他們把南希和她的狗當作時鐘,像是在路上要去赴約或在廢鐵工廠大門旁邊的車站等公車時。南希和她的狗就像時鐘一樣,每天都很準時,只要在銀河路附近看到她和狗就知道快六點了。
但是南希和傑克爾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沒有人知道。
「那是個謎。」喜兒說。她看看波西和我,然後揚起眉毛說:「真神祕。」
提議
我哥每講兩句話,就一定要穿插一句「狗屎」,無論如何他就是改不掉。他一直踢喜兒的腳,但喜兒懶得理他。第一,因為她很聰明,帶了一本很厚的書來,夠她看很久;第二,因為她不容易被惹毛,即使像波西那樣愈踢愈起勁,她還是愛理不理。
我看不下去了,替她出聲。
「波西,別鬧了!」
他停下來大大的歎了一口氣,一句狗屎不夠,接二連三的狗屎脫口而出,好像那是他的專屬詞似的。但你還是可以聽得出來,那字眼不曾屬於他,以後也不會屬於他。那是他從報紙上看來的,報上說有個愛爾蘭人有一天突然開始罵髒話,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