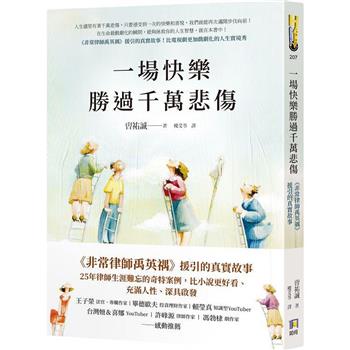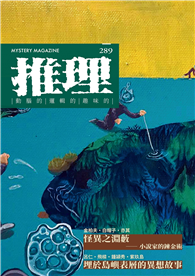桃園薈萃現代與傳統、工業與農業、進步與保守,
它的身影與面貌不停在改變,
不變的是生活在桃園的人擁有的共同記憶和集體想像。
它的身影與面貌不停在改變,
不變的是生活在桃園的人擁有的共同記憶和集體想像。
作者以凝視之眼、書寫之筆,透過記憶、訪查與想像,深刻勾描在生活中漂浪的桃園人圖像。
童年時的街屋、攤車記憶,一如未醒的夢;穿著入時、肩上爬著果子狸的俊俏男人,何以會變成眼神呆滯、推著回收車的拾荒者?客庄媽媽與草仔粿的故事,傳遞的是美好的人情味;從值班保全到父親的回憶,帶出忠貞新村移民的哀傷故事;百年客家詩社、二輪戲院等地景與童年舊事的點描……在作者筆下,都讓我們看到桃園人、桃園地、桃園事的蒼涼和美麗。
那些被拋擲和遺忘的桃園人文和自然景觀,通過本書,儼然縮時攝影,引領我們重新省視桃園人的故事。
向鴻全:「帶著自己家鄉的成長經驗或記憶,飛飄到這個世界的某處,落定下來,未來可能開出美麗的花或長成一棵成熟的樹,而文學需要更多的傳承,一棒接一棒,才有機會慢慢建立屬於桃園的文學記憶和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