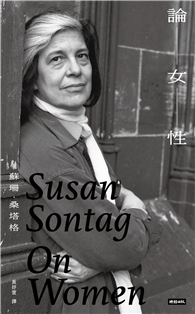一九九八年我出版《意象風景》時,心中經常有一種想法,那就是:儘量抽離自我,讓意象自身呈現詩的風景。因為抽離,詩作的題目文字儘量縮減。整本詩集中,兩個字為題的詩作共有四十一首,一個字為題的詩作共有二十七首,超過兩個字的詩題只有六首。
我的詩作經常「不說明」題旨,很少有「抽象概念」與情緒的字眼。《意象風景》的詩作更是如此。詩集中,一、兩字的題目大都呈現一個動作或是一個景象,如〈景象〉、〈風景〉、〈之後〉、〈癢〉、〈觸〉、〈幕〉等等。這樣的命題方式,對於任何情境,作者都不做說明,任由讀者想像發揮。
這是我那一段時間「執著」的想法,臺中文化中心出版後,我自己大致看一遍,嘴角不自覺地浮出微笑,心想:這就是我想要的詩集。
但近幾年,偶爾翻閱這本詩集,我將「作者」的意識隱去,以一個過路陌生的讀者看這些詩,閱讀不時讓自己疑惑甚至是驚異。正如上述,我的詩從不說明主旨,純粹以「意象」做「秀」(show),因此,在閱讀時,有好幾首詩雖然意象清楚,但很難掌握整體情境的輪廓。如〈之後〉,這兩個字不免引領讀者自問:「是什麼之後」,「之前發生什麼事嗎?」當讀者陷入如此的疑問時,詩行就可能變成獨來獨往的意象,很難勾勒成詩的情境。閱讀,變成對讀者的考驗,甚至是一種折磨。其實,這首詩與「什麼事的之前與之後」完全無關;如此命題,書寫時只是透露一種心境,一種時間行進中的轉折,一種時間過後可能的演變。但因為題目是「之後」,閱讀可能陷入「什麼事的之前與之後」中的泥沼,而錯失這首詩意象的繁花盛景。
兩個字的詩題如此,一個字的詩題更可能會讓讀者置身天馬行空。《意象風景》這本詩集中,不少一個字的詩題是描寫動作,如:望、飄、觸、傾、聽、奔、登、升等等。這是動作本身,沒有其他動作背景、過程的提示。讀者要進入詩的情境也有相當的難度。過去有些讀者說我的詩很難,我經常很疑惑,我的意象大都來自現實人生,意象敘述很清楚,文字很少刻意扭曲造作,怎麼會難呢?但,我現在能體會到一般讀者所感受的「難」。這個「難」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我的詩不「說明」題旨,因此對於那些想在詩中找主題的讀者,覺得難。二、是《意象風景》獨特的難。意象呈現一種動作「進行中」的狀態,缺乏具體情境的描述或是更明白的暗示。
如此的新發現,並不是對這本詩集感到失望。但重新閱讀中,發現若在題目上略微變動,讓詩題有更完整的敘述內涵,將有非常明顯的效果。〈之後〉那首詩,若是把整首詩的第一行「蟬叫醒夏的時候」當作題目,整首詩的情境就凝聚起來了。把〈景象之三〉改成〈刀劍鏗鏘之後〉,一個戰爭過後的「景象」就了了分明,閱讀馬上能感受到戰爭場面的悲劇。
再者,從一九九八年出版《意象風景》至今,二十五年已經過去了。隔著時間的距離重新看這些詩,不免有新的發現。過去的詩行、意象,有些已經無法面對當下的審視。於是,詩行做一些變動、修改,甚至是大量的改寫,已經是無法避免的命運。能「修改」舊作,也意謂當下已經跨越當時的視野與格局。如上述的〈之後〉,這首詩的第一行是「蟬叫醒夏的時候」,第二行是「正是雲要揮別山頭的時刻」,這次的重新閱讀覺得兩行的結尾「時候」與「時刻」太接近,應該略微調整,最後定稿變成詩題的第一行也改成:「蟬叫醒夏時」。這是意象的甦醒,詩的再生;類似的情形,不勝枚舉。於是,一本「變臉詩」詩集就這樣出現了。
以這個角度重新看其他詩集,也有新的發現。於是,《爆竹翻臉》與《放逐與口水的年代》也有一些詩「變了臉」。另外,二○○三年出版的《失樂園》,裡面有一些詩是「九二一」大地震心靈的震盪,而如此的震盪在二○一九年之後的「心冠病毒」中迴響。有些詩行與意象不自覺地在《變臉書》裡變成另一首詩。如〈國難〉裡的詩行「清晨,報紙有如訃文」成為一首新作的標題。〈災後〉中第二節變成《變臉書》中的〈輓歌〉的主要意象。我相信很多讀者跟我一樣,傾向以《變臉書》中新的詩名與修改過的內容取代舊有的詩作。但對我來說,《失樂園》的〈災後〉不應該被《變臉書》的〈輓歌〉取代。因為新作並不意謂對舊作的否定,而是以另一種新的面目作為時間落差下空間的迴響。藉由兩首詩的並存,我想呵護那個在兩個現實巨變中「神祕再現」的思緒。
這本詩集分成兩部分,正如標題所示,第二部分是「變臉詩」,第一部分則是全新的創作。整體說來,數十年來的書寫,詩作歷經一些風格的變化,乍看似乎有不同的面目,但詩心正如初心,並沒有變臉。
是為序。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變臉詩的圖書 |
 |
變臉詩 作者:簡政珍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1-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中文書 |
$ 323 |
小說/文學 |
$ 334 |
現代詩 |
$ 342 |
華文現代詩 |
$ 342 |
文學作品 |
$ 342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變臉詩
數十年來的書寫,
詩作歷經一些風格變化,乍看似乎有不同面目,
但詩心正如初心,並沒有變臉。
簡政珍的詩一向以意象和哲學思辨著稱,不過他過往的詩純粹呈現意象,沒有任何說明,也不代入任何色彩,單純呈現某個動作、時間的剎那畫面;《變臉詩》則開始注入作者的期待與希望,且這本詩集特別之處在於第二輯以「變臉」為核心,改寫舊作,讓舊作煥然一新,若同時比較舊作便可以察覺兩種不同感受的意象呈現。
《變臉詩》比以往的詩集都更突顯了簡政珍的詩心,帶著原本具備的哲學思辨、反諷暗喻、極富生命力等等特點,整體從難懂的空白填寫走到能懂的情感流動。
作者簡介:
簡政珍
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英美比較文學博士。曾任中興大學外文系專任教授、系主任,《創世紀詩刊》副總編輯兼主編,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外文系講座教授。
著有詩集《歷史的騷味》、《失樂園》、《放逐與口水的年代》、《臉書》等十二種;詩學、文論集《放逐詩學》、《詩心與詩學》、《電影閱讀美學》、《台灣現代詩美學》、《解構閱讀法》等二十一種。
批評家稱譽簡政珍為極具生命感與哲學厚度的詩人。洛夫說:中生代詩人中,「簡政珍的詩歌精神尤為突出」,「反諷暗喻和意象之精準有力,無人能及」。
曾獲創世紀詩刊詩獎、美國的大學博士論文獎、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等。2007年3月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曾為其舉辦「兩岸中生代詩學高層論壇暨簡政珍作品研討會」。2008年文津版的《台灣當代新詩史》稱之為「中堅代翹楚」。2019年聯經版的《台灣當代新詩史》將其選為新詩百年七位焦點詩人中的一員。
作者序
一九九八年我出版《意象風景》時,心中經常有一種想法,那就是:儘量抽離自我,讓意象自身呈現詩的風景。因為抽離,詩作的題目文字儘量縮減。整本詩集中,兩個字為題的詩作共有四十一首,一個字為題的詩作共有二十七首,超過兩個字的詩題只有六首。
我的詩作經常「不說明」題旨,很少有「抽象概念」與情緒的字眼。《意象風景》的詩作更是如此。詩集中,一、兩字的題目大都呈現一個動作或是一個景象,如〈景象〉、〈風景〉、〈之後〉、〈癢〉、〈觸〉、〈幕〉等等。這樣的命題方式,對於任何情境,作者都不做說明,任由讀者想像發揮。
這...
我的詩作經常「不說明」題旨,很少有「抽象概念」與情緒的字眼。《意象風景》的詩作更是如此。詩集中,一、兩字的題目大都呈現一個動作或是一個景象,如〈景象〉、〈風景〉、〈之後〉、〈癢〉、〈觸〉、〈幕〉等等。這樣的命題方式,對於任何情境,作者都不做說明,任由讀者想像發揮。
這...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變臉中的詩心
第一輯——光影沒入溪聲
春風的消息
睡醒之間
又有雨絲了
浩瀚無涯的星空
顏色革命
不必再等待
笑看微風吹起漣漪
心湖裡的倒影
望著流雲的魚
清晨
沸水的心事
失眠
生日
由遠而近
如歌的行板
我站在鐵軌旁邊
芒花——在父親的墓碑旁
空中搖晃的一生
雨季
酸溜溜的倒影
為了疫情
要告訴妳什麼呢?
朔風吹散三更雪
病毒的呢喃
宿醉
終局
這就是寒冬
光影沒入溪聲
翻掌時
等待所謂的晨曦
睫毛擴展眼球的企圖
遠方有戰爭
第二輯——變臉書
就在今夜
輓歌
清晨,報紙有如訃文
...
第一輯——光影沒入溪聲
春風的消息
睡醒之間
又有雨絲了
浩瀚無涯的星空
顏色革命
不必再等待
笑看微風吹起漣漪
心湖裡的倒影
望著流雲的魚
清晨
沸水的心事
失眠
生日
由遠而近
如歌的行板
我站在鐵軌旁邊
芒花——在父親的墓碑旁
空中搖晃的一生
雨季
酸溜溜的倒影
為了疫情
要告訴妳什麼呢?
朔風吹散三更雪
病毒的呢喃
宿醉
終局
這就是寒冬
光影沒入溪聲
翻掌時
等待所謂的晨曦
睫毛擴展眼球的企圖
遠方有戰爭
第二輯——變臉書
就在今夜
輓歌
清晨,報紙有如訃文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