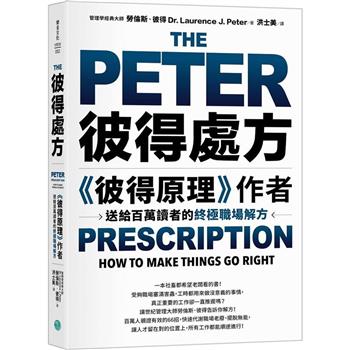是否只有回到北極,
才能擺脫被觀看的一生……
三代北極熊,透過書寫、表演與親密連結,在語言與記憶、夢境與現實間,與人類奇異的文學共振。
第一代北極熊「我」因為膝蓋受傷,從馬戲團當紅明星轉任行政工作,最後開始寫起自傳《眼淚的喝采》,意外地成為暢銷作家,不料卻就此流亡海外,從祖國蘇聯到西德柏林、加拿大,最後又回到社會主義國家東德;人類馴獸師烏爾蘇拉透過夢境與「我」的女兒第二代北極熊托斯卡成為心靈摯友,一人一熊共同演出駭目驚心的「死亡之吻」,並由烏爾蘇拉以其視角寫下與托斯卡相處過程的傳記,最終人熊的界線愈趨模糊……;托斯卡之子第三代北極熊努特出生即被遺棄,生活於柏林動物園,由一位男性飼養員悉心餵養長大,成為全球環境變遷代言人與寵兒。
多和田葉子以童話般寓言式的筆調,精巧魔幻的語言描寫北極熊三代橫跨冷戰時期、解凍時期、後冷戰時期,既悲哀又燦爛的「熊生」,梭巡往復於歷史真實和詩意幻想,將個體命運與國族隱喻、政治諷刺、環境倫理等巧妙融為一體。
《雪的練習生》既是冷戰幽靈的超現實寓言,也像是一部屬於動物的藝術家成長小說。
作者簡介:
多和田葉子
一九六○年生於東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一九八二年赴德國漢堡。蘇黎世大學博士課程修畢。一九九一年以《失去腳踝》獲群像新人獎。一九九三年,以《入贅狗女婿》獲芥川獎。二○○○年,以《雛菊茶》獲泉鏡花獎。二○○二年,以《球形時間》獲得日本文化村雙叟文學獎,以《嫌疑犯的夜行列車》獲谷崎潤一郎獎、伊藤整文學獎。其他作品有《掉進海裡的名字》、《修女與丘比特之弓》、《抓住雲的故事》等。以日德雙語發表作品,二○一六年因其德語創作獲得克萊斯特文學獎。二○一八年以《獻燈使》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部門)。二○○六年起定居柏林。
譯者簡介:
詹慕如
自由口筆譯工作者。譯作多數為文學小說、人文作品,並從事各領域之同步、逐步口譯。
臉書專頁:譯窩豐 www.facebook.com/interjptw
章節試閱
祖母的退化論
耳朵後側和腋下被他一搔,就覺得搔癢難耐,受不了、實在受不了,蜷起身子在地上滾動。可能還嘎嘎地笑了吧。屁股朝天,把肚子包在內側,身體呈弦月的形狀。因為還小,所以四肢著地毫無防備地肛門朝天,也絲毫不覺得有被襲擊的危險。不僅沒覺得危險,反而還有種整個宇宙都被吸進自己肛門裡的感覺。我在腸的內部感覺到了宇宙。一個「不過是長了幾根毛的嬰兒」竟然誇誇其談講起宇宙,一定會引人嘲笑吧。實際上我確實只是個「長了毛的嬰兒」。因為長了毛,就算全身赤裸也不會是光溜溜的狀態,摸起來會毛茸茸的。抓握東西的力量很發達,但不擅長走路,與其說走路,更像是趁著踉蹌的動力碰巧往前方移動。視界像罩著一層薄霧,聲音嗡嗡迴響,像在洞穴裡聽到的那樣,生存的慾望集中在手指和舌尖上。
舌頭上還殘留著母乳的記憶,所以把他的食指含在嘴裡時會有種安心感。他的手指上長著鞋刷一樣的硬毛。那手指在我嘴裡蠕動、陪著我玩。假如連這也玩膩了想起來,他會用整個手掌壓住我的胸,跟我玩相撲。
玩累之後我會直接把兩隻手掌貼在地板上,把下巴放在手腕上等待吃飯的時間。有時後我回想那曾經嚐過一次的蜂蜜滋味,難忘地舔著嘴。
有一天,他用一個奇怪的東西綁著我後腳。我奮力地蹬,想踢掉那東西,但那個東西牢牢綁著我的腳,怎麼也拿不掉。手開始覺得痛,我迅速舉起右手,然後馬上也舉起左手,但馬上失去平衡往前倒,雙手再次著地。手一碰到地板就很痛,我索性雙手用力往地板一推,借勢讓身體往後彈,花了幾秒保持平衡,但終究還是會往前倒、左手碰地。這時碰到地板的左手像被火灼燒般的痛。我急忙往地板一推。重複了好幾次這種過程,不知不覺中我竟可以用兩隻腳站立、取得平衡。
寫東西真是一件很詭異的事,像這樣盯著自己寫的文章看,腦子就開始天旋地轉,分不清自己人在哪裡。我進入了剛剛自己開始寫的故事裡,已經不在「此時此地」了。抬起眼,呆呆看著窗外,又慢慢回到了「此時此地」。但是這個「此時此地」,到底是哪裡?
夜深了,從飯店窗戶往外看,前面的廣場看起來就像個舞台。街燈的光像聚光燈一樣在地面照出一塊圓形。一隻貓走過那斜切的光束中。沒有觀眾。周圍一片寂靜。
那天有會議,會議結束後所有參加者都受邀參加豪華的餐會。我回到飯店房間先灌了幾口水。油漬鯡魚的味道還留在齒間。看看鏡子,嘴巴周圍有紅色的污漬。可能是紅蕪菁。我不愛吃根菜,但如果是飄著很多油脂的濃郁紅色羅宋湯,我往往會被肉香吸引,喝得津津有味。
坐在飯店床上,床墊被壓扁,下方彈簧發出吱嘎聲。今天的會議沒什麼特別的,之所以會忽然想起早已遺忘的幼年時代記憶,可能是因為今天「自行車之於我國的經濟意義」這個議題的關係。讓藝術家參加會議、對政策提出意見,可能是種圈套,所以大家都不太發言,只有我跟平時一樣,迅速地優雅舉起放在胸前的右手。我提醒自己動作必須流暢滑順、乾淨俐落。所有參加者的眼睛都集中在我身上。已經習慣。
我帶著有豐厚油脂的上半身、披著最高級雪白毛皮的身體格外龐大,把胸口稍稍往前挺,舉起手來,光是這樣就能讓性感的香氣如光粉般灑落,覆蓋周圍,不僅生物,連桌子、牆壁,都瞬間黯然失色淪為背景。毛皮的雪白帶有光澤,說是白又跟一般的白不一樣,是太陽光能穿透的白。太陽的熱能穿過這白色抵達肌膚,在肌膚下珍藏起來。這是成功活過北極圈的祖先們贏來的白。
要能發言必須獲得主席的指名,所以得比其他人更快舉手才行。會議上很少有人舉手能比我快。曾經有人挖苦地對我說:「您還真喜歡發言呢。」我答道:「這是民主主義的基本素養。」但是這一天我發現了。反射性舉手其實並非出於我自己的意志。我的胸口陣陣刺痛。我揮除這些疼痛,努力調整回原本的狀態。
假如主席那小聲得像蚊子叫的「請」是第一拍,那麼第二拍就是我緊逼而來的「我!」,第三拍大家會倒吸一口氣,到了第四拍我會堅定地說出:「有一個想法。」像這樣表面輕鬆、實則強勢地不斷往下講,之後就會漸漸進入舒適的節奏。
明明沒在跳舞,心情卻像在舞動一樣,我開始在椅子上扭腰,讓椅子發出吱嘎聲。發出重音的音節成了鈴鼓打起拍子來。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過來,呆呆看到渾然忘我,忘記任務、忘記體面,還有些男人耷拉著嘴唇,牙齒變成冰淇淋,開始溶化的舌尖變成口水,眼看著就要從濕潤的嘴唇滴落下來。
「自行車是人類至今發明的東西中最優異的道具。自行車是馬戲團之花,是環保政治的英雄。不久的將來,全世界的大都市中心將再也看不見汽車,完全被自行車所覆蓋。不僅如此。假如將自行車跟發電機相連結,大家不僅可以在家中鍛鍊身體,還可以自行發電。假如騎自行車去拜訪朋友,就不再需要行動電話或電子郵件。也就是說,除了自行車以外我們再也不需要其他機器。」
會場中有幾張臉沉了下來。一定是擔心不賣機器就賺不了錢。我說得更起勁了。「以後不再需要洗衣機,可以騎自行車到河邊去洗衣服。也不需要暖氣或微波爐,可以騎自行車到山裡去砍柴來燒就行了。」這時也出現了一些笑臉,但是漸漸鐵青的臉還是占了多數。別在意、別在意。這種時候不用急、冷靜慢慢來,我假裝沒看到大家的反應,只要在腦中想像著成千上百個如癡如醉傾聽我聲音的觀眾那充滿歡喜的臉,繼續往下說就行了。這裡是馬戲團。所謂的會議其實都是馬戲團。
主席輕咳兩聲,就像在提醒自己別被我牽著鼻子走,他看了看坐在最近座位、長著小鬍子的官員。對了,這兩人是一起進會議室的,應該彼此認識吧。也不是參加喪禮,但是那官員身穿黑色西裝,瘦得跟釘子一樣。「崇拜自行車、否定汽車,是荷蘭等部分西方國家可以看到的頹廢或感傷主義。」官員沒舉手就開始說話。「我們應該讓機械文明基於正確的目的繼續進化,加強連接住家和職場的交通機構。有人似乎誤解,覺得只要有自行車就能隨時隨地暢行無阻。這是很危險的想法。」我舉手想反駁,主席立刻宣布:「現在進入午休時間。」我沒跟身邊任何人交談,直接衝出建築物。明明沒必要奔跑,我還是像聽到下課鈴聲的小學生一樣,拔腿狂奔。
幼稚園時我經常像這樣跑出來,然後佔據院子最邊邊的角落一個人玩。就好像那個地方有什麼特別意義一樣。其實無花果樹下那裡曬不到太陽,十分陰濕,經常有人往這裡丟垃圾,沒有小孩願意走近,不過偶爾有小孩嬉鬧地跟在我後面,我就會把他們往前丟、嚇他們一跳。我力氣大,身體也大。
大家好像在背地裡叫我「尖鼻子」或者「雪人」。有個小孩很好心地告訴了我。其實我不知道對方告訴我這些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我根本不想知道別人是怎麼看待我的。不過這麼說來,好像真的只有我的鼻子形狀還有毛色跟大家不太一樣。
我看到舉辦會議的建築物旁邊有一個放了雪白長凳類似遊樂園的地方,便往那裡跑去。長凳對面有條小河,柳樹的枝葉百無聊賴地搔呀搔地輕撫水面。仔細看看,樹枝已經長出許多淺綠新芽。腳下的土也從內側開始翻鬆,探出頭的黃色番紅花在模仿著比薩斜塔嬉鬧著。耳朵裡開始覺得癢。但是不能挖耳朵。還站在舞台上的時代我堅守這條規矩,現在也都習慣不挖耳朵。
耳朵會癢不見得是因為有耳垢。可能是因為花粉,也可能是因為鳥兒們口中那些散落在高音域輕輕顫動的十六分音符。桃色的春天驟然降臨。春天到底用了什麼樣的機關?竟然可以帶著這麼多鳥和花迅速抵達基輔。是不是好幾個星期前就開始悄悄準備?難道是因為只有我在內心對冬天戀戀不捨,才沒發現春天腳步已經接近?我不太擅長談論天氣,所以很少跟其他人閒聊。經常因為這樣錯過了重要的訊息。腦中突然出現「布拉格之春」這幾個字。對了,布拉格之春來得也很突然。突然一陣悸動。該不會現在我身上正在發生什麼劇烈的變化吧?而只有我自己沒發現這件事?
凍結的地面融化,鼻腔裡開始覺得癢,黏稠的鼻涕垂下來,眼睛周圍的黏膜腫脹,忍不住流淚。這就是春天。春天很悲哀。有人說,到了春天會變年輕,但也因為變年輕,老是回想起小時候的事,回憶變成重擔,反而顯得老氣橫秋。真慶幸我現在還能讚嘆自己可以在會議上快速舉手這門絕活。但是說不定不要知道如何才能快速舉手比較好。
我不想知道。就算想知道,也不可能讓打翻的牛奶回到杯子裡。撲鼻的甘甜乳香滲透到桌布裡,我開始因為春天想掉眼淚。幼年期的回憶像蜂蜜一樣甜美。雖然甜,可是那種甜一旦濃縮,就會變苦。我沒有母親的記憶。母親去哪裡了呢?每次都是伊凡給我食物。
祖母的退化論
耳朵後側和腋下被他一搔,就覺得搔癢難耐,受不了、實在受不了,蜷起身子在地上滾動。可能還嘎嘎地笑了吧。屁股朝天,把肚子包在內側,身體呈弦月的形狀。因為還小,所以四肢著地毫無防備地肛門朝天,也絲毫不覺得有被襲擊的危險。不僅沒覺得危險,反而還有種整個宇宙都被吸進自己肛門裡的感覺。我在腸的內部感覺到了宇宙。一個「不過是長了幾根毛的嬰兒」竟然誇誇其談講起宇宙,一定會引人嘲笑吧。實際上我確實只是個「長了毛的嬰兒」。因為長了毛,就算全身赤裸也不會是光溜溜的狀態,摸起來會毛茸茸的。抓握東西的力量...
目錄
【導讀】在語言的冰面上共棲:《雪的練習生》與他者的語言政治/湯舒雯
祖母的退化論
死亡之吻
懷想北極的日子
【導讀】在語言的冰面上共棲:《雪的練習生》與他者的語言政治/湯舒雯
祖母的退化論
死亡之吻
懷想北極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