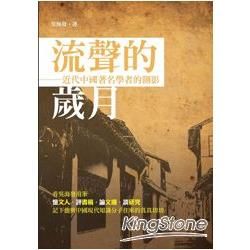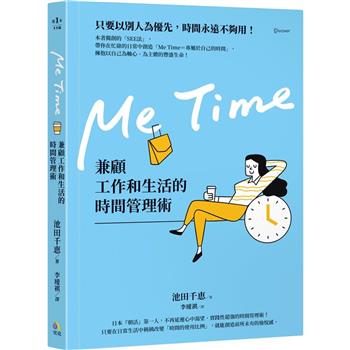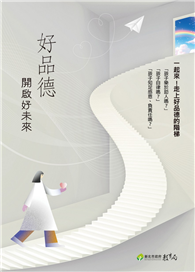代序∕余秋雨
文化,說起來很強大,實際上很脆弱。很多勝會高論、喜怒恩怨,轉眼就在歷史上煙消雲散。當然也會留下一些殘跡,後人以為是時間的結晶,其實並非如此。留下和殞滅,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即便是留下的,也未必是真相。
現在,資訊的貯存檢索技術越來越先進,照理不應該再有這方面的擔憂,但文化的事畢竟不能全然歸之於技術。這就像我們到一個村莊去,可以先在網路上查到各種相關的資料資料,歷年變遷,但把這一切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位安坐在河邊觀看落日的智慧長者。
這位智慧長者知道村莊裡很多無法形之於資料的人事往來、隱秘款曲。但這位長者必須知方圓、明事理、懂比較、有人緣,而且,又無官位之累,無名號之絆,只是勤奮記述,藏之箱篋,有人問起,便平靜表述。因此,我把這樣的人稱之為智慧長者。
本書的作者吳海發先生,就是這樣的智慧長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村莊」中,他以觀察者、問學者、品評者的身份,留存了很多易忘的片斷、特殊的記憶。可以算得出來,他在觀察、問學、品評之初,還是一個年輕人。他沒有多麼響亮的單位和頭銜,主要還只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卻為什麼會讓那麼多文壇名人與他頻頻書函往來?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別人被他所表現出來的學養、思路和態度吸引了。於是,很多堪稱重要的信件一封封寄到他所在的中學,而他也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某些線索的一個小小彙聚點。他在這方面的地位,已經超過很多著名大學中文系的教授。
從本書中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吳海發先生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全貌和細節都有比較廣泛的瞭解,對於現代漢語的知識和技能都有比較充分的修煉。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一份熱愛文化、保護文化的忠誠,追求著他心中的文化道義。他的筆墨,乾淨樸實,無雕琢之痕,無漂染之色。有時他也會與同行商榷,但只限文學,不攻人格,不作表演,有君子風。這一切,使他的文章讀起來有一種巷陌曲折的豐富性,又有一種不傷脾胃的安全感。
我的主業是中國宏觀文化史,偏重於宋元之前的文脈勃郁之時,因此對中國現代文學興趣不大。對當代文壇,更是避之唯恐不遠。本來我是不熟悉吳海發先生所寫內容的,但是,當我讀到科學家錢學森、楊振寧先生與他的書函來往,前輩文人葉聖陶、吳世昌先生與他的長篇通信,就覺得很有意思。那篇記郭沫若暮年隱痛的文章,讀來也覺得入情入理,溫厚公平,頗有心得。
有一次收到他寄給我的一部堪稱巨著的《二十世紀中國詩詞史稿》,未免有點吃驚,因為我知道他的年歲,要寫出一部八十多萬字的書稿很不容易。我儘管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仍然沒有多大興趣,但因有「詩詞」為引,也就與我的主業產生了局部交叉,便與他討論起來。二十世紀的詩詞創作,我覺得真正具有詩人神韻的,倒是郁達夫、蘇曼殊這些浪跡天涯的遊子。「曾因酒醉鞭名馬」、「踏過櫻花第幾橋」這樣的句子,僅從詩品而論,是高出於魯迅、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當然,吳海發先生要撰寫全史,必須顧全大局,不能像我這樣由著性情來。我雖然發了一通感想,但認真說來,還是沒有涉及現代文學,因為那些詩詞是現代人幹著古人的活兒,是新舊文化的一種「人格性銜接」。
感謝吳海發先生把一本專寫中國現代文學的散文集《流聲的歲月》,讓我這個「關閉現代」的人來寫序言。可能他想,外行也有外行的自由吧,那我也就輕鬆地享受這番自由了。因為明知是外行話,也就不寫「敬祈教正」這樣的客套話了,只能博吳先生和讀者一笑,如此而已。
是為序。
二○一二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