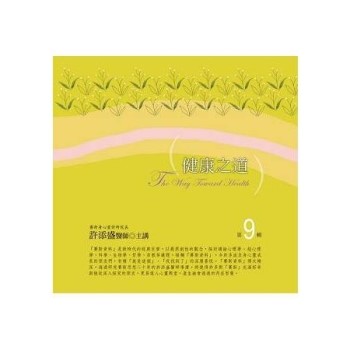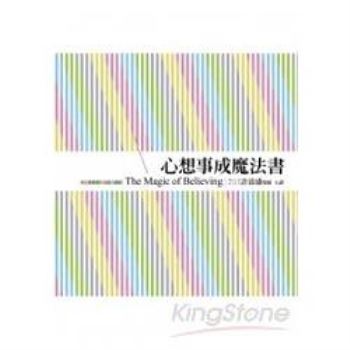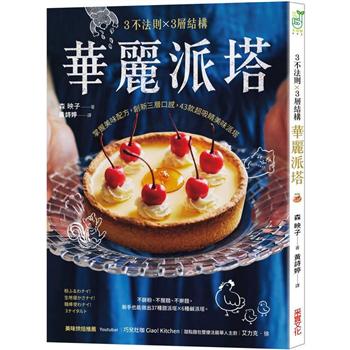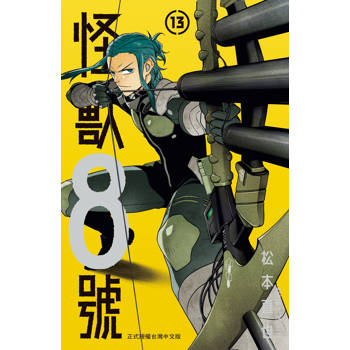作者寺本婉雅為繼河口慧海(1866-1945)之後第二位進入西藏的日本人,《藏蒙旅行記》是寺本婉雅三度出入西藏,於旅途中所記述的日記。這三次入藏之行分別為:第一次(東藏篇),日記始於明治31年(1898年)7月,至明治33年(1900年)4月止;第二次(蒙藏篇),日記始於明治34年(1901年)11月,至明治38年(1905年)8月止;第三次(青海篇),日記始於明治39年(1906年)9月,至明治41年(1908年)2月止。書末另有寺本婉雅於明治41年(1908年)6月及7月兩度登五臺山之行的日記。寺本婉雅於日記中記錄每日行止、觀察,以及對日本拓展西藏勢力的建議,是研究日本在中國邊疆外交情形的重要史料。
當時的西藏和日本同樣信仰佛教,寺本婉雅代表東本願寺以僧人的身分進藏,與西藏僧人討論佛法、研究經典,並代表日本與達賴喇嘛會面。基於傳播佛教的使命感,寺本婉雅積極地建立日本與西藏的友誼橋樑,盼能攜手弘揚佛法。
本書為昭和四十八年日文初版的中譯本,書中記載當時西藏的自然狀況、風土人情、神話傳說、政經制度與寺院制度等豐富資料,書前並附三十幅照片,內含關係人士與寺本婉雅往來書信等珍貴史料。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藏蒙旅行記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藏蒙旅行記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寺本婉雅(1872-1940)
日本西藏學及佛學學者。滋賀縣人。明治三十一年遠赴西藏留學,曾任通譯官,服務於北京公使館師團司令部。明治三十四年入拉薩哲蚌寺研學。明治三十九年第三度入藏,研究喇嘛教,明治四十二年返日。
返日後先後任真宗大谷大學教授、京都帝國大學講師,教授西藏語。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一生專事藏語佛典之研究,對藏語大藏經之研究貢獻甚大。
譯者簡介
洪晨暉
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日本社會語言學、日本文化。
胡稹
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退休教授,現任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學。
※此書為【日本人中國邊疆紀行】系列之一
主編:張明杰(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編:袁向東(廣東技術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館館長,日本成城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寺本婉雅(1872-1940)
日本西藏學及佛學學者。滋賀縣人。明治三十一年遠赴西藏留學,曾任通譯官,服務於北京公使館師團司令部。明治三十四年入拉薩哲蚌寺研學。明治三十九年第三度入藏,研究喇嘛教,明治四十二年返日。
返日後先後任真宗大谷大學教授、京都帝國大學講師,教授西藏語。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一生專事藏語佛典之研究,對藏語大藏經之研究貢獻甚大。
譯者簡介
洪晨暉
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日本社會語言學、日本文化。
胡稹
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退休教授,現任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學。
※此書為【日本人中國邊疆紀行】系列之一
主編:張明杰(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編:袁向東(廣東技術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館館長,日本成城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目錄
主編序/張明杰
導 讀/劉國威
譯 序/洪晨暉、胡稹
緒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猊下撰寫之序文
序言/山口益
值此亡父旅行記出版之際/寺本昌雄
第一章 第一次藏蒙旅行日記【東藏篇】
啟程至上海、北京
自上海至打箭爐
溯長江而上
自打箭爐至巴塘
自巴塘至歸國之前
追記
第二章 第二次藏蒙旅行日記【蒙藏篇】
啟程至北京
自北京至青海
自塔爾寺至拉薩
離開拉薩經由印度回國
離開札什倫布寺
第三章 第三次藏蒙旅行日記【青海篇】
於塔爾寺
自塔爾寺歸國
第四章 五臺山之行
自神戶赴北京
自北京赴五臺山遊記
抵達山西省五臺山
再度登臨五臺山
歸國
附錄
附錄一: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序
附錄二:呈送達賴喇嘛之原稿
附錄三:於日軍總參謀部演講之提綱
附錄四:西藏祕國逸聞(摘錄)
附錄五:追憶青藏高原巡禮
附錄六:我的西藏之旅/A.塔菲爾
附錄七:探訪西藏期間之往來書信(抄)
寺本婉雅年譜
跋/橫地祥原
導 讀/劉國威
譯 序/洪晨暉、胡稹
緒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猊下撰寫之序文
序言/山口益
值此亡父旅行記出版之際/寺本昌雄
第一章 第一次藏蒙旅行日記【東藏篇】
啟程至上海、北京
自上海至打箭爐
溯長江而上
自打箭爐至巴塘
自巴塘至歸國之前
追記
第二章 第二次藏蒙旅行日記【蒙藏篇】
啟程至北京
自北京至青海
自塔爾寺至拉薩
離開拉薩經由印度回國
離開札什倫布寺
第三章 第三次藏蒙旅行日記【青海篇】
於塔爾寺
自塔爾寺歸國
第四章 五臺山之行
自神戶赴北京
自北京赴五臺山遊記
抵達山西省五臺山
再度登臨五臺山
歸國
附錄
附錄一: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序
附錄二:呈送達賴喇嘛之原稿
附錄三:於日軍總參謀部演講之提綱
附錄四:西藏祕國逸聞(摘錄)
附錄五:追憶青藏高原巡禮
附錄六:我的西藏之旅/A.塔菲爾
附錄七:探訪西藏期間之往來書信(抄)
寺本婉雅年譜
跋/橫地祥原
序
導讀
劉國威(國立故宮研究院書畫文獻處研究員兼科長)
雖身為藏學領域的研究者,然我因日文素養不佳,對日本藏學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不熟悉,然而對此書作者寺本婉雅(1872-1940)確是久聞其名,只是過去也僅知道他是日本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初代藏學研究學者,任教於大谷大學,並有藏文文法的相關著作。以前在閱讀印順導師的著作時,當導師探討印度佛教史的相關議題時,常引用寺本婉雅所日譯的覺囊派祖師達拉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名著《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byung),而在討論龍樹的中觀見地時,也常引用寺本譯校的《中論無畏疏--梵漢独対校西蔵文和訳》,所以很早就對此位日本學者有印象。但直到此次有機會應邀撰寫短篇導讀,真正讀過他在清末那段詭譎多變的時期多次出入北京、蒙古、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回憶記錄,方對其生平有較深入的瞭解。
如果在網路查詢寺本婉雅的生平,中文訊息基本上都抄襲自《佛光大辭典》中的簡短記錄:「日本西藏學及佛學學者。屬日本真宗大谷派。滋賀縣蒲生郡鏡山村人。明治二十八年(1895)九月入真宗大學,三十一(1898)年六月退學後遠赴西藏留學,三十二年(1899)返日。翌年八月擔任通譯官,服務於北京公使館師團司令部。三十四年(1901)復被小村外務大臣派至西藏留學,十月,入拉薩哲蚌寺研學。於三十八年(1905)五月入札什倫布之僧院,十月,經由印度歸國。三十九年(1906)四月,第三度入藏,研究喇嘛教,四十二年(1909)始返日。返日後,於大正四年(1915)二月出任真宗大谷大學教授,同年九月兼任京都帝國大學講師,講授西藏語。昭和十五年(1940)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九。其一生專事藏語佛典之研究,對藏語大藏經之研究貢獻甚大。著有:西藏古代神話十萬白龍、于闐國史、西藏語文法、新龍樹傳の研究等。」這段記載實譯自《大谷學報》第22卷第1期,刊行於二戰時期的1941年,寺本教授剛於前一年過世,所以是大谷大學基於紀念其人所撰的簡傳。如果看過這部《藏蒙旅行記》,就知道這段簡傳所記錄的內容誤差頗大,或許是「為賢者隱」;也或許是當時二戰時期仍屬軍政府主導一切的非常時期,由於日本政府對西藏的政策轉變,寺本婉雅所屬的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在二十年前即已受到軍政府警告不得再與達賴喇嘛保持關係,所以大谷大學必須隱去此段事蹟;此外,這本《藏蒙旅行記》其實是到1974年方由寺本婉雅之子整理父親遺著而出版,據其子所說:他也是看到這些日記方知其父當年這般「輝煌」的事蹟,所以也頗可能1940年代那時的大谷大學也已不清楚三十餘年前的往事。從此書所記內容可知,以進入西藏核心地區而言(指拉薩與日喀則一帶的衛藏地區,或今日的西藏自治區),寺本婉雅僅第二次赴藏時成功進入藏區,但他在拉薩與日喀則一帶也僅待了不到三個月(1905年五月抵達拉薩,1905年8月底已到印度加爾各答),因此說他到哲蚌寺與札什倫布寺參學實有些過譽,他在西藏語文及文化方面的知識應主要是入藏前在塔爾寺待的近兩年期間而打下的基礎(1903年2月至1905年2月)。1899年他第一次欲入藏,打算從四川打箭爐一帶進入,但受當地藏人所阻未成;1906年所謂第三次入藏也僅是為了到塔爾寺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會面,之後1908年在五台山與北京與十三世達賴多次見面,並安排西本願寺住持大谷尊由與十三世達賴在五台山秘密會面;1908年11月十三世達賴赴北京謁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不久光緒與慈禧先後過世,達賴即欲離京返藏,據此書記載,寺本婉雅此時實積極遊說十三世達賴訪日,最終未成;1909年返日後就未再赴中國,也不再介入西藏事務,至1915年方成大谷大學專任教授。因此《大谷學報》的這段記錄實或有意或無意的隱瞞簡化了寺本教授的「三次入藏」。
不可否認寺本婉雅的入藏帶有政治目的,其實當時入藏欲與達賴政府結交的各國人士不免都有政治拉攏的動機,如一般常提到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的所謂俄國間諜喇嘛阿旺‧洛桑‧德爾智(Agvan Dorzhiev, ngag dbang blo bzang rdo rje, 1854-1938),作為十三世達賴的政治顧問,他確實是主張西藏與俄國聯合的核心人物,但一般談論這段歷史的人也往往忽略掉他身為布里雅特蒙古喇嘛的出身,對佛教實有深刻信仰,德爾智喇嘛也藉其影響力對其家鄉及鄰近蒙古文化地區的佛教促進重大發展;被尊為「台灣藏學研究之父」的歐陽無畏先生(1913-1991),當年入藏的初始動機也是基於「經略邊疆」愛國熱忱,即使入藏後真正對藏傳佛教產生興趣,入哲蚌寺出家為僧,但同時也為國民政府做工作。因此,寺本婉雅身為明治維新後的淨土真宗東本願寺大谷派的弘教師,其愛國與弘教雙方面的熱忱自不在話下,從此書內容可不斷看到他的這類看法。
由於寺本在北京、青海一帶所接觸的大多是滿蒙藏的上層人士,所以他所見聞的經驗頗有別於他之前的入藏的河口慧海(1866-1945)與之後的多田等觀(1890-1967),這兩位雖也都與十三世達賴有密切交流,但活動區域主要都是拉薩一帶的藏區,不像寺本主要在青海、蒙谷、北京等地。
寺本婉雅當時欲建立日本與西藏的外交關係,其政治作為與後續影響已有幾位大陸學者詳細論述,不用我於此再加贅言,由於個人主要研究佛教歷史文獻,因此對相關資料較感興趣,於此就書中所提部分獨特內容進行介紹,這或許是一般讀者未注意到訊息。
一、資福寺與黃寺所請《甘珠爾》
寺本婉雅在書中多處提及,他研究藏傳佛教的其中之一動機就是對藏文大藏經的蒐集整理分析,因此頗留心於此。1900年八國聯軍戰事後,「是年秋,余接受政府命令於北京從軍,開始與攝政王醇親王以及洵、濤兩親王及慶親王等交往,略為國家效力。同年九月十七日獲特別恩准,得以在處理軍務之同時,自由研究軍隊之精神教育與西藏語。為此進入安定門外之黃寺與資福院,一面鑽研喇嘛教,一面做進藏之準備。」他看到寺院內竟然有藏文的藏經文獻《甘珠爾》,大為驚喜。「因而當即與院內住持喇嘛聯繫,終得以將其買下。之後余以榮獲特別恩准,得以研究藏語之因緣將其運回國內。此事終達天聽,命余獻其部分經典於宮內,並製作藏文大藏經目錄。余遵命恭敬奉獻紺紙金泥之《甘殊爾》部與朱印字版之《甘殊爾》部及雜部。嗣後由宮中轉託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保存。而其餘部分則贈予真宗大學圖書館。」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朱印字版之甘珠爾部」即康熙27年(1688)在北京雕版刊印的北京版《甘珠爾》,後藏於「真宗大學圖書館」(即後來的大谷大學),1958年由鈴木學術財團將之影印出版,在數位資訊未發展的年代,日本翻印的此套《北京版西藏大藏經》,是學者研究藏文經典的必備參考。
而另一套,則是:「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所藏部分係余自黃寺購買,乃明太宗為報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將西藏原本翻刻刊行之複製品,附有永樂八年(1410)三月九日之《御製藏經贊》。之後經一百九十六年,永樂版得以再版,有『大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吉日奉旨重刊印造』序文。此時僅有《甘珠爾》部,而《丹珠爾》部尚未出版。除此萬曆版《甘殊爾》部外,尚有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御製抄寫之紺紙金泥《般若經》、《律師戒本經》等,以及其他數部抄經等,總共贈出二百九十三函。」據寺本教授的此段記載,此部即為萬曆版《甘殊爾》,萬曆版雖是永樂版的覆刻,但並不全同,永樂版現僅拉薩色拉寺尚存一部,但學界尋找萬曆版多年,僅數年前於波蘭某城堡偶然發現三十餘函,這是二戰末期德國納粹政府遷移國家重要典藏文物所致,這批不全經函可能也是八國聯軍時期的戰利品。至於明武宗時期的藏文泥金寫本佛經,更是至今未曾見類似文物,明武宗喜好藏傳佛教,因此宮內有不少相關御製器物,如故宮院藏一批正德年間上有梵藏文咒字的瓷器,其他典藏單位也收有正德年間的宮廷御製唐卡,然此時期的御製藏文佛典確是未見。然而不幸的是,寺本教授所收這批典藏於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的珍貴典籍,在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中全遭焚毀,現已不存。
二、參與清廷歲末法事
書中記載,1901年1月16日至20日(光緒27年12月7日至11日)期間,寺本參與在養心殿舉辦的佛教法事:「此五日間,紫禁城內養心殿舉行每年一度之法事。當日雍和宮一百零八名喇嘛自凌晨五時即在養心殿誦讀《長壽經》、《白傘蓋經》等。皇帝於初九正午駕臨,拈香禮佛,祈求萬福,諸王百官及蒙古王均參加。其他時日則由諸王輪流代替皇帝禮佛。」
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於中正殿設立掌管宮中藏傳佛教事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自此每年定期在殿內各佛堂舉辦佛事活動。據故宮所藏清宮檔案所述,每年十二月初九,中正殿舉辦遣送白傘蓋大迴避巴陵(此為梵文Balin的音譯詞,即食子供品)的除障法會;皇帝依制須親至中正殿壇城前拈香,向駐京各呼圖克圖供茶,並發放布施。養心殿有皇帝內廷的佛殿,因此中正殿法事亦會在該處舉辦;由於寺本與雍和宮住持阿嘉呼圖克圖(1871-1909)交好,因此有此機會入養心殿參加法事。
三、十三世達賴喇嘛與阿嘉呼圖克圖之齟齬
寺本到北京後,即向雍和宮住持第五世阿嘉呼圖克圖學習藏語,建立良好關係,甚至在八國聯軍戰役後應其邀請,阿嘉親自前往日本訪問,並安排面見日本天皇。
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年因英軍入侵,出逃拉薩後,先至蒙古庫倫,後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不和,1906年抵達塔爾寺。寺本在該年十月於塔爾寺謁見十三世達賴,書中也明白記載十三世達賴與阿嘉呼圖克圖間發生不合的經過,此事在二人的正式傳記中均未明述,但可在故宮院藏清宮檔案中得到印證: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二日,西寧辦事大臣慶恕(1840-1919)上奏「達賴喇嘛來文以塔爾寺阿嘉呼圖不守清規請予斥革」,達賴控告理由多項,顯示兩人不和已非短期(寺本所述事蹟已是三年前的紛爭,此時寺本已然返日),甚至兩個月後阿嘉因病圓寂,其弟子亦傳言是達賴下咒所致,直至慶恕介入調查,糾其誣告之罪,且達賴已啟程返回拉薩,此事方息。
書中提到宗喀巴出生於永樂十九年(1417),我們現在知道這當然是差了一甲子的誤解,但此錯誤無可厚非,因寺本引用的是清代漢文文獻,乾隆皇帝就是如此說法;此外,他敘述的乾隆朝漢文藏經與滿文藏經的編纂年代也都有些許錯誤,這也無傷大雅,在那個年代對這些文本的學術考證才剛起步。不過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寺本教授重視的是佛教藏經文獻,對西藏佛教的宗派其實並不重視。他在塔爾寺時,對喇嘛的辯經教育並未深入理解,興趣不大,評價也非正面;在江孜附近遇到寧瑪派的在家上師時,縱然周遭藏人對這位上師甚為恭敬,但寺本仍依其外貌判定,給予頗負面的評價。
這類對西藏佛教的偏見或誤解縱有其時代的限制,卻也有個人的民族主義與文化本位偏見,這從寺本教授後來的學術著作也略見端倪,他著重於藏文佛教經論研究,像是翻譯藏文的《阿彌陀經》(這當然與其淨土真宗的信仰背景有關)、《唯識三十頌》、《中論無畏疏》、《異部宗輪論》等,基本上都是藏經文獻;他雖曾與多位格魯派高僧學習,也在寺院生活一段時間,但他對格魯派的宗派內涵看來興趣不大,所以未見其曾引述分析格魯派祖師的著作,遑論他派。
此導讀短文僅是一些心得分享,閱讀過程收穫不少,一方面可與同時期其他入藏的回憶錄相比,從中見其特色,另一方面他所記錄的蒙藏地區史地資料,經百餘年變遷後,許多現已不存,從其記錄可見最後形影,如書中所錄天津的海光寺,北京的旃檀寺、資福寺、闡福寺等,在八國聯軍後均毀,至今不存。其描述除有助考證外,使滄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不甚唏噓。
劉國威(國立故宮研究院書畫文獻處研究員兼科長)
雖身為藏學領域的研究者,然我因日文素養不佳,對日本藏學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不熟悉,然而對此書作者寺本婉雅(1872-1940)確是久聞其名,只是過去也僅知道他是日本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初代藏學研究學者,任教於大谷大學,並有藏文文法的相關著作。以前在閱讀印順導師的著作時,當導師探討印度佛教史的相關議題時,常引用寺本婉雅所日譯的覺囊派祖師達拉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名著《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byung),而在討論龍樹的中觀見地時,也常引用寺本譯校的《中論無畏疏--梵漢独対校西蔵文和訳》,所以很早就對此位日本學者有印象。但直到此次有機會應邀撰寫短篇導讀,真正讀過他在清末那段詭譎多變的時期多次出入北京、蒙古、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回憶記錄,方對其生平有較深入的瞭解。
如果在網路查詢寺本婉雅的生平,中文訊息基本上都抄襲自《佛光大辭典》中的簡短記錄:「日本西藏學及佛學學者。屬日本真宗大谷派。滋賀縣蒲生郡鏡山村人。明治二十八年(1895)九月入真宗大學,三十一(1898)年六月退學後遠赴西藏留學,三十二年(1899)返日。翌年八月擔任通譯官,服務於北京公使館師團司令部。三十四年(1901)復被小村外務大臣派至西藏留學,十月,入拉薩哲蚌寺研學。於三十八年(1905)五月入札什倫布之僧院,十月,經由印度歸國。三十九年(1906)四月,第三度入藏,研究喇嘛教,四十二年(1909)始返日。返日後,於大正四年(1915)二月出任真宗大谷大學教授,同年九月兼任京都帝國大學講師,講授西藏語。昭和十五年(1940)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九。其一生專事藏語佛典之研究,對藏語大藏經之研究貢獻甚大。著有:西藏古代神話十萬白龍、于闐國史、西藏語文法、新龍樹傳の研究等。」這段記載實譯自《大谷學報》第22卷第1期,刊行於二戰時期的1941年,寺本教授剛於前一年過世,所以是大谷大學基於紀念其人所撰的簡傳。如果看過這部《藏蒙旅行記》,就知道這段簡傳所記錄的內容誤差頗大,或許是「為賢者隱」;也或許是當時二戰時期仍屬軍政府主導一切的非常時期,由於日本政府對西藏的政策轉變,寺本婉雅所屬的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在二十年前即已受到軍政府警告不得再與達賴喇嘛保持關係,所以大谷大學必須隱去此段事蹟;此外,這本《藏蒙旅行記》其實是到1974年方由寺本婉雅之子整理父親遺著而出版,據其子所說:他也是看到這些日記方知其父當年這般「輝煌」的事蹟,所以也頗可能1940年代那時的大谷大學也已不清楚三十餘年前的往事。從此書所記內容可知,以進入西藏核心地區而言(指拉薩與日喀則一帶的衛藏地區,或今日的西藏自治區),寺本婉雅僅第二次赴藏時成功進入藏區,但他在拉薩與日喀則一帶也僅待了不到三個月(1905年五月抵達拉薩,1905年8月底已到印度加爾各答),因此說他到哲蚌寺與札什倫布寺參學實有些過譽,他在西藏語文及文化方面的知識應主要是入藏前在塔爾寺待的近兩年期間而打下的基礎(1903年2月至1905年2月)。1899年他第一次欲入藏,打算從四川打箭爐一帶進入,但受當地藏人所阻未成;1906年所謂第三次入藏也僅是為了到塔爾寺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會面,之後1908年在五台山與北京與十三世達賴多次見面,並安排西本願寺住持大谷尊由與十三世達賴在五台山秘密會面;1908年11月十三世達賴赴北京謁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不久光緒與慈禧先後過世,達賴即欲離京返藏,據此書記載,寺本婉雅此時實積極遊說十三世達賴訪日,最終未成;1909年返日後就未再赴中國,也不再介入西藏事務,至1915年方成大谷大學專任教授。因此《大谷學報》的這段記錄實或有意或無意的隱瞞簡化了寺本教授的「三次入藏」。
不可否認寺本婉雅的入藏帶有政治目的,其實當時入藏欲與達賴政府結交的各國人士不免都有政治拉攏的動機,如一般常提到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的所謂俄國間諜喇嘛阿旺‧洛桑‧德爾智(Agvan Dorzhiev, ngag dbang blo bzang rdo rje, 1854-1938),作為十三世達賴的政治顧問,他確實是主張西藏與俄國聯合的核心人物,但一般談論這段歷史的人也往往忽略掉他身為布里雅特蒙古喇嘛的出身,對佛教實有深刻信仰,德爾智喇嘛也藉其影響力對其家鄉及鄰近蒙古文化地區的佛教促進重大發展;被尊為「台灣藏學研究之父」的歐陽無畏先生(1913-1991),當年入藏的初始動機也是基於「經略邊疆」愛國熱忱,即使入藏後真正對藏傳佛教產生興趣,入哲蚌寺出家為僧,但同時也為國民政府做工作。因此,寺本婉雅身為明治維新後的淨土真宗東本願寺大谷派的弘教師,其愛國與弘教雙方面的熱忱自不在話下,從此書內容可不斷看到他的這類看法。
由於寺本在北京、青海一帶所接觸的大多是滿蒙藏的上層人士,所以他所見聞的經驗頗有別於他之前的入藏的河口慧海(1866-1945)與之後的多田等觀(1890-1967),這兩位雖也都與十三世達賴有密切交流,但活動區域主要都是拉薩一帶的藏區,不像寺本主要在青海、蒙谷、北京等地。
寺本婉雅當時欲建立日本與西藏的外交關係,其政治作為與後續影響已有幾位大陸學者詳細論述,不用我於此再加贅言,由於個人主要研究佛教歷史文獻,因此對相關資料較感興趣,於此就書中所提部分獨特內容進行介紹,這或許是一般讀者未注意到訊息。
一、資福寺與黃寺所請《甘珠爾》
寺本婉雅在書中多處提及,他研究藏傳佛教的其中之一動機就是對藏文大藏經的蒐集整理分析,因此頗留心於此。1900年八國聯軍戰事後,「是年秋,余接受政府命令於北京從軍,開始與攝政王醇親王以及洵、濤兩親王及慶親王等交往,略為國家效力。同年九月十七日獲特別恩准,得以在處理軍務之同時,自由研究軍隊之精神教育與西藏語。為此進入安定門外之黃寺與資福院,一面鑽研喇嘛教,一面做進藏之準備。」他看到寺院內竟然有藏文的藏經文獻《甘珠爾》,大為驚喜。「因而當即與院內住持喇嘛聯繫,終得以將其買下。之後余以榮獲特別恩准,得以研究藏語之因緣將其運回國內。此事終達天聽,命余獻其部分經典於宮內,並製作藏文大藏經目錄。余遵命恭敬奉獻紺紙金泥之《甘殊爾》部與朱印字版之《甘殊爾》部及雜部。嗣後由宮中轉託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保存。而其餘部分則贈予真宗大學圖書館。」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朱印字版之甘珠爾部」即康熙27年(1688)在北京雕版刊印的北京版《甘珠爾》,後藏於「真宗大學圖書館」(即後來的大谷大學),1958年由鈴木學術財團將之影印出版,在數位資訊未發展的年代,日本翻印的此套《北京版西藏大藏經》,是學者研究藏文經典的必備參考。
而另一套,則是:「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所藏部分係余自黃寺購買,乃明太宗為報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將西藏原本翻刻刊行之複製品,附有永樂八年(1410)三月九日之《御製藏經贊》。之後經一百九十六年,永樂版得以再版,有『大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吉日奉旨重刊印造』序文。此時僅有《甘珠爾》部,而《丹珠爾》部尚未出版。除此萬曆版《甘殊爾》部外,尚有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御製抄寫之紺紙金泥《般若經》、《律師戒本經》等,以及其他數部抄經等,總共贈出二百九十三函。」據寺本教授的此段記載,此部即為萬曆版《甘殊爾》,萬曆版雖是永樂版的覆刻,但並不全同,永樂版現僅拉薩色拉寺尚存一部,但學界尋找萬曆版多年,僅數年前於波蘭某城堡偶然發現三十餘函,這是二戰末期德國納粹政府遷移國家重要典藏文物所致,這批不全經函可能也是八國聯軍時期的戰利品。至於明武宗時期的藏文泥金寫本佛經,更是至今未曾見類似文物,明武宗喜好藏傳佛教,因此宮內有不少相關御製器物,如故宮院藏一批正德年間上有梵藏文咒字的瓷器,其他典藏單位也收有正德年間的宮廷御製唐卡,然此時期的御製藏文佛典確是未見。然而不幸的是,寺本教授所收這批典藏於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的珍貴典籍,在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中全遭焚毀,現已不存。
二、參與清廷歲末法事
書中記載,1901年1月16日至20日(光緒27年12月7日至11日)期間,寺本參與在養心殿舉辦的佛教法事:「此五日間,紫禁城內養心殿舉行每年一度之法事。當日雍和宮一百零八名喇嘛自凌晨五時即在養心殿誦讀《長壽經》、《白傘蓋經》等。皇帝於初九正午駕臨,拈香禮佛,祈求萬福,諸王百官及蒙古王均參加。其他時日則由諸王輪流代替皇帝禮佛。」
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於中正殿設立掌管宮中藏傳佛教事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自此每年定期在殿內各佛堂舉辦佛事活動。據故宮所藏清宮檔案所述,每年十二月初九,中正殿舉辦遣送白傘蓋大迴避巴陵(此為梵文Balin的音譯詞,即食子供品)的除障法會;皇帝依制須親至中正殿壇城前拈香,向駐京各呼圖克圖供茶,並發放布施。養心殿有皇帝內廷的佛殿,因此中正殿法事亦會在該處舉辦;由於寺本與雍和宮住持阿嘉呼圖克圖(1871-1909)交好,因此有此機會入養心殿參加法事。
三、十三世達賴喇嘛與阿嘉呼圖克圖之齟齬
寺本到北京後,即向雍和宮住持第五世阿嘉呼圖克圖學習藏語,建立良好關係,甚至在八國聯軍戰役後應其邀請,阿嘉親自前往日本訪問,並安排面見日本天皇。
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年因英軍入侵,出逃拉薩後,先至蒙古庫倫,後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不和,1906年抵達塔爾寺。寺本在該年十月於塔爾寺謁見十三世達賴,書中也明白記載十三世達賴與阿嘉呼圖克圖間發生不合的經過,此事在二人的正式傳記中均未明述,但可在故宮院藏清宮檔案中得到印證: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二日,西寧辦事大臣慶恕(1840-1919)上奏「達賴喇嘛來文以塔爾寺阿嘉呼圖不守清規請予斥革」,達賴控告理由多項,顯示兩人不和已非短期(寺本所述事蹟已是三年前的紛爭,此時寺本已然返日),甚至兩個月後阿嘉因病圓寂,其弟子亦傳言是達賴下咒所致,直至慶恕介入調查,糾其誣告之罪,且達賴已啟程返回拉薩,此事方息。
書中提到宗喀巴出生於永樂十九年(1417),我們現在知道這當然是差了一甲子的誤解,但此錯誤無可厚非,因寺本引用的是清代漢文文獻,乾隆皇帝就是如此說法;此外,他敘述的乾隆朝漢文藏經與滿文藏經的編纂年代也都有些許錯誤,這也無傷大雅,在那個年代對這些文本的學術考證才剛起步。不過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寺本教授重視的是佛教藏經文獻,對西藏佛教的宗派其實並不重視。他在塔爾寺時,對喇嘛的辯經教育並未深入理解,興趣不大,評價也非正面;在江孜附近遇到寧瑪派的在家上師時,縱然周遭藏人對這位上師甚為恭敬,但寺本仍依其外貌判定,給予頗負面的評價。
這類對西藏佛教的偏見或誤解縱有其時代的限制,卻也有個人的民族主義與文化本位偏見,這從寺本教授後來的學術著作也略見端倪,他著重於藏文佛教經論研究,像是翻譯藏文的《阿彌陀經》(這當然與其淨土真宗的信仰背景有關)、《唯識三十頌》、《中論無畏疏》、《異部宗輪論》等,基本上都是藏經文獻;他雖曾與多位格魯派高僧學習,也在寺院生活一段時間,但他對格魯派的宗派內涵看來興趣不大,所以未見其曾引述分析格魯派祖師的著作,遑論他派。
此導讀短文僅是一些心得分享,閱讀過程收穫不少,一方面可與同時期其他入藏的回憶錄相比,從中見其特色,另一方面他所記錄的蒙藏地區史地資料,經百餘年變遷後,許多現已不存,從其記錄可見最後形影,如書中所錄天津的海光寺,北京的旃檀寺、資福寺、闡福寺等,在八國聯軍後均毀,至今不存。其描述除有助考證外,使滄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不甚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