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生物氣候學家對地球破壞最真實的反思;
一則結合先人智慧、冒險、愛情的全球反人類預言……
一則結合先人智慧、冒險、愛情的全球反人類預言……
創紀錄的異常高溫,莫名的疾病傳染;
超越演化機制、急速生長的巨大植物……
一群遭軍方隔離在地下十三層碉堡的人們,
經過二十天後不得不回到地面,卻發現整個巴黎竟宛如空城——
沒有人、沒有救援,根本不該出現於此的熱帶植物鋪天蓋地,甚至主動攻擊人類;
而他們獲救的唯一希望,是登上艾菲爾鐵塔,發出求救訊息……
身為專門開發熱帶林木的集團總裁,亞歷山大•格蘭深信開發熱帶雨林是人類勢必付出的代價與犧牲;面對向他抗議的環保團體及科學家,格蘭絲毫沒有動搖——然而他不會想到,人類已經將地球推向臨界點。自然的反撲,正式開始了。
起初是不明傳染病全球爆發。對此,人類毫無招架之力,死亡人數急速攀升;格蘭欲開發的雨林區被查證為傳染源頭,於是這名總裁和科學家一行人,以及遭到傳染病滅村、唯一生還的男孩,被法國軍隊軟禁於地下碉堡,協助調查原因。
同時,在地表,全球氣溫升高至異常溫度,這怪異的變化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影響——同時引發水災、土石流、蟲害,各種災難接踵而至。最可怕的是,因為潮濕如熱帶雨林的氣候,各類植物凶猛地生長,幾乎吞噬每一寸地面。它們像是獲得某種源源不絕的精力,將人類逼到角落。
原本堅不可摧的地下碉堡毫無原因與外界失聯,地下水穿越厚牆,入侵基地,逼得眾人不得不回到地面,卻發現巴黎已被全面棄守——格蘭與僅存的同伴在成為蠻荒叢林的巴黎尋找一線生機,但眾人心裡都很清楚,他們可能是這塊區域僅存的人類。地球已經將他們的主控權奪走,一點機會也不留。
為了人在紐約的女兒,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格蘭誓死要回到地球的另一端;然而,神祕的夢魘、出現古怪行為的男孩、美麗的女科學家,加上異常的環境和主動攻擊人類的植物,幾乎將他逼至瘋狂——難道地球走上毀滅之路,真的與他的基因改造實驗脫不了關係?
人類因驕傲自大,擅自將自己擺上食物鏈的頂端,並不顧後果,為所欲為。但當這般狂妄行為超越了界線,大地之母將不再姑息。祂將帶著怒意覺醒,給予人類應得的懲罰……
當人變成一種毫無益處的害蟲,清理禍害的時間就到了……
名人推薦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李偉文
科普作家 張東君
泛科學總編輯 鄭國威
香港科幻作家 譚劍
共同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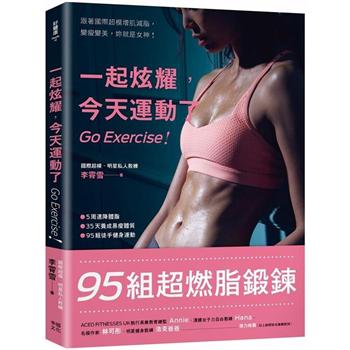









原文書名「蓋亞」《Gaïa》,蓋婭是古希臘大地女神的名字,1970年代,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蓋亞假說」(Gaia hypothesis),是指在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之下,能使得地球適合生命持續的生存與發展,陸生生物過程和自然過程共同作用產生並調節有益於生命繼續生存的環境。(節錄於維基百科)。 簡單的說,就是強調生物多樣性對地球的重要性。 本書的故事大致是這樣: 有天,地球突然從巴西熱帶雨林深處出現某種傳播快速的致命傳染病,於是政府與軍方火速地隔離可能最早感染的人,將他們安置在巴黎近郊一處處於地下十三層碉堡的軍事基地,打算從他們身上找出病源並製造抗體,二十天後由於碉堡發生巨變,他們為了逃生不得不回到地面上,卻驚覺整座巴黎竟宛如空城,以及處處可見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熱帶沼澤,在巴黎街頭有非洲牛鈴的獸奔,塞納河上處處可見熱帶的巨型鱷魚.....。 故事確實很精彩,作者對於受到大自然反撲的地球場景也描寫的非常傳神,當然如果可以改編成電影,絕對會比原著來得吸睛。 主角格蘭是亞馬遜河開發商的老闆,是個為了利益不惜毀掉整座森林的典型資本家,用強硬的態度面對環保團體與生態學者,運用政商勾結攫取不當利益,甚至為了利益不惜犧牲捕捉面臨絕種邊緣的各種動物,更惡劣的是他的公司還大量研究並種植基因改造的各種植物.... 很諷刺的是格蘭所開發的亞馬遜河流域剛好是第一批傳染病蔓延的地方,疑似感染的他也被軍方隔離。 世界末日的作品相當多,有外星人、變種人、突變的其他動動、隕石彗星、天然災害、致命病毒、核子戰爭.....然而本書的世界末日的成因竟然不是其他作品曾經提到的,作者的想像力相當豐富,居然可以想像出另類的世界末日。 基於閱讀道德,我不能曝雷破梗,只能說作者用了一種大家可能沒有想像到的人類末日來鋪陳故事。 生物多樣性的危機以及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是本書撰寫的重點,作者用想像力編織出人類為惡之後的苦果,倘若地球上因為突變而出現更高等的生物,倘若人類變成高等生物眼中的「家畜」或「害蟲」,倘若人類被更高等生物當成食物繁殖..... 作者有很強烈的主觀意識形態,所以書中出現了很大篇幅接近說教式的對話,作者也安排了格蘭這個破壞環境的要角當成主角,讓他苦嚐過度開發與破壞的所有後果,相當具有警世以及諷刺的意味。 人類的末日不等同於地球末日,故事中人類慘遭滅絕反而讓地球的環境變得更好,難怪在烏克蘭的車若比克核災區,二十幾年後竟然成為生態樂園,各類動植物生活繁衍地欣欣向榮,原來這個地球的最大甚至唯一汙染源是我們人類,為什麼我會提車若比呢?因為整本書的閱讀過程中,車若比的世界與遭遇的畫面始終浮現在我腦海中。 自私的人類始終認為自己是地球食物鏈的頂端,完全不顧其他生物滅絕的後果,作者想要藉由這個故事來提醒一旦人類的狂妄與貪婪超越了自然界線,大地之母蓋亞將不再姑息,祂將帶著怒意覺醒,給予人類應得的懲罰,而且還是最沉重的逞罰。 說了這本書精彩的部分當然也得述說一下本書比較不精彩的部分,一是說教意味稍微濃厚,二是某些關於科技的部分有點交代不清楚(這也許是我個人的科普素養不足吧),三是讀者老是陷入世界滅絕的原因的追蹤而略嫌枯燥,四是故事結局太過憂傷讓人喘不過氣來。 故事終了,格蘭面對了生為人類最殘酷的極刑,這極刑不是死亡、不是病痛、而是一切陷入寂靜....這或許是地球原本應該有的面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