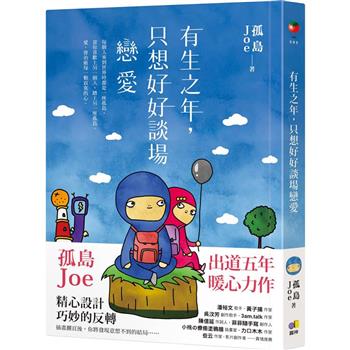哪怕你不相信故事,故事也相信你
哪怕你無視命運,或想像,他們都看著你,
並將你編織入內。
哪怕你無視命運,或想像,他們都看著你,
並將你編織入內。
應該告訴每個進入本書世界的人:你離開時的大小會跟進來時不一樣。
--娥蘇拉.勒瑰恩,奇幻經典「地海」系列作者
他覺得自己是透明的。
在人生的大半時間,他居無定所,時常覺得不被看見;他沒有相信的事物,也沒有事物相信他。他覺得自己的靈魂沒有顏色。
直到認識了那個女孩。
那是他生命中色彩最濃烈的一刻。
當他在仲夏那日徒步前往她所在的神秘大宅,與她結婚,從未想過自己會從此成為偉大歷史其中一個章節。女孩住在一個沒有地址的大宅,裡頭充滿奧妙奇異的事物――迷宮般的走廊、預言未來的紙牌、水塘裡的鱒魚爺爺、舊照片中若隱若現的精靈,和一個代代流傳的家族預言。他一直認為自己是誤打誤撞成為他們的一員,卻不知道他與女孩的邂逅並非偶然。在好久好久以前,他就注定要推開這扇大門……
「因為這是個故事。而故事是會成真的。」
「但我不知道這是故事。」
「置身故事裡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沒有例外。但故事就是存在。」
得獎記錄
美國史詩級奇幻鉅著
世界奇幻獎、創神獎得主
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世界奇幻獎終身成就獎
各界好評
跟莎士比亞、路易士卡羅一樣神奇,渾然天成……這是七十年來我最喜歡的一本書。――哈洛•卜倫,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西方正典》作者
若費茲傑羅在世,一定會對克勞利的文筆羨慕不已。――麥可•德達,普立茲獎得主,華盛頓郵報書評
美國的一段祕密歷史,張力十足的愛情故事,下一個世紀的啟示與觀點,想像力淋漓盡致的專著……至今最棒的美國奇幻小說。――華盛頓郵報
足以媲美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和俄國小說家納博可夫的《Ada》。――波士頓評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