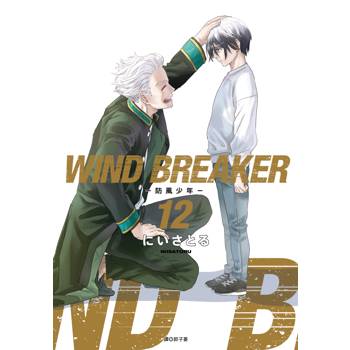前言:觀看的藝術
我用簡單的定義區分微縮品和純粹小型的東西:微縮品必須是較大物件的縮小版本,或可導向較大物件,而且本身經過有意識的創造。它也履行了微縮品的職責──解釋概念、解決謎題、喚起記憶。作為紀念品的建築物鑰匙圈就符合條件,雖然不太有趣;迷你琴酒也是;福斯金龜車則不算,史上最小的頂針也不是,不管這些東西的收藏家有多熱中都一樣。迷你吧和小型玩賞犬在合格邊緣,盆栽藝術也是,其中的「小」透過刻意修剪栽種而創造出來。沒有人會對五歲小孩用塑膠做成的玩具貴賓狗美勞作品感興趣。你還可以訂定更多規則,限定長寬高,就像航空公司限制手提行李大小那樣,但很快就會發現,微縮品在我們的世界占據的空間足以創造出一個與生俱來的位置:只要看到,你就認得出來,而且過了一會兒,你的眼中可能就容不下其他東西了。
微縮世界擁抱控制。我們童年時期喜愛的玩具在年幼時植下稀有的力量,賦予我們成年人擁有的力量,甚或是巨人的力量。玩具車和娃娃和塑膠維修工具箱不只可操控在手中,更讓我們成為征服者。除非持續玩耍到成年,否則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再這樣統治世界。那些在小屋和閣樓裡戴著火車駕駛帽玩模型的男人!他們的妻子早就跑了。然而他們的妻子也瘋狂著迷於瓷器、小小玩具家族、刺蝟毛線娃娃收藏品、毛氈做成的寶物。誰會為這些人發聲?我們埋首在自己創造出的小型宇宙,把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這就是本書的核心。有些人蹲伏身子細看微小處,彷彿整個世界都仰賴於此,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的世界確實仰賴於此。
微縮世界不只是聚集微縮品的地方,而是充滿活力又有深厚根源的生態系統。微縮化的心理學是一門引人入勝的學科,雖然這個領域本身十分微小,卻暗藏了錯綜複雜的道理。我對本書各章的構想也類似。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已觀察到微縮品可能徹底翻轉我們理解客體的方式:我們不再零散逐步地檢視它,因此或許可以慢慢發展出對全貌的理解,因見其整體而秒懂──用他所謂的「可知向度」取代「可感向度」。這是一股人性化的驅力,這是我們何以替具侵略性的大型建築物取親切幽默又使之縮小的名字:占據倫敦市中心的建築物被取名為小黃瓜、對講機、起司刨刀──交替使用可食用與可手持的東西──這些不只對我們來說是有趣的綽號,對建築物的擁有者和建造者也很有用,把本來可能令人反感又具威脅性的東西,馬上轉變得較友好又看似小了點。
沒有了模型,我們很難理解事物。超過兩百年來,模型都是博物館展示品的一部分,而且小孩子第一次參觀博物館的經驗之所以難忘,常常就是因為與這些模型相遇。玩賞小小事物的欲望轉變為創造小小事物的欲望,這兩個階段都回應了人類對掌控的需求。我們活在巨大而憂傷的世界,僅只是控制這世界中縮小後那微小的一部分,就有助於恢復秩序感與價值感。我們可能沒有參加世界盃足球賽或萊德盃高爾夫球賽,但永遠都可以玩桌上足球和迷你高爾夫。無人機不就是現代的遙控模型飛機嗎?地球儀不就濃縮了我們對地形的所有理解嗎?
我認為,少了業餘愛好者,我們也將很難理解事物。這世界因棚屋和閣樓裡的熱忱及獨創性而進步(蒸汽引擎、個人電腦),擁有怡品電子會員卡和早期電路板的微縮創作者幾乎都是業餘者。在世人懂得欣賞與珍惜他們的作品之前,他們只感受到內在的熱情與家人的反對。本書意圖將這份讚賞加倍放大,我們應該留意,業餘者的英文amateur源於拉丁文amare,意思是愛。
但我們還是要問:面對有著蟋蟀走過綠地的模型村,旁邊還有迷你消防員爬上迷你梯子,查看迷你茅草屋頂上的迷你破損處,我們該怎麼解釋?誰設計這些東西,造訪這些地方?關於我們的生活,它們能告訴我們些什麼?當伊莉莎白公主走在白金漢郡貝肯斯科特模型村的房屋之間,她是那天下午唯一一個相信自己統治了那個王國的訪客嗎?
(後略)
【其他章節摘錄1】
法蘭西絲‧格雷斯諾‧李(Frances Glessner Lee)年輕時常以普通的方式裝飾普通的娃娃屋──也就是一絲不苟的態度。她也製作了其他迷人的模型,例如整個芝加哥交響樂團:九十位音樂家與九十件樂器。但她之所以為世人記住,卻是因為某個更令人不安也更有用的東西。
(中略)
李在一九四〇年代開始精熟於製作小型但逼真的模型箱,描繪恐怖事件的發生地點。這些模型以木頭、布料、金屬、塑膠、玻璃、以及其他你預期在普通住家可以找到的材料製成,有十九座模型成功留存下來,雖然可能還有些模型沒能完工。每個模型都花數月打造,而且全都富含精確有力、反映時代的細節;她堅信如果在細節上出了錯,或者粗製濫造,就會馬上失去觀者的專注。於是,地毯、水槽旁的肥皂、桌上的麵包和牆上的鏡子全都經過完美縮小。咖啡滲濾壺裡有真正的咖啡粉,浴室中有隨手可及的極小藥罐,而客廳裡的棉布扶手椅則舒服得讓觀者幾乎想坐在那兒。
但其實你不會真的想坐在那兒:這些房間有人在廚房地板上流著血,吊在繩子上或倒在樓梯底。一具軀體往後倒在浴缸裡,水龍頭流出來的水湧向臉龐。有時候房裡有破壞或打鬥過的跡象,但有時只有枕頭上的口紅。但永遠都有一具屍體,因為謀殺事件屬於李的職責範圍,而最終總是發現屍體──裙子下的內褲底下穿著緊身褲、還有真皮鞋底的編織拖鞋──創造出這栩栩如生的場景只為表現其死亡。李稱呼她的模型為「死因不明案件的微型研究」(Nutshell Studies of Unexplained Death),在這些模型誕生大約八十年之後,有些案件死因依然不明。
李之所以從高貴的上流社會走向暴力血腥,是受到朋友麥格拉斯的啟發,這位波士頓法醫經常為警察於法醫涉入案件前,在犯罪現場表現的草率行徑而感到震驚(他們會移動或移走證據、清理血跡)。李創作的場景出自想像,但常基於麥格拉斯的描述或報紙上的謀殺報導。她為那些場景增添層次:爐台上一盤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曬衣繩上剛洗好的床單隨風飄動──都是經過刻意設計的誘餌。這些誘人的物件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讓觀者找到殺人動機、行凶手法或犯人(儘管並非每具屍體都曾遭遇犯罪行為:也有些人死於古怪的意外或自然死因)。最重要的是,李想讓她的立體透視模型具有教育意義,以大約一英寸比一英尺(一比十二)的比例輔助觀察。三十英寸的桌子被縮小到不到三英寸,而一把約十一英寸的左輪手槍則被縮小到一英寸。她說,她的意圖是要從模型頂端開始,以順時針方向向內旋轉移動,慢慢前進以確保沒有遺漏任何東西,最終結束在中心的屍體;九十分鐘應該足以收集所有線索。她不把自己的作品視為藝術或工藝,也肯定不是娛樂(但她的模型和早期的電視差不多大,這一點很妙)。她的作品完全沒有索恩製作的房間那種美學吸引力。反之,李將她的作品視為科學,如果她知道這項實驗至今依然有價值,一定會很高興。
***
每當李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在她晚年時常發生),她總是被稱為「有錢老太太」。她確實是,但如果這種形容方式讓人聯想到上流貴婦的形象,純屬誤會。李成為犯罪模型製作者之前是一位正義狂。她盡一切努力來提升警察執勤績效,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守護自己的特權地位,但也為了保護弱者。最重要的是,她相信若犯罪打擊者目標清晰而不腐敗,他們的任務是要「為犯人定罪,還無辜者清白,以及找出最終真相」。為此,她在一九三〇年代協助哈佛法醫系及哈佛警察科學協會成立,兩者都旨在將謀殺調查現代化:她相信現在該以演繹的科學技術,而非傳統調查方法或魯鈍直覺來指引道路,而她的信念是革命性的。歷史上稱她為鑑識科學之母,而她的關注焦點及受她影響的人,或許拯救無數人免於處決。這個歷程進一步延伸為她血腥的立體透視模型:藉由把行為濃縮到只剩下核心成分,她讓觀者看見真正重要的事物。即便到了今日,我們已受過懷疑論的充分薰陶,依然很難不在看著這些模型時同時感到厭惡與欽佩。它們不過是些用來玩賞的箱子,卻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把戲:以懷疑籠罩我們,而懷疑正是進一步調查探究的前兆。
李很了解死亡。她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六年之間失去了兄弟、母親、女兒、父親。就像伯茲近距離拍攝李的模型之書中所觀察到的,研究李這個人或許要以慰藉為題。她是個強硬苛刻的人,一位家族成員描述她是精神科醫師的絕佳案例。她外型具男子氣概:短髮、素顏、五官突出、戴金屬框眼鏡;連最資淺的心理學家都會注意到她渴望融入男性主導的世界。根據伯茲的說法,她早年同時受到保護與壓抑,她擁有舒適的上層階級背景,同時家長對她期望不高。她精通家政工藝,卻只有狹隘的職業選擇;她想上哈佛大學的要求被視為不夠淑女。李計畫逃離壓迫她的雙親;她在破裂婚姻中生下的三個孩子說她在脫離他們的束縛之後看起來最快樂。一九三〇年代首次聯繫麥格拉斯,並初嘗經濟獨立的滋味之後,她的命運產生了顯著的轉變。
李熱愛福爾摩斯和克莉絲蒂,或許她的外表變得像克莉絲蒂筆下的瑪波小姐並非純屬偶然,她把頭髮全都挽成髮髻,穿釦子扣到最高的深色襯衫和受一九二〇年代瑪麗皇后風格影響的帽子,神態嚴肅。但她比任何人都深知外表可以欺瞞他人。她對於克莉絲蒂許多溫暖讀物中出現的精采社交生活不感興趣,反而擁護下層階級;李製作的許多箱子都反映出艱苦都市生活對尊嚴的損害與不確定性。雖然掙扎於日常生活本身無法解釋降臨在箱裡娃娃身上的恐怖結局──在套房、穀倉、門廊、車庫裡──但確實讓這些箱子以慘淡的現實主義為根基;她創作的場景常瀰漫著一股強烈的悲傷。
她的受害者大多為女性,但目擊她們的微小死亡的幾乎都是男性。「視察者若想像自己是個六英寸高的小東西,最能好好檢視這些犯罪場景。」她解釋:「只要觀察一段時間,就能讓他走進那個場景,發現許多若不這麼做就會忽略的微小細節。」她表示這些模型意圖描繪每個場景最具「效果」的一刻,「如同電影畫面停格」。
李的每個模型都附有幾段文字。這些文字來自「目擊者」,經常是家人或死者在當地認識的人,他們發現屍體,因此提供了重要證詞,即便是杜撰的。例如,在「粉紅浴室」中,「羅絲‧費雪曼太太」死在地上,目擊者是她的管理員山謬‧魏斯。他在口供中回憶,「幾個房客抱怨有一股氣味,然後我在三月三十日開始尋找氣味的來源。」他顯然聞到了費雪曼的氣味。她沒來應門,魏斯看到信箱裡積了一堆郵件。他進入屋裡,但沒辦法打開浴室門,所以從防火梯通過浴室窗戶爬進去,發現倒下的費雪曼太太。
李接著解釋,「我們千萬不能忽略,這些口供可能是真的、可能有誤或故意講錯,也可能結合以上兩、三種情況。因此觀察者必須用全然開放的心檢視每一個案子。」就魏斯先生的情況,他的陳述屬實。費雪曼太太從浴室門上吊,但只有最敏銳的眼睛才會注意到她浴袍的藍色綁帶有幾條細線落在浴室門頂端;魏斯強行進入浴室時移動了懸掛著的遺體。
「粉紅浴室」和「黑暗浴室」的場景頗為不同,也就是屍體在浴缸中、水龍頭湧出水的那個場景。這具屍體是瑪姬‧威爾森,目擊者為她的室友麗茲‧米勒。米勒在宣誓後陳述威爾森患有癲癇(一個可能死因),但她發現屍體那天,也有兩個男人去威爾森房間,而且他們似乎喝了很多酒(另一個可能死因)。浴缸裡的水是為了淹死她,或是在她發作後想讓她甦醒?死後僵直的屍體是否被移動過,還有,為什麼屍體呈現這麼怪異的姿勢?地毯上的罐子和旁邊的藥暗示了什麼?創造出這個謎題的人──那個女人用大頭針大小的針編織著死者的黑色棉製長統襪,然後寫信給兒子談論這個工作真是費力得不可思議──成功地把我們帶離她模型的精細尺寸,進入一個比模型大上許多的世界。
大約八十年後,我們依然深受李的作品吸引。經過幾十年後,她的模型肯定因年代感而顯得更加獨特,但依然離逼真有一段距離。二〇一七年秋天,這些模型曾是史密森尼學會一場展覽的主題,但它們平時通常存放在附近巴爾的摩法醫長辦公室的高樓層(法醫長辦公室也主辦每年的法蘭西絲‧格雷斯諾‧李謀殺調查專題研討會,出席的有偵探、病理學家、律師,為期一週的活動中,必定會花幾個小時仔細端詳「微型研究」。)她的作品曾經啟發虛構作品的創作,電視影集《CSI犯罪現場》有一季出現了微縮品殺手──一個連續殺人犯在犯案現場總是留下自己精細的縮尺模型以示挑釁。李如果知道,會強烈譴責她的罪行,但欣賞她對細節的關注。
無論從任何角度、在任何年齡,看完這些模型之後,都無疑有種實現野心的感覺留在你心中。你是否解開了粉紅浴室中屍體的謎團不是重點,也從來都不是。重點是,李充分運用了微縮品的潛力,而同樣這股潛力可以連結到瑪麗皇后的娃娃屋裡的所有房間及索恩的作品。你靠得愈近,就看到愈多,於是又靠得更近。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艾菲爾鐵塔到底能縮多小:一部知識豐富、熱情洋溢的人類微縮文化史╳模型博物誌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艾菲爾鐵塔到底能縮多小:一部知識豐富、熱情洋溢的人類微縮文化史╳模型博物誌 作者:賽門‧加菲爾 / 譯者:吳芠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7-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艾菲爾鐵塔到底能縮多小:一部知識豐富、熱情洋溢的人類微縮文化史╳模型博物誌
在世界分崩離析之前,且讓我們縮小並緊握它
───
★亞馬遜4.4顆星,《泰唔士報》熱情盛讚
★書市僅此一本的全球微縮文化史料蒐羅+田野調查+文化分析
「微縮品」是無用的極致展現
出於一種珍貴、純粹,不具功利性的喜愛和熱情
最微小的事物以其令人著迷的特質推動了文明的演進
反映自古人類內在深層的需求
◎ 搖滾巨星洛‧史都華二○○七年害羞「出櫃」,坦承二十年來都帶著心愛的鐵道模型巡迴,在各地飯店組裝
◎ 「法醫科學之母」法蘭西絲‧格雷斯諾‧李推動鑑識實務的工具是一個個還原謀殺現場的娃娃屋
◎ 科技小說先鋒威爾斯出版過《地板遊戲》一書,指導讀者如何在家中以迷你人偶和微型碉堡進行對戰,並提出「地毯式的轟炸就該留在地毯上」的反戰思維
◎ 建築大師札哈‧哈蒂認為,那一個個模型是許多偉大構想曾經存在過的唯一證明
小人國、娃娃屋、建築模型、玩具車、模型飛機、袖珍書、地球儀、艾菲爾鐵塔鑰匙圈……微縮品在我們身邊俯拾即是。會不會說到底,我們每個人都是不自覺的模型迷?
作者賽門‧加菲爾蒐羅各地微縮品的重大事件和奇聞軼事,結合歷史、心理學、藝術史,當然還有個人的小小偏執,探討微縮品的強烈吸引力從何而來,人類為何自古就有把事物縮小的古怪癡迷,這些小小事物又如何幫助我們對世界產生整體性的認識。
微小事物可提供對偉大事物的類比,顯示知識的軌跡。
──古羅馬哲人盧克萊修
中古歐洲貴族會請畫家繪製袖珍肖像,作為名片或求偶信物
中世紀歐洲和俄國皇室將娃娃屋作為私人財產的目錄,順便炫富
初登艾菲爾鐵塔的經驗對當時人們的衝擊之大,旅遊消費紀念品自此誕生
全球的袖珍書愛好者每年都舉行密會,書籍內容同樣瘋狂,且都不需要版權
數百萬根本不下廚的人都迷上線上觀看烹煮微型食物是怎麼回事
世界各地模型村的誕生與衰亡──何以最受歡迎的都出自業餘愛好者之手,商業化的模型村卻一個比一個悲傷,還很詭異……
兒時的玩具將成人的世界植於我們心中,
而某些玩賞小小事物的欲望又轉變為製作小小事物的欲望。
掌控一個縮小的世界賦予我們新的觀點,在不確定的年代中重建我們的秩序感,
讓我們得以用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看待世界。
────
【微縮品/Miniature的定義】
不同於純粹小型的東西,微縮品是較大物件的縮小版本,而且本身經過有意識的創造。為此,它也履行了微縮品的職責──解釋概念、解決謎題、喚起記憶。
各界推薦
不只是尺寸,是尺度的變換,讓我們獲得新的視野,產生新的洞見。站在艾菲爾鐵塔上,巴黎變成一張地圖;握在掌中的模型,讓我們可以環視與凝望一個戰場、田園與住屋。這本書帶給讀者入神的閱讀經驗,進而開啟了嶄新的世界。──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畢恆達
知識淵博,熱情滿溢。──《泰晤士報》
文筆有種討喜的輕鬆感,令人耳目一新。──英國作家黛安娜‧艾希爾(Diana Athill)
這是一份難得的享受,愉悅、巧妙又引人入勝。賽門‧加菲爾穿透表面,挖掘出微縮世界的奇異之處──引人費解卻奇妙無比,有點傻氣又超級迷人,正合我的口味。──英國作家凱姬‧卡魯(Keggie Carew)
扣人心弦又感人,而且極其幽默。──英國作家妮娜‧史提比(Nina Stibbe)
本書特色
文化觀點細緻精采、脈絡清晰,史料蒐集豐富有趣,令人大開眼界。
作者以英式幽默描述微縮迷不為外人理解的「nerd」心情,捧腹之餘也相當感人。
從文化和歷史談微縮文化的唯一經典。
【佳句摘錄】
我們活在巨大而憂傷的世界,僅只是控制這世界中縮小後那微小的一部分,就有助於恢復秩序感與價值感。
──
早期電路板的微縮創作者幾乎都是業餘者。在世人懂得欣賞與珍惜他們的作品之前,他們只感受到內在的熱情與家人的反對。
業餘者的英文「amateur」源於拉丁文「amare」,意思是愛。
──
對微縮物的渴望始於童年,通常在成年接近時就被拋下,就像火箭急速飛向月球時,助推器從上面脫離:青少年不要玩具車,他們想要真正的車子。如果他們不想要真正的車子,別人或許會覺得他們很古怪,而正是這份古怪吸引了我們。
──
一八八九年春末,艾菲爾鐵塔落成──
除非你過去曾乘著氣球飄浮,否則這必定是你第一次見到這世界以等比例縮小……
登高望遠的激動感結束在極樂的安寧境界:馬糞與煤灰的臭氣就此蒸發。
「巴黎沉入黑夜,彷彿某個在低語聲與教堂鐘聲之中沒入海底的傳奇城市。」
對於頭幾個月登上鐵塔的眾人而言,看到的景觀「在一八八九年意義重大的程度就相當於八十年後從月球看到地球的景象。」
那謙遜加上敬畏的古怪組合──在雲朵之中,我們多麼無足輕重,但朝著雲朵前進這件事意義卻多麼重大──無論在任何季節或門票價格多高都一樣;那是在比例上進行冒險,以及重新看待我們的世界。
艾菲爾鐵塔的開幕代表大量消費紀念品的誕生。從此以後,一個象徵物只有在也成為返家行囊的一部分時,才真正成為地景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
英國記者暨紀實作家,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早年曾為BBC寫過紀錄片劇本,也替英國獨立報、觀察家報等媒體撰文。興趣廣博,對雜學、軼人軼事、文化史皆有高度熱忱,著有《計時簡史》(Timekeepers)、《地圖的歷史》(On the Map)、《淡紫色──改變世界的顏色》(Mauve)、(以下書名暫譯)《致書信》(To the Letter)、《Mini車款的故事》(Mini)、《首位鐵路事故輪下魂威廉•赫斯基森的最後一日》(The Last Journey of William Huskisson)等多部作品。二○一○年以《字體故事》(Just My Type)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亦曾以《純真的盡頭:AIDS在英國》(The End of Innocence: Britain in the Time of AIDS)榮獲毛姆獎。
作者網站www.simongarfield.com
譯者簡介:
吳芠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畢業。譯有《不要靜靜走入長夜》、《如何說,如何聽》、《關掉螢幕,拯救青春期大腦》等書。
章節試閱
前言:觀看的藝術
我用簡單的定義區分微縮品和純粹小型的東西:微縮品必須是較大物件的縮小版本,或可導向較大物件,而且本身經過有意識的創造。它也履行了微縮品的職責──解釋概念、解決謎題、喚起記憶。作為紀念品的建築物鑰匙圈就符合條件,雖然不太有趣;迷你琴酒也是;福斯金龜車則不算,史上最小的頂針也不是,不管這些東西的收藏家有多熱中都一樣。迷你吧和小型玩賞犬在合格邊緣,盆栽藝術也是,其中的「小」透過刻意修剪栽種而創造出來。沒有人會對五歲小孩用塑膠做成的玩具貴賓狗美勞作品感興趣。你還可以訂定更多規則,限定長...
我用簡單的定義區分微縮品和純粹小型的東西:微縮品必須是較大物件的縮小版本,或可導向較大物件,而且本身經過有意識的創造。它也履行了微縮品的職責──解釋概念、解決謎題、喚起記憶。作為紀念品的建築物鑰匙圈就符合條件,雖然不太有趣;迷你琴酒也是;福斯金龜車則不算,史上最小的頂針也不是,不管這些東西的收藏家有多熱中都一樣。迷你吧和小型玩賞犬在合格邊緣,盆栽藝術也是,其中的「小」透過刻意修剪栽種而創造出來。沒有人會對五歲小孩用塑膠做成的玩具貴賓狗美勞作品感興趣。你還可以訂定更多規則,限定長...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觀看的藝術
微縮品在我們生活中的存在與重要性,以及它如何滋養了我們對世界的欣賞
第一章 高處的風景
艾菲爾鐵塔如何改變我們對城市的理解,並普及紀念品
同場加映: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埃及棺材
第二章 模型村與模型城,有些特別幸福美滿
模型如何永遠固定住一個國家看待自己的眼光
同場加映:一七八九年,英格蘭的奴隸船
第三章 一段婚姻的肖像
袖珍畫如何揭露秘密
同場加映:一八五一年,漢堡才華洋溢的跳蚤
第四章 袖珍書協會的精彩年會
世界上最小的書有多大,以及你到底要怎麼翻開它?
同場加映:一九一一年,英格蘭...
微縮品在我們生活中的存在與重要性,以及它如何滋養了我們對世界的欣賞
第一章 高處的風景
艾菲爾鐵塔如何改變我們對城市的理解,並普及紀念品
同場加映: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埃及棺材
第二章 模型村與模型城,有些特別幸福美滿
模型如何永遠固定住一個國家看待自己的眼光
同場加映:一七八九年,英格蘭的奴隸船
第三章 一段婚姻的肖像
袖珍畫如何揭露秘密
同場加映:一八五一年,漢堡才華洋溢的跳蚤
第四章 袖珍書協會的精彩年會
世界上最小的書有多大,以及你到底要怎麼翻開它?
同場加映:一九一一年,英格蘭...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21/01/05
202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