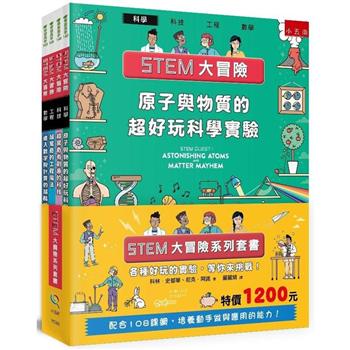第一章:
住。在民國(一):那些偉人凡人都要面對的生活大小事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一九一九年實在無法讓人安心自適。這一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務員周樹人忙壞了,倒不是因為這年京城發生了一個叫「五四運動」的運動,也不是因為他經常要以「魯迅」的身份替《新青年》寫稿,而是因為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不再是一個可以什麼也不管不顧的毛頭小伙子,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在北京置產了。
周樹人是個十九世紀的「八年級生」——他生於一八八一年。跟現在許多「八年級生」一樣,混得不好也不壞。周樹人的官位不大,已經在教育部當了七年公務員,但也只是混了個科長級的「僉事」而已,就連這個工作都是他拜託老鄉蔡元培謀來的。
對於當時普遍富有的浙江人來說,到北京來當個公務員似乎沒有多大出息,不過,如果你看到周公務員的薪資單,就會明白他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工作弄到手:他每個月的工資是三百大洋。請注意,這是真正的大洋——三百枚吹起來有清脆響聲的大銀元。如果你不知道一枚大洋值多少錢,那你可以到北京的潘家園,或者你所在城市的文物市場詢個價,眼光銳利的文物販子會告訴你一枚「袁大頭」現在最便宜也要兩千五百元,這樣一來,周樹人的月工資相當於我寫這本書時的七十五萬元。更重要的是,周樹人手上那三百大洋的購買力可不是現在的七十五萬元可比擬的,現在這筆錢在北京的二環內(周樹人時代的北京城範圍)還買不了一個獨間套房的廁所,而周樹人的三百大洋已經能買下一個相當不錯的四合院——還能挑三揀四的買:地段要好,要清淨——這是周樹人對房屋仲介提出的要求。
如果你仍然搞不清楚三百大洋到底能幹什麼,我們這裡為您訪問到當時和周樹人同住北京城的一個老外——美國人狄登麥。狄登麥是一個好奇心強烈的老外,因為他的好奇和專業精神,讓我們知道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北京究竟是什麼樣子。魯迅買房這一年,狄登麥剛好調查了北京的物價和一般人的消費水準,對於一個北京的五口之家來說,只要一百大洋,就足夠他們還算體面地生活一年:
「有了一百圓生活費,食物雖粗而劣,總可以充飢;房雖不精緻,總可以避風雨;此外每年還可以做兩套新衣裳,買一點煤,免除到路上撿柴;更可以結餘五圓當做零用錢。拿了這五圓可以在年節買一點肉吃,間或喝喝茶,若家裡沒有病人,不需醫藥費,或者還能去附近山上進香拜拜。」
我們將這樣的生活水準乘上三十六倍,就能明白魯迅過的是什麼日子。對於一個每月都有三百大洋進賬的人來說,買房和買白菜的區別並不大,也許最大的區別是買房總需要一個仲介,而買白菜不需要。公務員周樹人當然也找了一個仲介,不得不找仲介的原因是老北京根本沒有新建大樓可買!因為當時根本還沒有「開發商」這種角色。
好吧,周樹人開始了跟著仲介到處看房的生活。在《魯迅日記》裡,我們可以看到周公務員這位身材消瘦的小個子四處奔忙的身影。請不要忘記,這一切和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是同時進行的:
二月二十七日晴。上午往林魯生家,同去看屋二處。
三月一日晴。上午往銘伯先生寓。午後同林魯生看屋數處。
八日曇。午後邀張協和看屋。夜雨雪。
十一日晴。午後同林魯生看屋。
十四日晴。午後看屋。下午復出,且邀協和俱。
十九日晴。午同朱孝荃、張協和至廣寧伯街看屋後在協和家午飯。
五月二十九日晴。下午與徐吉軒至蔣街口看屋。晚錢玄同來。
周樹人看了很多間房子,但沒有一間讓他滿意,原因是這些房子都不夠大。要知道,他買房可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自己名下那一大幫需要他養著的人——這個團隊分三個體系,加起來有一個排:
老娘體系:周樹人母親魯老太太,周樹人髮妻朱安(這是老太太給兒子的「禮物」,對周樹人來說,她與其說是自己的附屬物,還不如說是老太太的附屬物)。
二弟體系:二弟周作人,二弟媳羽太信子,侄子周豐一,姪女靜子、和子,周作人內弟羽太重久(這個比較搞笑,娶個媳婦還要幫忙養媳婦的弟弟,後來又加入更多娘家的人)。
三弟體系:三弟周建人,三弟媳羽太芳子,侄子豐二、豐三,姪女鞠子。
伺候這一大幫人自然還需要僕人、保姆、廚師、司機、保安等一整套人馬,一個普通的四合院怎麼住得下呢?終於,一個三進的大院子——八道灣衚衕十一號院入了周公務員的法眼:
北京八道灣衚衕十一號院大門。「十一」這個數字就像兩個人前後站在一起,冥冥中似乎預示著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當時的親密,但「十一」又像兩條平行線,又預示著兄弟後來的分道揚鑣。
周公務員辦事犀利,看中這間房子後三下五除二就將它買了下來:
七月十日小雨。上午寄羅志希信。午後晴。約徐吉軒往八道彎看屋。
七月二十三日晴。午後擬買八道彎羅姓屋,同原主赴警察總廳報告。
八月十八日晴。午後往市政公所驗契。
十九日晴。上午往浙江興業銀行取泉。買羅氏屋成,晚在廣和居收契並先付見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
從這些天的日記可以看出,那時候買房的手續也是一道也不能少,任何時代的政府都一樣,對房地產交易控制相當有一套。不過,終於找到大房子的喜悅壓過了他辦手續的煩惱,這房子有三進院落,足夠他那些侄子姪女們玩耍的,更有三十多間房,哪怕周作人再來多少個小舅子都夠住。
房子很快成交了。雖然每月有三百大洋進賬,精明的周公務員還是做了小小的抵押借質,房價一共是三千五百元,他依照公務員的身份到浙江興業銀行貸款五百元,加上變賣老家舊房子的錢,自己幾乎沒付多少錢就買下了這所大房子。在這項皆大歡喜的生意中,仲介可能是最高興的:他沒花多大力氣就淨賺一百七十五大洋,如果他願意來到現在的北京市,這筆錢足夠讓他買下一間兩房一廳的房子了。
買完房的周公務員就像每個剛買房子的人年輕人一樣,興奮得很,他三天兩頭往新房子跑,一是要監督工人修繕,另一方面,單是看看房子就能讓他很有成就感,這種成就感跟他以「魯迅」身份寫出《狂人日記》的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畢竟,一間能讓全家人快樂的大房子比那些虛幻的思想啓蒙來得更加堅實:
十日晴。休假。上午往八道彎視修理房屋。
十九日晴。星期休息。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婦及豐、謐、蒙乘馬車同游農事試驗場,至下午歸,並順道視八道彎宅。
二十三日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十一月一日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七日曇,風,午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十日曇。午後往八道彎。晚小雨。夜劉半農來。
十二日曇。上午往八道彎。
讓周樹人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裝修房子竟然比買房子還麻煩。為了替新房子裝設下水道,工人、鄰居、看熱鬧不怕小事化大的掮客等等,都想趁機撈一筆。對這些有理或無理的要求,周公務員一概拿錢擺平,在文化論戰中他是多凶悍的人啊,但在生活中他基本上是一個息事寧人的老好人:
十三日晴。在八道彎宅置水道,付工值銀八十元一角。水管經陳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費三十元,又居間者索去五元。
十四日晴。午後往八道彎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晚潘企莘來。夜風。收拾書籍入箱。
房子裝修終於大功告成了,一共花了他六百多大洋。拿到錢的各色人等一定都在暗自偷笑。不過,這只是周公務員兩個月的工資,是他弟弟周作人即將在北京大學領到的一個多月的工資而已,花了也就花了。這時候已經是十一月,寒風已經奔襲到北京,周樹人收拾著自己的書和在琉璃廠買來的各種小文物開始搬家了。
二十一日晴。上午與二弟眷屬俱移入八道彎宅。二十二日晴。上午寄晨報館信。午後往留黎廠買嵩顯寺及南石窟寺碑陰各一枚,佛經殘石四枚,共券五元。往陳順龍牙醫生寓,屬拔去一齒,與泉二。過觀音寺街買物。夜風甚大。
生活就是這樣平靜。馬上就要四十歲的周樹人,同時也是已經聲名卓著的魯迅,像往常一樣繼續著他的幸福生活:寫信,買書,拔牙,購物,晚上聽好朋友錢玄同報告街上運動的進行狀況。哪管夜裡的寒風刺骨,也不怕政治的高樓上山雨欲來。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去,活在民國是不是也不錯呢?
9. 民國人的髮型
髮型與政治息息相關,在中國是確切無疑的。清朝入關後,要求全體中國人留辮子,違者殺頭,這樣一來,千萬個中國人為保護自己的髮型而丟了命。幾乎沒人想過為什麼要留辮子,其實,留辮子是人類的一個大發明,對於遊牧和狩獵民族來說,將亂糟糟的頭髮梳成辮子有其便利性,可以防止腦袋被異物勾住以致喪命,但對於向來以農耕為主的漢族人來說,留辮子簡直就是累贅。
當辮子這種累贅髮型終於植根於中國人內心時,辛亥革命來了。
革命黨革命成功後,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中國人剪掉辮子。這時的中國人早忘了當年為了不留辮子而喪命的往事,面對革命黨明晃晃的剪刀時,很多人竟然嚇得自殺了。
對於剪辮子態度最積極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公務員,一種是唱戲的。
公務員代表政府,政府說要剪辮子,公務員當然要帶頭,也只有這樣才能展現出自己的合法性,所以警察、辦事員們早早就把辮子剪了,然後上街替行人剪辮子。這是一個經典的場面,可惜沒有畫家給記錄下來:被剪掉辮子之後,有人摸著後腦勺,涼颼颼的感覺讓他悵然;有人手裡還攥著辮子,怔怔地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這個「文物」;有人興奮地大叫,有人出錢請每個剪了辮子的人吃一碗大肉麵……
唱戲的為什麼對剪掉辮子抱持歡迎的態度呢?因為實際上的需要。唱戲的總要化妝,那根辮子太礙事了,而且睡覺時那根辮子怎麼擺都不對勁。所以一聽說革命了,不能留辮子了,第一個響應的就是京劇大師梅蘭芳。梅蘭芳覺得剪辮子簡直是個德政,不僅自己剪了,還拿起剪刀替自己身邊的人剪。他有兩個僕人,一個是聾子,一個是大李。聾子晚上睡覺沈,又聽不見,梅蘭芳就趁他睡著的時候偷偷剪了,第二天聾子醒來發現辮子不見了,差點嚎啕大哭,但沒辦法,沒了就是沒了。梅蘭芳用這個辦法剪了很多頑固派的辮子,大李是最頑固也是最精明的,他生怕自己的辮子也被暗中剪掉,於是睡覺時都把辮子藏在身子底下,讓梅蘭芳無從下刀。梅蘭芳連盯了三、四天都沒找到機會,後來他終於等到大李的辮子露出一點來,趕緊出手,但可惜的是辮子只剪了一半。第二天,大李哭喪著臉找梅蘭芳的伯母訴苦,但半個辮子也實在不像話,也只好徹底剪掉了事。
其實,當漢族人留戀辮子的時候,反倒是滿族人對剪辮子沒什麼意見。滿族人向來是以當兵為業,每天的工作就是練習打架,而打架的首要目標就是不要被對方抓住自己的辮子,這一點讓滿族人相當苦惱,但留辮子本來就是自己提倡的,也只能延續這個傳統。革命後,滿族人一聽到可以不留辮子,大多歡呼雀躍,紛紛將辮子剪了,不僅剪了,而且都剃了光頭——這樣打起架來就完全沒有罣礙了。剪辮子在滿族人之中完全沒有阻力,就連王公貴族也紛紛響應,到了最後,只有末代皇帝溥儀本人的辮子還留著。他這根辮子象徵意義太重,所以遺老遺少們堅決反對剪掉,但溥儀還是執拗地將它剪了。
知識分子大都沒有剪辮子的問題,因為他們在留學之前就已經剪過了。
留學越早的,辮子自然也剪得越早。魯迅是民國名人裡留學較早的,一到日本他就把辮子剪了: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裡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裡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魯迅不愧是個會過日子的人,剪掉的辮子還要送給日本女人做假髮,以免浪費。
胡適和趙元任是坐同一條船去美國留學的,上船前,有人要求他們穿上西裝,剪掉辮子,留著那根東西到了美國,實在是太不搭調了。據趙元任回憶,替他剪辮子的理髮師一再問他「是不是真的要剪?」因為就在不久前,一個男的剪掉辮子後,那人的妻子竟然憤而自殺了,人命關天,理髮師怎麼能不謹慎呢?
趙元任剪了辮子之後馬上就把它扔了,胡適卻不然,他細心地將辮子包好,寄給了遠在安徽的老母親,這頗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也要還給母親的意思。
就在所有人都剪了辮子的時候,偏偏有那麼幾位留起了辮子,這樣做的理由無非是要證明自己反對這個社會。最有名的兩根辮子,一根是辜鴻銘的,一根是王國維。
辜鴻銘本來是沒留辮子的。他是華僑,還是混血兒,從小就是西裝革履的打扮,但一回到中國就把辮子留起來了,至死皆然。他對自己這根辮子十分得意,時時加以宣傳,後來竟然成了北京城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辜鴻銘的奇特之處在於他不僅自己留辮子,連他的御用車夫也要留辮子,且看周作人的記述:
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所以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同課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出的人物。
辜鴻銘雖然留辮子,但是他只是要表明自己是一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並不是要復辟大清朝,所以當辮子軍主帥張勳復辟時他並未參與,他要的是皇帝這種制度,而不是皇帝本人。王國維則與之相反,他雖然做學問比辜鴻銘要廣博開明得多,但在政治立場上確實是忠於大清朝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被紫禁城裡的小朝廷聘為皇帝的老師。王國維的辮子比辜鴻銘的還頑固,他在日本留學時就已剪了辮子,回國之後又再次留起來,見到末代皇帝溥儀時,溥儀命令他剪掉,「君無戲言」,王國維只好再次剪掉,但等風聲過後,他又留了起來——這簡直叫整個中華民國都拿他沒轍了。
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沉湖自殺,辜鴻銘於一九二八年病逝,中華民國最後兩條著名的辮子也伴隨他們離開了人世。再想找辮子,只能往戲台上去了。
和男人們的這些辮子風波比起來,中華民國的女人們要幸福多了,因為她們根本就沒有這些政治任務。她們的髮型只需要跟著時髦走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活在民國也不錯: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愛、辦會館......完整重現民初風範百態史(搭配近百幅民初珍貴老照片)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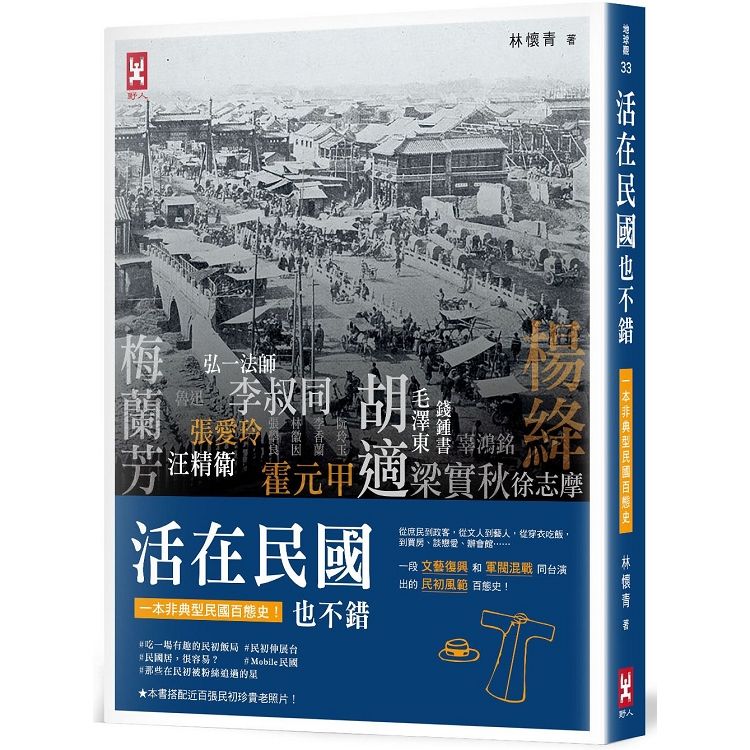 |
活在民國也不錯: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愛、辦會館......完整重現民初風範百態史(搭配近百幅民初珍貴老照片) 作者:林懷青 出版社:野人 出版日期:2019-10-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6頁 / 17 x 23 x 2.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0 |
中國歷史 |
二手書 |
$ 300 |
二手中文書 |
$ 332 |
Social Sciences |
$ 357 |
社會人文 |
$ 370 |
中文書 |
$ 370 |
中國歷史 |
$ 370 |
Others |
$ 37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活在民國也不錯: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愛、辦會館......完整重現民初風範百態史(搭配近百幅民初珍貴老照片)
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
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愛、辦會館......
一段文藝復興和軍閥混戰同台演出的
民初風範百態史!
★本書搭配近百張民初珍貴老照片!
沒人敢惹的小公務員魯迅、整個北京城的偶像胡適、
寫粉絲信的毛澤東、拿釘子戶沒轍的蔣介石、
冰心的同性愛驚天動地、錢鍾書和楊絳的愛情唯美精緻……
快來看看民初時期政客文豪的囧態百出,
市井小民的平凡幸福。
食、衣、住、行、育、樂,
一個不缺,
讀一本課本不會教的非典型民國史。
你沒想過的民初生活,你想不到的民初風光。文人的民國、政客的民國、明星的民國;歷史中的民國、思想裡的民國、舌間上的民國,說到底,都是老百姓生活著的民國。活在這樣的民國,好像也不錯?
【吃一場有趣的民初飯局】
*人人都想品嘗的「滿漢全席」,為何溥儀卻說一點都不想念?
*吃「豬血」在民初竟然是「民族主義」的表率,國父孫中山還動用「建國方略」為其辯護?
*吃「好吃的」只是普通饕客,讓弘一法師告訴你,如何讓「不吃」也成為一種境界。
【民初伸展台】
*不只女人用服裝行頭耍心機,蔣介石也曾用服裝陰了李宗仁一把?
*剪辮子,是潮流;留辮子,是個性。辜鴻銘、王國維表示:「老子愛剪不剪,干你啥事?」
*民初第一才女林徽因親自設計婚紗!不知各位毒舌時尚評論家怎麼看?
【民國居,很容易?】
*現代人為了買房過得苦哈哈,魯迅卻只要一年薪水就能買豪宅?
*明明買房很容易,為何胡適還是寧可租屋,當個「無殼蝸牛」?
【Mobile民國】
*胡適不買房原因大揭密:錢都拿去投資古董車收藏?
*大名人魯迅也可能是「疲勞駕駛」受害者,難道有更大的陰謀牽扯其中?
*與陸小曼結婚後的徐志摩窮到要去「搭便機」,友情提供「便機」者為「少帥」張學良?
【那些在民初,被粉絲追過的星】
*霸氣毛澤東也有小粉絲情懷,崇拜對象正是大家的好朋友胡適?
*「四大美男」如果穿越到現代,會是國民老公還是極品小鮮肉?
*「霍元甲」爆紅奇蹟!專家表示:「足見民初時期的造星技術已十分成熟」
作者簡介:
林懷青
中年大叔,骨灰級歷史扒皮手。拿歷史當飯吃,寫點字換酒錢。論壇上拍過磚,部落格上耍過寶,微博上賣過萌,自稱「活在民國也能混個臉兒熟。」出書不多,就此一本——四十歲的處男作。請您笑納!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住。在民國(一):那些偉人凡人都要面對的生活大小事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一九一九年實在無法讓人安心自適。這一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務員周樹人忙壞了,倒不是因為這年京城發生了一個叫「五四運動」的運動,也不是因為他經常要以「魯迅」的身份替《新青年》寫稿,而是因為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不再是一個可以什麼也不管不顧的毛頭小伙子,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在北京置產了。
周樹人是個十九世紀的「八年級生」——他生於一八八一年。跟現在許多「八年級生」一樣,混得不好也不壞。周樹人的官位不大,已經在教育部當了七年...
住。在民國(一):那些偉人凡人都要面對的生活大小事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一九一九年實在無法讓人安心自適。這一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務員周樹人忙壞了,倒不是因為這年京城發生了一個叫「五四運動」的運動,也不是因為他經常要以「魯迅」的身份替《新青年》寫稿,而是因為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不再是一個可以什麼也不管不顧的毛頭小伙子,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在北京置產了。
周樹人是個十九世紀的「八年級生」——他生於一八八一年。跟現在許多「八年級生」一樣,混得不好也不壞。周樹人的官位不大,已經在教育部當了七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住。在民國(一):那些偉人凡人都要面對的生活大小事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憤青毛澤東和他的幸福生活
※胡適:租個房子也不錯
※司徒雷登:六萬塊錢買下北京大學未名湖
※公務員魯迅二次買房記
※老北京城的氣味和聲音
※胡適的私家車
※民國人怎麼穿衣服?
※民國人的髮型
※退休公務員魯迅上海租房記
※保定:民國小城裡的生活
※民國的「釘子戶」
第二章:
住。在民國(二):那些名流們的勵志奮鬥記
※紹興會館的「虐貓」人
※績溪會館的高考考生
※湖廣會館裡賞給宋教仁兩記耳光
※最美麗的監獄:宋...
住。在民國(一):那些偉人凡人都要面對的生活大小事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憤青毛澤東和他的幸福生活
※胡適:租個房子也不錯
※司徒雷登:六萬塊錢買下北京大學未名湖
※公務員魯迅二次買房記
※老北京城的氣味和聲音
※胡適的私家車
※民國人怎麼穿衣服?
※民國人的髮型
※退休公務員魯迅上海租房記
※保定:民國小城裡的生活
※民國的「釘子戶」
第二章:
住。在民國(二):那些名流們的勵志奮鬥記
※紹興會館的「虐貓」人
※績溪會館的高考考生
※湖廣會館裡賞給宋教仁兩記耳光
※最美麗的監獄:宋...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