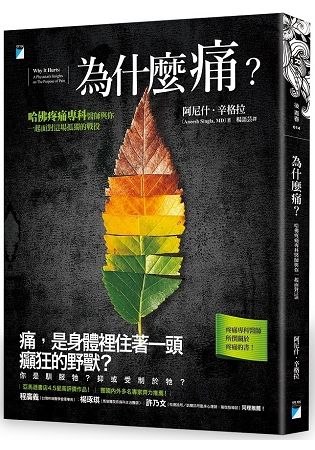痛,是身體裡住著一頭癲狂的野獸?
你是馴服牠?抑或受制於牠?
你是馴服牠?抑或受制於牠?
你還在疼痛的絕望黑洞裡拚搏,還在無止境地質問?
你是不是希望有人告訴你所有疼痛的答案?希望有人告訴你這世界不會有白白的痛?
了解疼痛、馴服疼痛,就從這本書開始。
「疼痛真正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
我們都曾經做過這樣的詰問。這也是阿尼什•辛格拉作為一位疼痛專科醫生最常被追問的問題。因此,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與疼痛對話,並從一位專業的疼痛醫師角度出發,書寫疼痛(生理與心理的疼痛)。他在書中手把手地教我們如何「管理疼痛」、「處置疼痛」、「翻轉疼痛」,並且提供了個人對於疼痛的哲學性思考,讓我們細察自己的疼痛經驗,知道如何從心應對疼痛,並在其中取得平衡。
★ 疼痛專科醫師所撰關於疼痛的書!
★ 亞馬遜書店4.5星高評價作品!
★ 獲國內外多名專家齊力推薦!
★ 程廣義(台灣疼痛醫學會理事長);楊琢琪(馬偕醫院疼痛科與麻醉科主治醫師);許乃文(松德診所/凱薾診所臨床心理師、瑜珈指導師)同理推薦!
•因腿部神經受損而吃盡苦頭,馬克對醫生要求說:「可以幫我截肢嗎?」
•每天處於水深火熱神經疼痛中,史考特說:「過去的那個我長什麼模樣?」
•服用了高劑量的鴉片後,還是無法控制脊椎疼痛,大衛說:「我這輩子就只能這樣了嗎?」
•下背痛逐年惡化導致無法自理生活,瓊妮說:「我難道不可以過正常的日子嗎?」
•罹患憂鬱症而每日鬱鬱寡歡,安妮問:「我已經那麼痛了,為什麼其他人都看不到?」
•當醫生無法找出疼痛病源,病人憤而質問:「所以一切疼痛都是我自己的想像?」
……
你是否已經發現,他們不是你,卻看起來如此熟悉?
疼痛之所以讓人窮思極研、恨不能刨根究底,讓人卯起來抵禦,
因我們都曾經一樣地痛,因我們都不曾一樣地痛。
痛不僅僅是痛,你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
◎ 應對疼痛的方式
◎ 無痛人生未必是好事
◎ 如何分辨好的疼痛與壞的疼痛
◎ 心理痛與生理痛息息相關
◎ 習得找出疼痛原因的方法
◎ 如何使用有效的方式來管理疼痛
◎ 為疼痛設定停損點——不過度治療
◎ 領悟疼痛的價值
◎ 重拾快樂人生的方法
本書特色
◎「疼痛教育」的入門,一本把「疼痛」寫得淺顯易懂的書!
◎由疼痛專科醫生所撰。
◎作者為哈佛醫生,有十多年的疼痛專科經驗。
◎亞馬遜讀者好評4.5顆星。
◎作者個人網站:http://www.whyithurtsbook.com/
◎本書獲國內外多位疼痛專家齊力推薦!
佳評如潮
「面對疼痛,你可能處理不足,又有時會過度處理,疼痛無所不在,它既主觀又不真實。期待本書的出版,能讓讀者以全新觀點來看待疼痛,翻轉疼痛。」——程廣義(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麻醉暨疼痛科主治醫師兼主任、台灣疼痛醫學會理事長)
「這本書應該要成為全民疼痛教育的基礎書籍之一!」——楊琢琪(馬偕醫院疼痛科主治醫師)
「溫柔覺知屬於你的身心疼痛對話,翻轉疼痛」——許乃文(松德診所/凱薾診所臨床心理師、瑜珈指導師)
「在他的新書《為什麼痛?》中,阿尼什.辛格拉醫師用全面且幽默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為什麼痛?》著重真實生活的案例:我們為何疼痛、我們為什麼需要疼痛以及如何提供疼痛更妥善的管理。讀者將發現書中許多醫學與「真實病人」的經驗,可以解釋痛什麼痛,如果你的疼痛無法求診於辛格拉醫師,這本書會是你的第二選擇。」——瑞克.布萊德利(《快速健身:十五分鐘不流汗運動》作者 (Rick Bradley: author of Quick Fit. The Complete 15-minute. No-Sweat Workout))
「海豹特種部隊有此一說:『美好時光只在昨日』。有了辛格拉醫師的著作,你下一個美好時光也許是明天!閱讀這本書吧!」——丹.瓦萊克 (Dan Valaik),(醫學博士,前海豹特種部隊隊員,約翰霍普金斯骨外科醫師)
「以生花妙筆將複雜的疼痛轉化成扣人心弦之作。」——史帝芬.巴爾納 (Steven Barna)(醫學博士,南佛羅里達大學醫學院矯形及運動醫學助理教授)
「以清晰易懂、盡智竭力、悲天憫人的見解,說明我們如何經歷疼痛和苦難,以及如何處理。」——約耳.耶格爾 (Joel Yager)(醫學博士,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精神病理學教授)
「終於有一本表達明晰、見解深刻、內容有趣的書籍,討論許多病人(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處理的議題。」——傑.康納 (Jay Khanna)(醫學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骨外科副主席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