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卡夫卡寫給巨人父親的控訴與傾吐,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一本「父愛創傷」。
★內容簡介
「我的寫作都與你有關,我在作品裡申訴的,
是那些無法在你胸懷裡申訴的話……」
─── 卡夫卡的熾誠家書 ───
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一本「父愛創傷」
//
你是我衡量所有事物的尺度。
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領域,才可能是我的生活。
而根據與你高大身軀一致的想像,這樣的領域寥寥無幾……
//
▍「親愛的父親,最近你問我,我為何聲稱對你感到恐懼……」
▍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寫給巨人父親的控訴與傾吐
卡夫卡的文學作品充滿壓抑、疏離與絕望,始終在與權威、自我拉扯,他的寫作動機乃至人格養成,都和其父赫爾曼有關。
卡夫卡在他離世前五年,寫了一封長達103頁的信給父親,道盡對父親既崇仰又恐懼,急於逃離又交織著歉疚的矛盾情感。信中細述宛如巨人強大的父親對其施加的壓力,如何使他喪失全部的自信心──他渴望肯定,而父親給他的更多是言語上的羞辱與暴力;他亟欲獨立自主,結局卻是終生恐婚,難逃父親龐大的身影。
這封信最終被母親退還回來,未成功交到父親手上,但仍被留存下來。它是後世讀者親近卡夫卡、認識其寫作起源的一把鑰匙,也是一個始終追尋父愛、飽受童年創傷的男孩,對父親沉重而赤裸的控訴與傾吐。
//
你幾乎沒有真正打過我,可是你的咆哮,你漲紅的臉,
你急匆匆解下的褲子吊帶,它垂掛在椅背上隨時待用的狀態,
對我來說更為糟糕。就像一個人即將被絞死那樣。
如果他真被吊起來,他就死了,一切就結束了。
而如果他必須目睹整個準備絞刑的過程,一直到絞繩已垂在面前了,
才得知自己已被赦免,那麼,他可能會為此痛苦一生。
//
★特別收錄:卡夫卡不同時期之肖像及其家族成員照片。
★名人推薦
●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專文導讀:「《給父親的一封信》不是文學作品,是卡夫卡對原生家庭的控訴。或許自覺與卡夫卡有類似經歷的讀者,能在卡夫卡的信中找到認同,因為他說過:『只是為了那些絕望者,希望才被賜予我們。』」
● 平路(作家)專文推薦:「我始終記得第一次讀到這本書的震撼。閱讀時我很年輕,想著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境,一句接一句,卡夫卡寫下如許絕望的句子?……翻開卡夫卡,段落間如果您不覺歎口氣,某些字句刺到了痛點?甚或悄悄流下淚水?那麼,經歷的或許是另一個意義的『成人禮』。回顧困擾您的父子關係,您內心將會出現通透而舒暢之感。」
● 張亦絢(作家)專文推薦:「卡夫卡對父親『既糾纏又挑戰』,對現在的讀者來說,應該是『太可疑的暗黑療癒』。然而,不同於現今的『乾淨俐落』,卡夫卡『並不直接來個過肩摔』──如何解釋?我不傾向套用『他優柔寡斷』這種浮泛說詞。我以為,卡夫卡是視他的創造者與虐待者為『自己的一部分』。因著大大忠於自我,無論多痛苦或多見笑,他都不以失憶與拒認為手段──這也是『寫信給父親』,但『非常反家書』的這封『陳情表』,值得我們思索的方向。」
● 周慕姿(諮商心理師)、凌性傑(作家)、鄭宜農(創作歌手)、蕭雅全(導演)|動容推薦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也是現代主義、存在主義文學的奠基者。
1883年7月3日生於布拉格的中產階級猶太家庭,大學攻讀法律,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後,進入勞工保險局任職,並利用下班時間專心寫作。1917年,卡夫卡被診斷出結核病,1924年病情惡化,6月3日逝世於療養院,享年40歲。
卡夫卡曾與兩人三度訂婚,又因對婚姻的異常焦慮而解除婚約,終生未結婚。
卡夫卡在世時只出版過包含《變形記》在內的幾則中短篇小說。臨終前,他交代摯友馬克斯.布洛德(Max Brod)焚毀自己的所有手稿,但布洛德並未遵守,並將其遺作整理出版,包括長篇小說《審判》、《城堡》》;書信集《給父親的一封信》、《給菲莉絲的情書》、《給米蓮娜的信》;中短篇小說《沉思》、《判決》、《司爐》、《蛻變》、《鄉村醫生》、《飢餓藝術家》、《在流刑地》等。
譯者簡介:
★譯者簡介
禤素萊
生於馬來西亞馬六甲,畢業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留學日本、德國,進修語言學、比較文學,並曾在台灣淡水短暫居住。
自小身處東西方文化匯聚之地,啟發她對語言學習的興趣,通曉中、英、德、日、馬來語。曾於聯合國「特遣北約維和部隊」擔任隨軍翻譯,專職提供軍隊語言與文化上的訓練。著有《隨軍翻譯──一本聯合國維和部隊隨軍翻譯者的文化筆記》(寶瓶文化)以及《戰地情書》(有人出版)。
章節試閱
最親愛的父親,
最近你問過我,我為何聲稱對你感到恐懼。我太了解你了,一如往常,我沉默以對,部分原因恰恰是出自於對你的恐懼,部分原因也正是解說這恐懼會牽涉許多細微末節,根本難以讓我在談話中概括。而當我在此嘗試以書寫回答,它也將是殘缺不齊的,因為就算在文字裡,對你的恐懼及其後果阻擾著我,何況素材之繁多遠遠超出了我的記憶力與理解力。
對你來說,事物往往極其簡單,至少相對於我,以及沒有選擇地,相對於許多其他人而言。事情看來是這樣的:你一輩子辛勤工作,犧牲一切,全都為了兒女,尤其為了我,我因而得以過得「奢華」,享有完全的自由去學習自己想要學習的,無須為五斗米折腰,什麼也不必操心。你未曾期待兒女的感激,你明白「兒女的感激」是怎麼回事,但起碼兒女們該有些因應之道,以顯示一點同理心。反之,我卻老是躲著你,躲到我的房間、書本裡,躲到瘋瘋癲癲的朋友群以及浮誇的想法中。我從未對你敞開心胸聊天,在教堂不曾走近你,在弗朗茲溫泉(註:Franzensbad,位於捷克西部的一水療小鎮。)我也從不去探望你;此外我也不具備家庭觀念,對生意以及你的其他事務我毫不在乎,由你去肩負工廠重責並離棄了你。我支持奧特拉(註:Ottla[1892-1943],卡夫卡最小的妹妹,也是卡夫卡最喜愛、親近的妹妹。)自身的意願,而對你卻連一根手指頭都懶得動(連劇院門票都沒給你帶來過半張),為朋友我又願意赴湯蹈火。如果你總結對我的看法,結果即是,雖然你沒指責我徹頭徹尾地不合禮數或惡劣(例外的或許是我最近的結婚意向),但卻指我為人冷酷、陌生、忘恩負義。你如此這般指責我,彷彿這是我的錯,好像我就可以像扭轉方向盤那樣,把一切轉向,而你沒有丁點過錯,若有的話,也只錯在你對我太好了。
你的這些慣性陳述我認為只有一點正確,即連我也相信,我們的疏離全然不是你的錯。但也全然不是我的錯。如果我能讓你承認這點,那麼或許──不是指一新生活的可能性,畢竟我倆都有點年紀,但至少會有種平靜,不是去終結,而是緩解你持續不斷的責難。
怪異的是,對於任何我想說的話,你算是有些概念的。例如你最近告訴我說:「我一直都很喜歡你,儘管我在表面上看來待你不如其他為人父者,但這也只因我無法像他人那樣偽裝自己而已。」總的來說,父親,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對我的好意,但我認為這句話不正確。你不偽裝自己,的確如此,但想藉此斷言其他父親是在偽裝自己,你要麼就是不容討論地自以為是,要麼──在我看來確實是──在暗示,暗示我們之間出了點問題,而你有份引起,卻不具罪責。如果你真是這意思,那我們就想法一致。
我當然不是說,我之所以是這樣的我,乃因透過你的影響而成。這未免太誇張(而我竟也傾向於如此誇張)。即便我在成長過程中完全擺脫你的影響,我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合你心意的人。我當會是個軟弱、膽怯、猶豫不決、焦躁不安的人,既不是羅伯特.卡夫卡(註:Robert Kafka[1881-1922],卡夫卡的堂哥,叔叔菲利浦之子。)也不是卡爾.赫爾曼(註:Karl Hermann[1883-1939],卡夫卡的大妹艾莉之夫婿。),不過一定有異於真正的我,我們彼此或許會相處得很棒。我會因為有你這樣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作為我自身的岳父(儘管有些猶豫)而感到幸運。唯有作為父親這點,你對我而言卻過於強大,尤其是我的弟弟們早夭,妹妹們的到來又間隔得久(註:卡夫卡是家中長子,兩個弟弟皆在一歲左右夭折,六年後,三個妹妹艾莉[Elli, 1889-1941]、瓦莉[Valli, 1890-1942]、奧特拉相繼出生。),我首當其衝還必須獨自面對,我對此太無力承受。
把我們兩相比較:我,簡而言之,是一個帶有些許卡夫卡脈絡的洛威(註:Löwy,卡夫卡母親的娘家本姓。),但這脈絡卻並非受到卡夫卡式的生命力、事業心、征服欲所激發,而是經由洛威式的鞭策,偷偷地、羞怯地,朝另個方向發揮,還經常無以為繼。你則是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胃口佳、聲線宏亮、能言善道、自滿、對外界具優越感、有毅力、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大方,當然也具有與這些優點相關的所有失誤與弱點,而其中你的脾氣以及偶發的躁鬱驅使你這樣。就我而言,如果拿你來與菲利浦叔叔、路德維希叔叔、海因里希叔叔(註:Filip Kafka[1847-1914]、Ludwig Kafka[1857-1911]、Heinrich Kafka[1850-1886],卡夫卡父親的兄弟。)比較,你在世界觀上也不完全是個卡夫卡。這是奇怪的,對此我也不太明白。他們全都比你快樂、活潑、隨意、輕鬆,不像你那般嚴厲(順便說一下,這方面我倒是沒少繼承你,而且還把這份傳承管理得太好,但我本性不具備你所擁有的那些必要的平衡力)。另一方面,你在這點上也算經歷了不同階段,或許快樂過,直到你的孩子們,尤其是我,讓你失望,讓你在家感到壓抑(來了外人,你就另個模樣)。你現在或許又變得快樂了,因為你的外孫和女婿,再度給了你那些你自己的兒女們,瓦莉或許除外,所不能給的些許溫暖。無論如何,我們截然不同,並且在這差異裡互為威脅。以至於如果有人去預估,像我這樣成長緩慢的孩子以及你,一個成年人,會如何對待彼此,可想而知,你會輕易把我踩在腳下,踩得我一無所有。當然這並沒有發生,生命無法算計,但是也許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我一再請求你不要忘記,我丁點都不曾認為過錯在你。你對我的影響是不由自主的,只不過你必須停止認為我之所以屈服於這影響,是由於我這方面的惡意所造成。……
(全文未完)
最親愛的父親,
最近你問過我,我為何聲稱對你感到恐懼。我太了解你了,一如往常,我沉默以對,部分原因恰恰是出自於對你的恐懼,部分原因也正是解說這恐懼會牽涉許多細微末節,根本難以讓我在談話中概括。而當我在此嘗試以書寫回答,它也將是殘缺不齊的,因為就算在文字裡,對你的恐懼及其後果阻擾著我,何況素材之繁多遠遠超出了我的記憶力與理解力。
對你來說,事物往往極其簡單,至少相對於我,以及沒有選擇地,相對於許多其他人而言。事情看來是這樣的:你一輩子辛勤工作,犧牲一切,全都為了兒女,尤其為了我,我因而得以過得「奢...
推薦序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九一九年,卡夫卡想與新戀情茱莉.沃里契克(Julie Wohryzek)結婚的事,受到他父親強烈的反對,讓卡夫卡感到憤憤不平,這就是《給父親的一封信》的起因。通常我們寫信,不論寫得再長,信的結尾總是攤牌的時刻。《給父親的一封信》也是一樣,卡夫卡在前面提了許多父子關係的陳年往事,但到了最後,還是點到整件事的關鍵,卡夫卡寫道:「但像我們現在這般情形,婚姻的大門對我是已經關上了,因為那恰恰是你的個人領域……只有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領域,才可能是我的生活。而根據與你高大身軀一致的想像,這樣的領域寥寥無幾,無法給我多大慰藉,婚姻尤其不在其中。」
父親巨大的身軀壟罩了卡夫卡的生命。巨大的身軀這個意象,是源自卡夫卡童年的經驗。當然,每個父親的身影都是巨大的,只是他們的父親同時也是慈愛的,但卡夫卡覺得他的父親不是。在信的一開始,卡夫卡第一次提到巨大父親的段落,是「那個巨人,我的父親,那終極權威,會幾乎不需要理由地在三更半夜把我拖出被窩並拎到屋外過道去,對他而言我什麼都不是。」
卡夫卡並不認同這樣充滿巨大身體力量的父親,為了對比自己與父親的不同,他在信的開頭提到:「把我們倆相比較:我,簡而言之,是一個帶有些許卡夫卡脈絡的洛威。」卡夫卡在這裡展示了對母系的認同,洛威是母親(本名Julie Löwy)的姓氏。卡夫卡強調,母親這邊是「洛威式的鞭策,偷偷地、羞怯地……」,而父親這一方剛好相反,「你則是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胃口佳、聲線宏亮、能言善道、自滿、對外界具優越感、有毅力、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大方……」
除了母系這邊的洛威,我們不能不提另一個洛威,那是卡夫卡年輕時認識的猶太劇團演員洛威(Jizchak Löwy)。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參考《卡夫卡日記》(商周,2022),您將會發現,從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卡夫卡在這段期間的日記裡,寫下了大量他與洛威的密集互動。洛威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他所參與的猶太劇團當時於布拉格的薩伏咖啡廳(Café Savoy)巡演,卡夫卡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他的觀戲經驗。後來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個猶太劇團的演出,對正往文學之路邁進的卡夫卡在創作上,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比如,卡夫卡於一九一三年發表的小說《判決》,其結構與內容上就與當時猶太劇作家戈爾丁(Yakov Gordin)的另一部作品《神,人與魔鬼》(Gott, Mensch, Teufel)類似,卡夫卡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提到他去聆聽洛威朗誦此作。
卡夫卡將洛威視為好友,他的纖細與敏感,讓卡夫卡覺得像是找到新的同盟,可以一同對抗父親。卡夫卡對父親的負面經驗,也來自父親對洛威的不友善。卡夫卡邀請洛威來家裡玩時,父親卻對客人指指點點,很不禮貌,讓卡夫卡相當生氣,他在日記提到此事時說:「……寫著寫著我簡直恨起父親來了。」卡夫卡的氣憤,不是沒有原因,因為他認同洛威,而父親對洛威的否定,讓他看清楚自己與父親的差異。卡夫卡寫這封長信的一九一九年,當時他已經三十六歲。可是八年前父親羞辱洛威一事,他依舊懷恨在心,在信中他就抱怨說:「像意第緒演員洛威如此天真無邪的人,也不得不為此受罪。在不了解他的情況下,你用我已忘記的可怕方式,把他比作害蟲。」這件事就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卡夫卡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因父親說洛威壞話,而跟他頂嘴的事。
「害蟲」,卡夫卡用了Ungeziefer這個字,這個字也是小說《蛻變》提到那隻蟲時,所用的德文字。父親罵我最好的朋友是害蟲,那不就等於間接說我也是一隻害蟲嗎?我想卡夫卡內心的潛台詞應該是如此。
這封信的另一個重要的隱藏訊息,是關於他最小的妹妹奧特拉(Ottla)。在卡夫卡的妹妹當中,就屬奧特拉跟他最親。但是奧特拉與天主教徒約瑟夫.大衛(Joseph David)交往一事,跟父親起了激烈衝突(兩人最後於一九二○年七月結婚)。卡夫卡在信中替奧特拉抱不平,因為奧特拉也是屬於母系這一邊,是他的盟友,卡夫卡在信中形容奧特拉:「她那方面是洛威式的反叛、敏感、正義感、不安。」
卡夫卡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或十三日間,寫下這封一百零三頁的手稿之後,他再打字成四十五頁的長信,並請他的母親轉交給父親。但是卡夫卡的母親並沒有依照兒子的想法,最後是將信退還給他。雖然卡夫卡與茱莉的婚約於一九二○年七月取消,但他隨即又談起了戀愛,這次是捷克記者米蓮娜(Milena Jesenská),卡夫卡寫了大量的情書給她。當然,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一個重視俗世金錢價值的父親,自然很難忍受自己的小孩以文學、哲學或藝術為人生志業。根據美籍猶太裔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看法,班雅明與卡夫卡在面對原生家庭的糾結,有不少類似之處。她為《啟迪:本雅明文選》寫的導言提到:「這個時代的文學中充滿了這種父子衝突。如果佛洛伊德是生活在其他國家,使用其他語言,而不是在提供他病例的德國-猶太人社會環境進行研究,我們可能永遠不會聽說伊底帕斯情結。」
《給父親的一封信》不是文學作品,是學法律出身的卡夫卡對原生家庭的控訴。如同卡夫卡在兩個洛威身上尋求支撐,或許那些自覺與卡夫卡有類似經歷的讀者,能在卡夫卡的信中找到認同,因為他說過:「只是為了那些絕望者,希望才被賜予我們。」
※另有作家平路、張亦絢精采專文推薦,詳見本書。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九一九年,卡夫卡想與新戀情茱莉.沃里契克(Julie Wohryzek)結婚的事,受到他父親強烈的反對,讓卡夫卡感到憤憤不平,這就是《給父親的一封信》的起因。通常我們寫信,不論寫得再長,信的結尾總是攤牌的時刻。《給父親的一封信》也是一樣,卡夫卡在前面提了許多父子關係的陳年往事,但到了最後,還是點到整件事的關鍵,卡夫卡寫道:「但像我們現在這般情形,婚姻的大門對我是已經關上了,因為那恰恰是你的個人領域……只有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
目錄
目錄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卡夫卡家族照
給父親的一封信
【推薦文】你與我一直在決鬥? ◎平路(作家)
【推薦文】並不直接來個過肩摔:罪玫瑰的害怕權與話語力 ◎張亦絢(作家)
目錄
【導論】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卡夫卡家族照
給父親的一封信
【推薦文】你與我一直在決鬥? ◎平路(作家)
【推薦文】並不直接來個過肩摔:罪玫瑰的害怕權與話語力 ◎張亦絢(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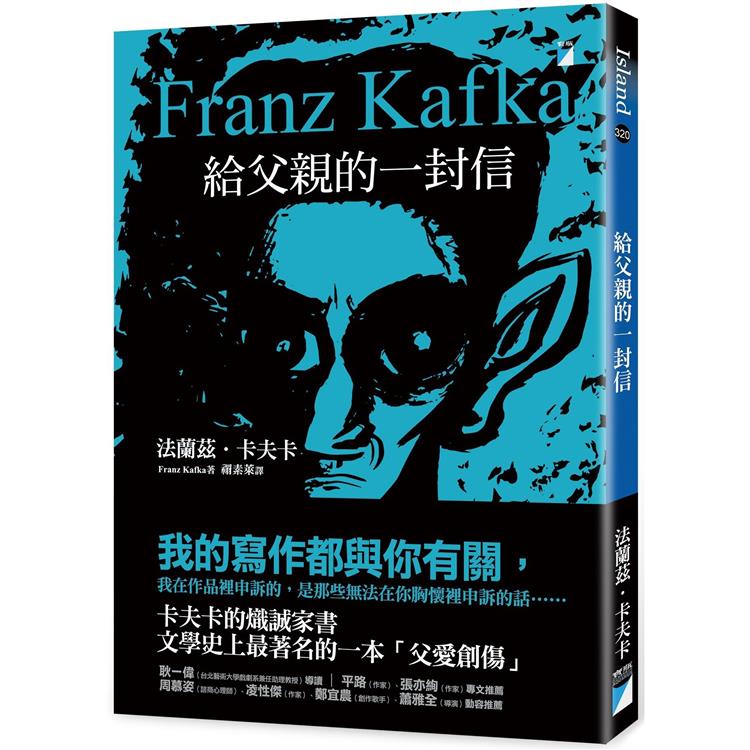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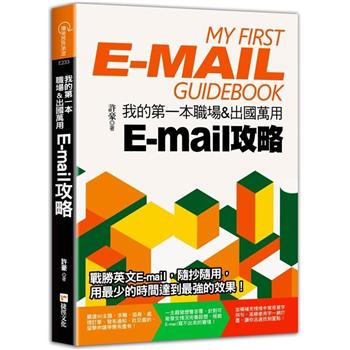







![114年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專業軍士官] 114年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專業軍士官]](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