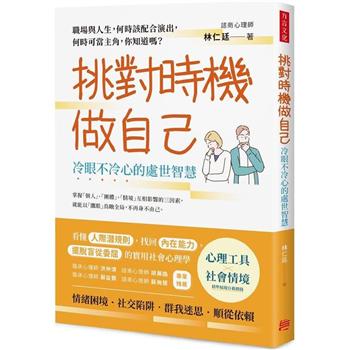代序
八二華年
⑴
惜別晚宴就要開始了,一起前來香港開了四天會的朋友在大廳入口處排隊,等待服務人員帶我們入座。
「你是紫荊桌!」
我愣了一下,怎麼她不是說「第幾桌」,而是說出一個「花名」來。我朝名單上一望,原來大廳中十幾桌,桌桌都是花名,什麼牡丹啦,杜鵑啦,玫瑰啦,百合啦,丁香啦,芍藥啦,薔薇啦,紫羅蘭啦……
這香港,實在有吃的文化,不說第一桌、第二桌而代以花名。讓我恍然以為自己錯進了大觀園,參加了賈府的花園野餐……
不過正胡思亂想,服務小姐已把我帶到位子上了,我忽然發現不妙,這紫荊是首席(香港以紫荊為「港花」)。吃飯貴在「自在」,吃飯而坐在大人物中間,其實是有點礙手礙腳的——當然,這是我的偏見。
待我剛要坐下,對面有位先生就對我發問了,我一時有點愕然——其實,不是他想問,他是代他身旁的一位靦腆不好意思開口的朋友問的:
「他,他想問你,你高壽多少……」
這在洋人,不知為什麼,算是不禮貌的提問。但因我是華人,對方也是(雖然分屬岸之一方),華人提這問題,我算它是善意的。
「我,八十二歲,我常笑自己是八二年華,並且常常故意講錯,說成是『二八年華』……」
大家都笑了。
⑵
首席還算好,並沒有令我害怕的官方氣味,尤其令人難忘的是有位具一半蒙古血統的施先生非常能唱,我可以近距離聽他那既潤又亮的嗓子,且因其人已走過一段人生到了中年,因而能在歌聲中有些溫柔和滄桑的餘韻。這份耳福十分值得珍惜,何況席間還有人提供了一瓶上好茅台。
⑶
不過,我其實也很想回問一下那位坐在我對面的「提問人」:
「你為什麼會提這麼一個問題呢?是不是看到我拄著一根拐杖還跑前跑後,還被指定在大會短講,還對事情提意見,還跟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高談闊論。其實,你不知道,我在大會正常開會之外,還『被朋友抓差』,另做了兩場演講,其中一場是對香港中學語文教師的一個協會。我比你看見的更忙碌、更操勞,我晚上在旅店還要看書、還要寫稿……
「你是想問我:『這麼老了,幹麼活得這麼辛苦……』嗎?」
這問題,我在席間沒好意思開口,原來,我跟那發問者一樣容易靦腆怯場。
⑷
「二八」其實指十六歲。(不過,八二不也是十六嗎?)
更早的時候,南朝鮑照有詩謂:
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
指的卻是十五和十六夜的完美月圓。俗語說「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十六夜的月色的確強碩飽滿。
但,十六,也指美少女的稚齡初熟之美。
白居易的詩中有:
見人不歛手,嬌癡二八初。
歛手,是縮手,是古代女性見人時表示謙抑自歛的肢體語言(平劇中,女子跟人打招呼時尚有這動作)。白詩中,此女尚年少,不懂女子必須謙卑自抑的社會陋習,只傻傻地、大剌剌地、毫無心機自自然然地站著,因而反具一分天真絕色。
二八是女子的妙齡——不過,我認為,八二也是。
⑸
唉,那位席間發問的朋友,今夕席散之後,我今生今世會不會有機會再見到他,其實也很難說。我姑且假定了他想問的事,也順便想好了回答如下:
我出生於一九四一,今年恭逢二○二三,無功受祿,我糊里糊塗就活到八十二歲了。一個八十二歲的人該怎麼活,我也不太知道。如果是孔子,就沒有這問題,他七十二歲就走了。蘇東坡也沒這問題,他只活到六十四。日本時代的台灣人更慘,他們平均年齡只得三十九(另有一說是四十),還不到我的一半,我好像應該有點為活這麼久而自慚。
但我要活到幾歲呢?這話可不是我說了算。
一捆柴,能在山村冬夜的火爐裡燃燒多久,能提供多少芳馨和溫暖,很難預測。柴的本質、火爐的造型和製作、生火和烤火之人的技巧和維護、當日的風向和溫度、濕度,以及火頭滅了之後仍然燜在灰裡的餘燼可以延捱其熱度多久,都不是事先可以掐算的。
⑹
如果上帝自己親自來垂詢:
「我問你,在這個人世間,你還想停竚多少歲月?」
我會狡獪地回答:
「隨祢,祢看著辦吧!我不想自作主張。」
「奇怪,你都不想長壽嗎?你有完善的養生規劃嗎?不要都賴在我頭上。」
「長壽,我也不反對啦!但我不刻意。我只想簡單吃,安心睡,不煩惱。有時去做個體檢,對能令我愉快的事就熱心去做。但,什麼會讓我愉快?我認定『幫別人』讓我愉快——不過,這件事,可能有人認為是勞瘁傷身且令人折壽的呢!事實如何?我也說不出其是非。
「總之,活到幾歲,由祢定奪——但,怎麼活,我自有主意。而這主意,其實也是祢給我機會從書本和前人的榜樣中受到教育而學來的,那就是原則上『為世人而活,只留下一點點資源給自己』。譬如說,在自家陽台,用花盆加上吃橘子時留下的橘核,自種幾棵橘子樹,春來時,欣賞它新抽的粉嫩的小綠葉,恍然中,竟以為那就是我自己今年的新容顏……」
上帝無言,只在我肩頭拍了一記,輕輕無感的一記,丟下介乎有聲和無聲之間的一句話:
「好吧!孩子,你就照你領會到的法子去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