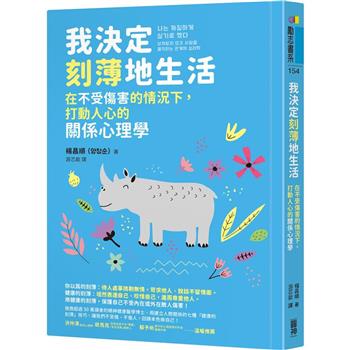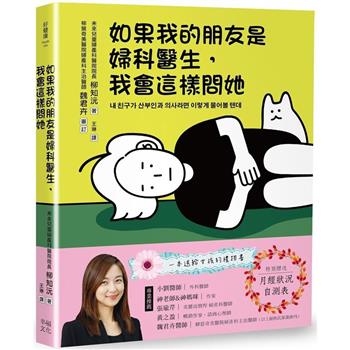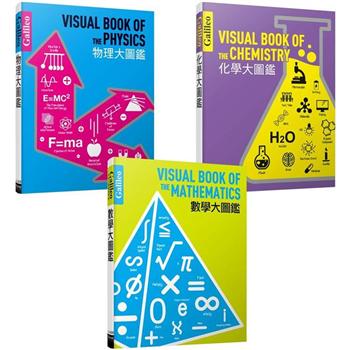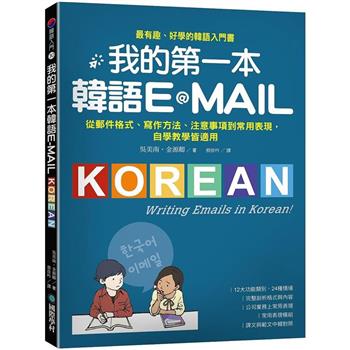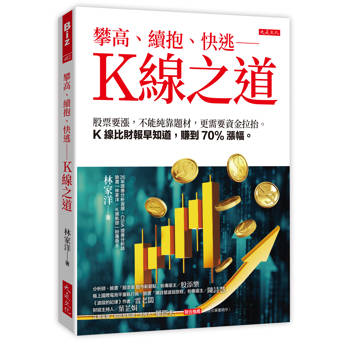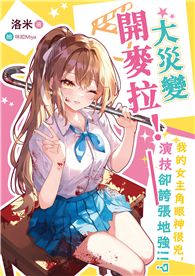◇⊱—「讀空氣」文化的研究經典—⊰◇
「日本人是空氣在決定事情!」
「讀」空氣,是現代日本人立足世間的基本,
是具有獨特性的心靈秩序與傳統思想,
難以名狀如空氣般存於周身的群體默契,
不僅約制個人言行,也是社會運作方式,
理解日本社會性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就由與周遭他人的「空氣」框架開始。
「日本人是空氣在決定事情!」
「讀」空氣,是現代日本人立足世間的基本,
是具有獨特性的心靈秩序與傳統思想,
難以名狀如空氣般存於周身的群體默契,
不僅約制個人言行,也是社會運作方式,
理解日本社會性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就由與周遭他人的「空氣」框架開始。
「空氣」,擁有「只能這麼做」的權威影響力,
往往最終拍板的,「是現場空氣,而不是人」。
人們高舉實證邏輯與科學理則等作為判斷事物所據,實則經常有「某種事物」凌駕於各種論理,從大問題到日常小事,甚或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某種事物」都成為控制人們言行的標準。
「空氣」確實是呈現某種狀態的精準表達,人們被無色透明而難以在意識上確認其存在的「某種事物」控制著,這個擁有絕對威權的妖怪,更因無法透過邏輯說明,所以才以「空氣」來稱呼。
察言觀色、審時度勢、揣忖臆測……旁棄理據上的客觀情勢,服從「空氣」形成決斷,是日本社會的隱藏體制。空氣宛如「本能」附在人們身上,以此形態控制每個人。而被蔑稱白目的KY(讀不懂空氣者),輕則處境尷尬、人際不佳,重則在群體中成為眾矢下的異類。
本書作為日本「空氣」研究的開基之作,細剖傳統源流與近代發展之脈絡,並與異國的社會集體性做出比較。是「日本人論」書類中,不可缺讀的一本。
「真正能夠理解『空氣』時,就擺脫了空氣的控制。」――山本七平
本書特色
本書出版於一九七七年,是首部全面解析日本「讀空氣」文化的經典著作,即使四十多年後的今日,仍是日本人甚至是外國人理解日本集體決定論的必讀經典。山本七平認為戰後的日本人連自己都無法理解自身遵從的規範是基於哪種傳統而來的,因此連空氣實際上如何影響、拘束人們等都搞不清楚,就算被控制,也無法掌握如空氣般的操控者。透過這本論著,山本嘗試探討潛匿於日本的傳統思想與內心秩序,以及基於這樣的背景建構出來的隱藏體制;甚至提出透過理解,得以反過來控制這以往控制自己之物。
專文導讀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藍弘岳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