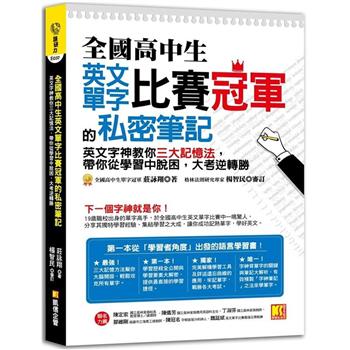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親愛的艾格妮絲〉
整體來說,這是一場成功的葬禮。
那天早晨原本灰暗無風,但當我們去到戶外的墓地,太陽就撥開了雲朵露臉,透過榆樹的黃葉投下不規則形狀的光點。
艾瑞克一定也會喜歡。秋天。天色豁然開朗,在空氣中留下爽利的氣息。清新而不冰冷。往莫納方向的田野已經收割了,但還沒有犁過。遠方的一個農夫正在焚燒雜草。
主持葬禮的牧師名叫席德馬克,是個高瘦蒼白的男人;當然,我們前一週就碰面過,議定儀式的流程。他剛來到這個教區,脊椎似乎因為某種傷病而變形,使得他行動笨拙,幾乎是瘸了腿,也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老邁。但他的臉龐光采煥發,並且將份內工作處理的完美無缺。
我們總共有二十幾人參加。孩子們當然來了。他的母親和她的隨行者;女性好友和那位粗魯的護士。
碧翠斯和魯道夫。
賈斯丁。
漢德瑪家,他們不智地帶了小孩一起出席。孩子不過十或十二歲大;一個害羞的男孩,和一個牙齒歪斜、眼神緊張的女孩。帶他們來有什麼好處?兩個孩子和艾瑞克都扯不上什麼關係,就我記憶所及,可能就只見過他兩、三次。
有一位肯定是艾伯特‧坎納,和幾個我沒見過的現職同事。精確來說是四個人,兩男兩女。還有負責在教堂裡朗讀悼詞的孟森醫師,現在到墓地邊也忍不住要說個幾句。
他說著清朗的秋日,和我們人生在世的時光。說細心敏銳是艾瑞克的個性特色,穿透陽光的雲朵也見證了他的這一面。
空談。
我有點累了。在這個由悼唁者、半是悼念半是圍觀的群眾、以及只是為了例行原因而來的人圍成的黑色圈子裡,一陣疲憊淹沒了我。也許是真切的悲痛。不盡然是為了艾瑞克而哀痛,而是哀悼生命。
生命的不公與盲目。那些被我們埋藏掩匿的虛偽謊言,只要時日一久、只要我們一不留心,還是會找上我們。
我沒有哭泣。整場葬禮中,我的眼睛連一滴淚水也沒有擠出來。我不在乎旁人會作何感想,但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使人麻木遲鈍的藥物,所以我的表現也許並不罕見。我沒有和任何人對話。只有技巧性、確認性質的眼神交流而已。握手。輕輕的擁抱,以及虛有其表的點頭致意。
他年少時的故友和划船俱樂部的友人負責抬棺。總共有四人,我認得其中三個人,但不知道名字。他們都住在格謝姆這邊,據牧師說,他們是自告奮勇來的。
然後還有赫妮。
我的本意不是要把在場的每個人條列出來,但現在我發現,我就是這麼做了。
赫妮‧德嘉朵。
她在教堂裡穿的是黑色長袖,但我們來到戶外之後,她肩上披了一件深紅的斗篷。我記得她以前向來習慣穿紅色,不盡然是正紅,但總是帶有紅色調。有時候是惹眼的鮮紅。暗紅的上衣或圍巾。我個人偏好藍色和冷色系。早在高中的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區分各自的領域:赫妮是紅色、黃色、褐色。我是藍色、水綠、冷色。只有綠色是共通的,但我們還是分據光譜的兩端。稍後,大概是在大學的第一個秋季學期吧,我們一起去找了個色彩分析師,對方也贊同我們直覺性的選擇,將一塊塊不同顏色的布料舉到我們訝異的臉孔旁,談論我們不同的膚色特性。膚色人格,簡直像是某種玄學。
赫妮她看起來出人意料地年輕。苗條而健康;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點令我意外,但我的感覺就是如此。當然,她是單獨出席的;她的丈夫和孩子住在郭特堡,沒錯,她的兩個女兒我都沒見過,但是她們的受洗典禮邀請卡被我貼在某本紀念冊裡。
過了這麼多年又再重逢,我們卻沒有交談,感覺有點奇怪。然而,我有種直覺,覺得她會聯絡我。我不知道原因會是什麼,但如果我猜錯了,我會非常意外。畢竟,以兩個不是親戚也不是愛侶的同性友人而言,我們曾經無比親密。雖然已經過了這麼久,還是有些徵兆和小小的暗示,能夠在我們心中觸動比認知和語言更深的層面。當然是這樣的。
賈斯丁問我需不需要他留下來過夜,但我婉拒了。賈斯丁這個人善良又體貼,儘管他的行事風格有點欠缺氣質,我一直挺喜歡他,但我想要獨處。就我一個人和狗狗們,壁爐裡生著火,扶手椅拉到窗邊。配上一兩杯波特酒,欣賞暮色籠照庭園、樹型扭曲並經過修剪的蘋果樹、黃楊樹叢、還有靠近莫納方向的軟土坡。伴著相簿和回憶度過全然安靜的幾個小時。也許我還會抽根菸,我已經好幾年沒有抽菸的習慣了,但這是個特別的日子,我也有一兩包菸在手邊。
我下個星期也請了病假。課堂一半延後了,一半交給布魯恩(Bruun)代課。一如往常。把濟慈和拜倫交到他笨拙的手裡真是令人惋惜,但是別無他法了。離口試時間只剩下三個星期,所有進度都必須在十五號以前教完。
一切終於結束了,感覺不錯。當然,我一直知道自己有一天會孤身一人。艾瑞克比我大了十八歲;我選擇他,並不是為了熱戀激情,他是屬於我的藍色。但是他才五十七歲,從來沒有徵兆顯示他會英年早逝,孟森的悼詞裡也強掉他還有許多未竟之業。他說,學者並不是會被年歲和日常瑣事消磨衰弱的族群。我明白他指的既是自己──他差不多也七十歲了──,也是某個在場的同僚。
但就像他們在薩爾布呂肯的家裡說的,艾瑞克不得不停下腳步。他的終點到了。
我坐在扶手椅上,眼睛半看著外面的暮色和庭園,半看著室內的爐火和書本。多年來,這裡累積了不少藏書。接下來幾天,我要重新整理一下,我心想。把沉重的醫學書移到閣樓,讓文學作品放到更顯眼的位置。
這只是我得費心處理的眾多瑣事之一。但事情得等到明天。現在我只想坐在這裡,好好休息。
回想過去、翻閱相簿。我想起了貝林的幾句詩。
我想念母親微微的汗味──
和他們在開學第一天
逼我穿上的短褲。
我想念烏蘇拉‧李平斯卡亞,還有精神飽足地醒來
面對一片空白的夏日時光。
但我最想念的是那無法觸及的煙霧
來自我不曾在咖啡館吸到的香菸
我這就點了一根菸。一股壓抑下的滿足感在我體內搏動。
彷彿我早已預測到的某件事終於即將發生。
狗狗們睡在爐火前,他們看起來也並不想念他。
※
致:艾格妮絲‧R
賈爾達別莊/格謝姆/
九月二十六日寫於郭特堡
親愛的艾格妮絲,
請原諒我在你恢復獨居之後這麼快就寫信來,我希望你不至因為喪事而悲痛過度。我非常開心能再見到你,儘管我當然希望我們不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相見。而且,既然我都到場了,我當然應該跟你說幾句話的,但是有某原因讓我卻步了。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有時候我們的行動就是會被某種無以名狀的力量所阻擋。不是嗎,艾格妮絲?
但是,那場葬禮辦得美麗而莊嚴,我不認識你的丈夫,所以當然說不準儀式是否也像英國人常說的那樣「得體」。
總之,我希望能跟你恢復聯絡,已經過了這麼多年,我覺得你不該這麼輕易地一刀兩斷。我們曾經如此親密,親愛的艾格妮絲。
那麼,我可以寫信給你嗎?把關於我自己和家人的一些事告訴你?如果你願意回信的話?
我們或許可以先通信,再看看之後如何。我很難習慣電子郵件,那東西好輕浮又好膚淺。
如果你不願重敘舊友之誼,當然也可拒絕無妨。
期盼你的回覆。
赫妮敬上。
致:赫妮‧德嘉朵
百利金路二十四號/郭特堡/九月三十日寫於格謝姆
親愛的赫妮,
老天,你講得好像我們是八十歲的老人了!
你當然可以寫信來,我也樂於回信。我相信我們會有不少話題,但既然是你起的頭,我就讓你先說吧。
別猶豫了,請快點寫信來吧,我們有十九年的時光要彌補呢!
艾格妮絲敬上
※
心中存好意,早晚有回報。
那是我們在郭特堡的第二天,而儘管我當時只是個瘦巴巴的十一歲小孩,我也知道她在說謊。
或者不是。這個紅頭髮的女孩子名叫赫妮,昨天跟她的媽媽來拜訪過,當時我們正在拆開僅有的一箱行李。她完全搞錯了。她完全不了解人生是怎麼一回事,不了解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但我沒有反駁。年幼的我找不到詞彙來表達這些概念,何況這也不重要。當時是傍晚,我們站在橋上,往下看著棕色的河水;我們的媽媽叫我們出來散個步,讓赫妮跟我介紹一下附近的環境。我媽生性多疑,卻對赫妮抱有那種一見如故的信任。
而且赫妮的表現的確教養良好又可愛迷人,我不否認。
而且李子果醬是好鄰居之間彼此饋贈的理想禮物。
聰敏的笑聲,真誠的目光。
心中存好意,就是這樣。
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回答的,也許我什麼都沒說。我們在家附近散步,路線歪歪扭扭。遊樂場。鐵道邊的亨格巷。克林格路兩旁的商店。我們在她叔叔,屠夫史密特家停下來打招呼,他給了我們一人一根白臘腸和一個硬幣。我們在岔路口轉角的菸草店買了口香糖。
然後是教堂和墓園,我們邊走邊看那些墳墓:赫妮的祖父和祖母葬在這裡,她自己有一天也會在這裡有一塊墓地;這是一個佔地廣闊的家族墓園,容得下好幾代的成員。
史騰普路、加森路、雅各巷,諸如此類的路名。然後是瓦曼小學,赫妮已經在這所學校待了五年,我九月份也要入讀。那是一座古老的石造堡壘,橡木大門上寫著一句拉丁語銘言。Non scholae sed vitae discimus! 赫妮背頌道,然後我們一起唸了幾次,好讓我坐在課桌後聽龐皮斯校長、瑪蒂森老師和駝背的小裁縫師教課前,就熟記這句話。
Non scholae sed vitae discimus!
我們是為了人生而非學校學習。
但我們現在懸靠在橋梁的欄杆上;這座橋叫作卡爾‧艾格斯橋。赫妮不知道這名字是怎麼來的,也不知道卡爾‧艾格斯是誰,但這條河是叫作納卡河。它流過我們所在的這個區域周圍,至少從東到北,是我們和傑林市之間的界線,那是個跟這裡完全不同的地方,赫妮對它一無所知,只知道她的表親莫里茲搬去地中海邊的馬賽以前就是住在那裡。搬家是為了莫里茲惡化的健康狀況著想,但他才八歲多不滿九歲的時候就死了,所以地中海說穿了可能也不如傳言中的那麼好吧。
也許他不夠心存好意,我想道,但沒有說出來。我把口香糖吐進流動的河水裡。
「你不能把口香糖吐到水裡啦,」赫妮說,「可能會有魚吞進去然後就窒息了。」
魚會窒息才有鬼呢,我心想,牠們又不呼吸。
但我也沒有說出來。
搬到郭特堡的只有我和我媽。我爸和我哥還是住在薩爾布呂肯的史林格巷,雖然比我大三歲的克勞斯一直跟我處不來,剛搬家的這幾天,我還是好想念他,想得胸口發痛。
我在七月一日發現我爸媽要離婚了,整整一個月之後我們就出發去新家。他們在丟下震撼彈以前就把整件事仔仔細細計劃好了:我們當時在克魯斯餐廳吃飯,我不知道父母告訴小孩自己要分居的時候帶他們上館子,到底算不算稀奇。但他們的態度非常和氣,不管對彼此或是對克勞斯和我都是,這一點不容否認。他們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但他們現在就是這樣了,事情就是演變成這樣了。人生有時候就是會如此發展,活在世間就是多苦多難,你也沒辦法控制,等等等等。我點了整份菜單上最貴的主菜,比目魚佐白酒醬時蔬,他們毫無異議地接受了。
爸爸和克勞斯會留在這裡,他們在吃甜點──野覆盆子鏡面蛋糕加柑橘雪酪,搭配糖漬榛果及糖粉──的同時如此解釋,在工作和學校方面,這樣安排最好。媽媽已經在郭特堡跟一位名叫馬汀斯的牙醫找到新工作,在伍瑪路上找了一間公寓,有四個房間和一個廚房。我會有自己的房間,裡面有磁磚壁爐,還有面向公園的景觀。
幾週後,我們打包行李時,我媽才提起我爸已經有了一個交往將近三年的情婦。
我哭了十天。至少前十天我都是哭著入睡的。然後我就停止不哭了,換成胸口隱隱作痛,就像我想到克勞斯的時候一樣。
我的肚子也不對勁。肚子裡面好像有蝴蝶在亂飛,有些天便秘,有些天腹瀉。
我的房間裡真的有一座磁磚壁爐,但是裡面是不可能生火的。煙囪管在五十年代就封起來了,房仲溫特先生說。煙囪有裂縫,如果餘燼跑出去,整棟樓可能一眨眼就燒起來了。
我覺得就算整個郭特堡一眨眼就燒起來,對我來說也不痛不癢。我不想住在這裡,我討厭這個城市,如果我們被活活燒死,那倒還是解脫呢。我就永遠不用去新學校上課,也永遠不用再看到那個綁著傻氣的髮辮、一臉聰明笑容的鄰居女孩了。
但我在這裡晚上也不哭。只是胸口發痛,肚腹翻攪。
對了,她叫作艾爾曦(Else),我爸的那個新歡。她已經搬進史林格路的房子跟他們同住了。她的女兒住在我的舊房間裡。
最糟的是,那個女兒的名字也叫做艾格妮絲。
※
致:艾格妮絲‧R
賈爾達別莊/格謝姆/十月四日寫於郭特堡
親愛的艾格妮絲,
謝謝你這麼快回覆,也謝謝你不介意我們用這樣的方式重新聯絡。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過了這些年讓我有這種感覺,但不管怎麼算,艾格妮絲,我們都得承認,我們已經開始步入中年了。我二月就要滿四十歲了──而你到了五月一日的生日也是,我記得好清楚。你記得你在郭特堡這裡過的第一個生日嗎?我送了你一本日記。你說你一個字也不想寫,但是九月開學的時候,你給我看你已經寫到要買一本新的了。
雖然我不覺得自己老了,一點都不,但看著女兒們,我就感到時光飛逝。芮雅已經十一歲了,跟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是同個年紀──貝蒂十二月時也要九歲了。
而大衛去年春天就四十七了,他才是我之所以寫信給你真正的理由,但容我稍後再提。一下下就好,我覺得我必須用迂迴的方式接近話題的核心,我們有時候就是這樣相處的,你說對吧,親愛的艾格妮絲?
但是,至於葬禮,我完全沒有猶豫,一在報上看到訃聞,我就知道我非出席不可。當然這不是為了你的丈夫,我並不認識他,而是因為我想再跟你見面。這些年來,我當然交了不少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有,別誤會了──,但是從童年就相識的人,總是格外特別。你說對吧,親愛的艾格妮絲?不管過了多久,不管經歷了多少事,我們彼此之間總是有某種連結。我真心希望你懂我的意思,艾格妮絲,也希望你跟我有相同的感受。雖然我見到你的時候說不出話。
是的,我和大衛的社交生活現在依舊活躍;自從他當了電視劇部門的主管,總是有雪片般的聚會邀請函飛來,我們至少每週請人來家裡作客一次。但這也令人厭倦,艾格妮絲,多麼令人厭倦。這麼多的微笑,這麼多技巧高竿的搭話專家,還有不請自來的傾訴,都會讓你覺得劇場就這麼搬進了你的家、你的生活,哪怕你根本不想要。它滲入你的骨髓,鑽進你的皮膚,洗也洗不掉......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說什麼,艾格妮絲,也許我表達得太不清楚了。
我跟大衛一結婚,我就把自己在演藝方面的企圖心束之高閣;他認為一個家裡有一個戲子就夠了,而我也承認他說得沒錯。反正,我在事業上能夠活躍的時間也不多了,我們一直不缺錢,我也為了照顧女兒在家待了快十年。但是我從一月開始幫布姆與克里斯戴夫事務所工作,在柯林路上,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做法語和義大利語的翻譯,不是什麼高技術的工作,但是薪水不錯,而且能夠利用到以前花了那麼多時間學習的技能,令人很有滿足感。而且,知道自己在必要時能夠獨立自足,也是很不錯的。
但女兒才是我的一切,艾格妮絲,我想強調這一點。就我所知,你還沒有子女,我不知道這是出於你的選擇,或者該說是因為生理因素而放棄了這個選項。每個人各有不同,當然也要各找各的路,就像老尼格倫教授以前說的。你還記得他嗎?我想他是瑞典或挪威人。
芮雅和貝蒂也非常不同,雖然她們同父同母,而且出生以來都生活在同樣的環境。芮雅精確、實際又有企圖心,貝蒂則是個夢想家。幾乎就像是硬幣的兩面──或是像陰和陽的概念,雖然兩個都是女孩子。我對她們的愛也是一樣的,也許主要是因為她們兩人互補得如此完美。前幾天我突然想到,她們有點像是你和我,艾格妮絲,我們相處的樣子──或者至少是我們以往相處的樣子。你當然是芮雅,我就是貝蒂,人生竟然能延伸成一條這麼長而遠的弧線,有時候帶給你強烈得驚人的既視感,好像同一齣戲重演了,真是不可思議。
我們住在百利金路上的一間大公寓裡,就在保羅教堂旁邊;我們有好幾次討論要買獨棟房屋,但住在這裡很舒適,離女兒的學校又近。此外,大衛在山上還有一間他小時候住的舊房子──就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雖然是我們和他的弟弟與弟媳共同持有的,但是他們住在加拿大,每年只會回來至多一、兩個星期。
我發現在我在這第一封信裡談了好多我自己和家人的事,我本來沒有計劃要這樣,但也許這是很自然的。但如我提到的,我現在處世的方式明確多了,但我想我們得下次再聊。現在已經過了午夜,大衛和一些電影圈的人出去;如果我沒搞錯,他們在談皮蘭德婁某齣劇的大型搬演計畫──兩個女兒都睡了,而我在我們家的書房裡坐了兩個小時,一面寫信一面沉思。也喝了三杯酒,我得承認,但明天是上班日,所以現在我真的該收尾了。
請原諒我寫得如此浮誇,親愛的艾格妮絲,請切勿覺得你也必須長篇大論。只要少少幾句話,就能讓我非常開心了,我保證我下次會寫得精簡些。當然,我想了解你的感受。失去了人生伴侶,你只感覺到悲傷嗎?或是在失落之中隱約也感到些許自由?相信你也知道,婚姻常被比喻成牢籠,有的人想進去,有的人想出來。我希望你明白,你可以像我們過去相處時一樣,坦誠而毫無保留地面對這些疑問。
先睡了。
請保重,快快寫信給我吧!
赫妮敬上
致:赫妮‧德嘉朵
百利金路二十四號/郭特堡/十月七日寫於格謝姆
親愛的赫妮,
謝謝你的長信,相信我──我讀來覺得非常充實。不要害怕向我傾吐心聲,我們以前的對話就是這樣的──你寫了一百個字,我才回十個字。
也請不要覺得我不了解你,即便有點離題,聽你說話還是非常有趣。現在我們差不多都活完了大半生,想到這一點、還有艾瑞克的離世,就覺得這是個思考人生的好時機。
至於我的狀況,不像你有那麼多值得交代,因為我孤家寡人。艾瑞克在我們認識的時候就已經有成年的子女,我們也早早就決定不要再把更多孩子帶到這個疑慮重重的世界上。過去這八年來──也就是我完成畢業論文之後──,我在H大學任教,離我們這裡只有七、八公里的路程,我從一開始就對學術生涯甚感喜愛。最近幾個學期,我真正掌握到了最深得我心的課程主題──浪漫時期和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就像你一樣,親愛的赫妮,我覺得自己找到了值得奉獻一生的任務,創造繼起之生命,儘管我不會有自己的孩子。
艾瑞克和前妻離婚的時候,保留了他在莫納的豪華房子,我們婚後就一直住在這裡。這是一間混用木料和石材的漂亮老屋,庭園生機盎然,還有面河的景觀。如果我對未來有什麼憂慮可言,那就是我該如何保住這間房子。艾瑞克的孩子,克拉拉和亨利,自然繼承了房子一半的產權,天曉得我要怎樣把他們的那一份買回來。我不知道你在葬禮上有沒有看到他們。亨利很高,膚色深,一副自大的樣子,克拉拉有點駝背,頭髮是鼠灰色,至少超重了十公斤。兩個人在教堂裡都坐第一排,雖然是跟我隔著走道的另一側。坦白說,我討厭他們的程度就像他們討厭我一樣,但我相信這個問題還是有可能解套的。我有點意外,遺產清點完已經兩週了,他們現在竟還沒有為了遺產的事跟我聯絡,但我相信不久後我就會接到某間知名法律事務所的電話。
除此之外,你說的完全沒錯,艾瑞克死後,我的感覺中有一種平靜和輕鬆的成分。嫁給一個年紀大你一截的人,你難免會擔心自己最後孤獨終老(從事醫療業當然不是長壽的保證,我想反而還是減壽呢),也許稍稍值得慶幸的是,生離死別發生在你四十歲的時候,而不是五、六十歲。當然,你說我們已經步入中年,這也沒錯,赫妮,但我相信我們都還能夠發揮長才,生活也有意義。你說是吧?
你寫到你是因為一個確切的原因──一個明確的意念──而開始通信,而這個原因和你的伴侶有某種關聯。我得承認,這讓我好奇了起來,所以我得請你別再「像個女人家似的兜圈子」──下一封信就直說重短點吧,希望很快就會收到你的信。
我就以這個請求為這封信畫下句點了,帶狗狗出去傍晚散步的時間到了;你知道的,我們家有兩條狗,都是結實又活潑的獵獅犬,我還沒決定要不要繼續養──我們已經養了五年,我也很喜歡他們,但不可否認,照料他們需要時間也需要精神。就像現在。
但是,如前所述,赫妮,請快快來信。我滿心期待著你的回音!
致上溫馨祝福。
艾格妮絲敬上
※
那所學校叫做瓦曼小學,得名於一個叫J.S.瓦曼的人,在一百五十年前死於戰爭。我們這班有二十五個學生;我跟一個叫卓格曼的是這個秋季學期的新生,原來有兩個學生轉走了,所以齊默曼老師說我們來補上他們的空位真是太好了。
赫妮和我是班上最出色的學生,還有一個叫亞當的,戴著厚如瓶底的眼鏡。他在搖籃裡就開始看書,把眼睛都看壞了。他的親戚馬維也在班上,我和赫妮跟他們有些往來。馬維是成績最差的那群學生之一,數學和拼字尤其慘不忍睹,但他個子大、身體壯,打架時有他在挺不錯的。
我在學校表現得很好,去年聖誕節我演了《陌路世人》的主角,齊默曼老師說我很有戲劇天份,而我努力不要太常想到薩爾布呂肯的爸爸和哥哥。整個秋天和冬天,我只去拜訪了不到兩次,我哥哥有一天下午要去雷文斯堡參加童軍營的途中,來我們的公寓待了幾個小時。我們的聯繫這麼少,感覺很奇怪,但也許更奇怪的是我其實不太在乎。
我媽工作時間很長。馬汀斯在葛克商場開了牙醫診所,我也去過,補了兩顆蛀牙。我不喜歡他;他講話尖酸刻薄,而且全身都是毛,眉毛又黑又濃,你坐在診療椅上的時候,還可以看到他的鼻孔裡也長了滿滿的毛,他還能夠呼吸,真是太驚人了。
前幾個月,赫妮的媽媽生病了,我們下午有時候要幫忙照顧她的弟弟班傑明。他是個滿臉鼻涕的六歲小孩,抱怨個不停,整天都在鬧不高興。有一次我們在敏德公園把他搞丟了。那天很冷,又下著雨,我們找他找了好幾個小時。天暗了,我們還是沒有找到他,赫妮哭了起來,說班傑明如果死了,她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她繼續胡說了一堆,說她要去撞火車,或是跳進納卡河,一了百了。但是當她在我們最後一次看到班傑明的遊樂場沙坑裡跪下來──對著上帝祈禱──,他突然就出現了。我是說,班傑明出現了,不是上帝。他比平常流了更多鼻涕、更愛抱怨,還把原本乾乾淨淨的衣服扯破了。
只要你盡力而為,把命運交到上帝手中,一切最後都會順利的,赫妮說著,擁抱了她全身髒兮兮、濕答答的弟弟。
我什麼也沒說;他出現了,我想這算是件好事,不然我們麻煩就大了,但是老實說,如果他真的失蹤了、不知怎麼地死了,我可不敢說我會想念他。
※
到了五月中旬──我的十二歲生日後兩個星期,我初經來潮之後兩天──,我發現了一件恐怖的事。
我媽和她的老闆,牙醫師馬汀斯,在談戀愛。完全是出於巧合,我撞見他們手牽著手從葛拉克路上的波馬多餐廳走出來。我跟他們撞個正著,他們看起來尷尬得嚇壞了,兩個人都是。我們只說了「哈囉」和「再見」,我就繼續往原本要去的伍瑪廣場圖書館走──但兩個小時後我回到家,我媽就告訴了我這是怎麼一回事。她說他們開始交往看看;她只用了這個說法,「交往」,我覺得這聽起來既老氣又愚蠢。她又還沒那麼老。
我告訴我媽,我覺得馬汀斯這個人很噁心,而且她應該比他小了至少三十歲吧。我媽生氣了,說馬汀斯是個有同情心又有教養的人,而且他還沒五十歲呢。
而且,她都已經把人生浪費在我爸那種浪子身上了,現在當然需要一點安全感。
我再說一次,我覺得馬汀斯令人作嘔,然後就把自己鎖在房裡。我媽半個小時候來敲門,我把燈關掉,假裝睡著了。
大人決定讓我跟赫妮一起度過暑假的大半時光。赫妮的叔叔和嬸嬸在拉戈瑪湖(Lake Lagomar)畔有一間大房子,我們會有各自的房間可住。除了叔叔嬸嬸之外,她還有三個堂弟妹住在那裡,一對跟我們同齡的雙胞胎男生,和一個五、六歲的女孩。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真的很想去拉戈瑪湖,但我曉得我別無選擇。我沒有抗議,而赫妮似乎對這個安排很期待。學期最後一天,我們互相比較成績的時候,發現我們的總平均分數完全一模一樣。亞當比我們高了零點幾分,但我們都覺得那是因為他是男生,而且戴眼鏡。
搭巴士出發去拉戈瑪湖的前一天晚上,我跟赫妮、亞當和馬維一起抽了生平第一根菸。我們躺在敏德公園的某片樹叢裡,赫妮反胃得吐在馬維的西裝褲上。馬維則是抽了兩根,說菸草讓他感覺很舒服,就算每個人都在他褲子上吐,他也不介意。他的成績是全班最差的,得去上暑期課程以免留級。亞當回家以後,馬維問我跟赫妮想不想看他的小弟弟。赫妮說她看不看都沒差,我說那就好吧。他解開褲襠,把它掏出來,解釋說它是因為割過包皮看起來才是這樣。赫妮跟我謝謝他讓我們看。
※
致:艾格妮絲‧R
賈爾達別莊/格謝姆/十月十二日寫於郭特堡
親愛的艾格妮絲,
感謝你的來信,我讀得很有興致。很高興聽到你對工作如此滿意,以及你平靜地接受了丈夫的去世。當然,我知道你一向冷靜,不會被捲入情緒的風暴中,看起來你又拾回了這項優點。我無法百分之百肯定地判斷我自己這些年來改變了多少,但有時候我覺得,內心深處的我仍然跟十二、十五或十八歲時是一樣的。如果假以時日我們打算再次見面,你一定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出我的想法是對是錯。同樣地,我也會有機會發現你內心的那個小女孩,對吧,艾格妮絲?
但我暫且不想要和你面對面,親愛的朋友,要解釋這一點,我必須觸及我當初與你開始通信的原因──這個原因到現在也有很大部分仍然成立。你敦促我不要避談這個原因,趕快切入重點,所以我現在就鼓起勇氣直說了。我希望你不會不開心,但我終究得冒著這個險,不得不然。
如我先前說過的,這和大衛有關。你知道我們結婚至今已經將近十八年了。演完《李爾王》之後才幾個星期,他就向我求婚,我們在六月訂婚,同年十一月就結婚了,是的,你不會不曉得這一段。大衛和我,我們度過了美好的歲月,如今回想,我知道那段時光的確幸福......至少起初的十年是如此。我知道──你不需要否認,親愛的艾格妮絲──你有時候覺得我這個人天真單純得無可救藥;我還記得我們的許多次對話,和許多次的意見相左,你並不像我一樣相信上帝的守護和人生的光明面,相信我們能做的唯有盡力而為,不管結果如何都只能接受。
相信我們必須對人性的良善抱有信心。大衛和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也針對這些事討論了很多,當我們發誓永遠忠於彼此,那些話並不只是空洞的誓言和虛有其表的儀式。我們是認真的;我們決定和彼此、和我們未來的孩子共同生活一輩子;愛不能有條件,不能禁不起世事或時間的考驗。就是這麼簡單,但也就是這麼困難。
但現在事情發生了。透過一些我不想在此時此地細數的機緣,我得知大衛在和別的女人約會。我不知道對方是誰,也不在乎。但大衛背叛了我、我們的孩子和我們愛的誓約,我不想默默接受。我不知道這段所謂的婚外情進行了多久,但我是六個月前發現的,也許發生的時間已經有兩倍長。很自然地,大衛隱瞞著這件事,我也有樣學樣:我沒有表現出我知道他在我背後亂搞,連一個字或一個表情都沒有透露。我不想透過跟他攤牌或是曉以大義──演出被抓包的丈夫和受騙受傷的妻子之間那套老掉牙又可悲的戲碼──來解決這個問題。過去幾個月來,我思考過各種可能和不可能的解法──以我自己和女兒的最佳利益為念──親愛的艾格妮絲,我毫不懷疑。大衛必須死。
如果你現在正一面喘氣、一面脈搏加速地重讀前幾句話,我非常能夠理解。也許你會把這封信推開,眼神空洞地凝視著前方。搖著頭、按摩太陽穴,就像你認真思考事情以前會做的那樣。
但那樣無濟於事。這些字句已經寫下,我的決心無可動搖。我丈夫必須死。他不配活在世上,不管如何,艾格妮絲,請不要與我爭論這一點。
至於接下來,你可能會──顯然會──提出許多於理有據的意見。但我要說的是,我想要你幫忙。
不,請別把信推開,好心的艾格妮絲!至少看在我的份上,把整封信讀完吧。不論你的反應如何,我會確保大衛在不久後的未來就會送命。不管是用什麼方法。大概一年前,我讀了一本犯罪小說,我忘記作者的名字了,但我想那是個美國人──書裡描寫兩個在火車上相遇的陌生人,他們在對話中發現兩人都可以透過一位近親的死亡牟取極大的利益。也就是說,有兩位潛在的受害者,他們身邊各有一位。但他們不能就這麼把礙事的親人除掉,因為他們立刻就會背上嫌疑。可是接下來他們想出了一個點子,他們可以互換謀殺對象。他們把這叫作交換謀殺。A負責謀殺B的妻子,B會殺掉A的有錢親戚。
你懂我的意思嗎,艾格妮絲?我開始思考大衛的背叛、把這件事跟交換謀殺的點子連起來時,我突然就想到了你。的確,我無法提供你相應的幫助(我是這樣想的),但重點是,下手謀殺大衛的必須是個完全不在我社交圈裡的人,而我自己要待在別的地方,製造滴水不漏的不在場證明。整個計畫就是這樣。而且,我保證會付給你一筆豐厚的酬勞。你上一封信裡提到,你擔心你要怎樣才有辦法繼續住在艾瑞克的房子裡──相信我,艾格妮絲,十萬元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如果你需要的數目更大,我們也可以討論。
我發現我又開始囉嗦了;你現在肯定已經了解我向你請求的是什麼。目前我還沒有想到做法等等──我們再過一會兒才要過那座橋,我喜歡這樣講──但我現在忍著肚子裡些微的翻攪,靜候你的回覆,你一定懂的。我認真地請求你,花個兩天的時間考慮我的提議──若是如我全心希望的,你給了我初步肯定的答案,那也不代表你之後不能改變主意。當然不。此時此刻,我唯一的請求,就是希望你願意跟我討論這件事。就像人家說的,用開放的態度討論假設的問題。
那麼,親愛的艾格妮絲,請好好想一想,再告訴我答案。不論你的反應如何,我仍然是、也一直會是你忠心的朋友。
赫妮敬上
※
致:赫妮‧德嘉朵
百利金路二十四號/郭特堡/十月十九日寫於格謝姆
親愛的赫妮,
你的上一封信,我已經讀了十次,還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的要求真是無比卑劣可惡,令我無言以對。我認真地說,我懷疑你的精神狀況是否正常,我已經想了一整晚該如何回覆──卻想不出任何適當的方案。
有鑑於此,我要改而請你寫一封信作為澄清,看是要放棄你的要求,或是解釋清楚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以及為什麼你竟然會認為我有可能參與你這個荒謬至極的計畫。
艾格妮絲敬上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詭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5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詭計
只能誕生在冷冽凜風中的顫慄故事
北歐犯罪小說家哈康‧納塞,獻給讀者的惡魔短篇集
★如履薄冰、峰迴路轉!收錄五則精采短篇〈湯姆〉〈瑞恩〉〈親愛的艾格妮絲〉〈撒馬利亞之花〉〈本案所有資訊〉
★《罪行》費迪南.馮.席拉赫般震撼+《人骨拼圖》傑佛瑞•迪佛式大逆轉!
★三篇已改編成電影,瑞典版《千禧年三部曲》導演精采翻拍!
★英國《衛報》:哈康.納塞身居最優秀的北歐犯罪小說作家之列!
冬陽(推理評論者)
臥斧(作家)
路那(推理評論者)
──刺激推薦!
【故事簡介】
湯姆死了,瑞恩死了,薇拉死了,無名女孩死了,還有一人的丈夫將會死去。
五件案子,四件不尋常,一件平凡得刺骨──以上句子,藏有謊言。
瑞典最佳犯罪小說獎、玻璃鑰匙獎、赫爾辛基文學獎
三冠王瑞典犯罪小說家使出渾身解數的驚嘆短篇集!
〈湯姆〉
茱蒂絲半夜接到電話,來電者自稱湯姆,輕喚她:「母親。」她嚇得匆匆掛掉。日日過去,以為沒事的深夜,電話再度響起,對方在話筒另一端對湯姆的事如數家珍,連禁忌的「那件事」都牢記在心,茱蒂絲滿心恐懼,因為湯姆失蹤數年,可能已死……對方是誰?目的是什麼?為何知道湯姆的祕密?
〈瑞恩〉
譯者大衛的編輯收到國際級作家瑞恩的信件及手稿。瑞恩在信中強調「本書絕不能以我的母語發表,須採最高層級保密。」並在數日後自殺身亡。大衛接下這起不尋常的案子,心中藏有別的盤算,他失蹤的妻子曾在出版社安排的工作地點出沒。他一面工作一面委託偵探尋找妻子時,竟發現瑞恩遺稿裡的死亡訊息……
〈親愛的艾格妮絲〉
艾格妮絲在丈夫葬禮與兒時玩伴赫妮恢復聯繫,展開信件交流。艾格妮絲談到自己保不住房子,正在解決財務問題。赫妮筆鋒一轉談起家中醜事又欲言又止,艾格妮絲催促對方寫出真意,卻收到「請妳替我殺掉丈夫!」的回信。赫妮保證如果幫忙,將替她解決債務,為了生活,艾格妮絲不安地和對方籌備起殺人計畫……
〈撒馬利亞之花〉
亨利回到兒時故鄉,因為老友打電話給他,希望他幫忙編撰一本犯罪小說。見面當日早晨,亨利收到一封信,上頭寫「回來的時候聯絡我」寄件者是薇拉.卡爾──三十年來眾所皆知的失蹤者!薇拉是與亨利同校的校花,她在畢業舞會的夜晚連同騎的淑女車一同失蹤……已經過三十年的今日,薇拉還活著?為什麼沒和大家聯絡?又為什麼聯絡了亨利?
〈本案所有資訊〉
S是個普通的年輕男人,成功應徵教師,前往一所美麗的學校,那兒有令他驕傲的學生,上學期結束前,班上女孩不幸身亡。S手足無措,更令他不安的是,學校所有人都開始討論:期末要結束了,他們該如何打這個已經死去女孩的期末成績呢?尤其,她有一份作業還沒交……
犯罪小說中,殺人就和真相大白一樣常見。
然而,驟現的惡意、墮落的人性、作者的詭計藏在何方?
各位讀者,面對書中五則短篇,睜大眼看清楚了……
【書評推薦】
★獲《時代雜誌》、《星期日郵報》、《Stylist時尚雜誌》、《星期日泰晤士報》、《婦女與家庭月刊》、《地下鐵報》等國際級書評媒體讚譽!
節奏恰到好處、令人意猶未盡的作品!
──路那(臺灣推理評論者)
作者以冷靜的口吻描述暗潮洶湧的日常,角色的隱瞞不僅是出自類型書寫的布局,更映射出你我在現實中理所當然的決定,當自己沉浸在宛如親臨的不安猶疑時,翻轉性的結局將轟然朝你撞來……具有深刻探索感的黑色懸疑短篇集,衝擊力道十足。
──冬陽(臺灣推理評論者)
這本書是獻給尤.奈斯柏粉絲的,無比緊張刺激的閱讀體驗。
──英國《Stylist時尚雜誌》
作者簡介:
哈康.納塞Håkan Nesser
1950年出生,瑞典犯罪小說家,三度榮獲瑞典最佳犯罪小說獎(Best Swedish Crime Novel Award)、瑞典犯罪小說獎「玻璃鑰匙獎」(Glass Key Award)、赫爾辛基文學獎(Palle Rosenkrantz Prize)等文學獎項,他在瑞典最蔚為人知的犯罪小說系列是「Van Veeteren series」,數次在瑞典被翻拍成影集;《詭計》中的三部作品亦曾被改編成電影。
http://www.nesser.se/en/biography
章節試閱
〈親愛的艾格妮絲〉
整體來說,這是一場成功的葬禮。
那天早晨原本灰暗無風,但當我們去到戶外的墓地,太陽就撥開了雲朵露臉,透過榆樹的黃葉投下不規則形狀的光點。
艾瑞克一定也會喜歡。秋天。天色豁然開朗,在空氣中留下爽利的氣息。清新而不冰冷。往莫納方向的田野已經收割了,但還沒有犁過。遠方的一個農夫正在焚燒雜草。
主持葬禮的牧師名叫席德馬克,是個高瘦蒼白的男人;當然,我們前一週就碰面過,議定儀式的流程。他剛來到這個教區,脊椎似乎因為某種傷病而變形,使得他行動笨拙,幾乎是瘸了腿,也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老...
整體來說,這是一場成功的葬禮。
那天早晨原本灰暗無風,但當我們去到戶外的墓地,太陽就撥開了雲朵露臉,透過榆樹的黃葉投下不規則形狀的光點。
艾瑞克一定也會喜歡。秋天。天色豁然開朗,在空氣中留下爽利的氣息。清新而不冰冷。往莫納方向的田野已經收割了,但還沒有犁過。遠方的一個農夫正在焚燒雜草。
主持葬禮的牧師名叫席德馬克,是個高瘦蒼白的男人;當然,我們前一週就碰面過,議定儀式的流程。他剛來到這個教區,脊椎似乎因為某種傷病而變形,使得他行動笨拙,幾乎是瘸了腿,也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老...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2021/07/07
2021/07/07 2021/06/16
2021/06/16 2021/05/29
2021/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