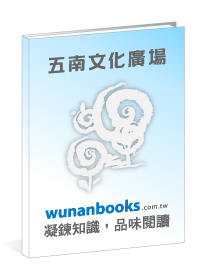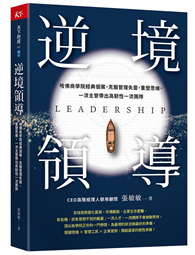傳統之「上嫁」邏輯或是經濟理性考量常常是一般理解臺灣與東南亞籍配偶之間所產生跨國通婚的框架,本書的印尼婚姻移民即是在如此的視角下遭受臺灣社會的「觀看」。 然而,事實上通婚不只對於結婚雙方來說是一個個人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再加上需與另一半攜手踏上未知的將來,在走上婚姻之路時,夾雜許多個人的想像或是意圖。與此同時,由國際政經秩序、移出者分別在原生國家與接收社會內部政治、社會與歷史下所處的脈絡所構成的外在的結構要素,亦影響跨國通婚的決定與選擇。為了勾勒出跨國通婚中的複雜樣貌,本書以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主體,透過她們述說自己的經驗,打破她們常被呈現或是被「想像」的單一面貌,而還原鑲嵌在其移動人生中業已存在的複雜性。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身為Amoy:在臺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之生命敘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教育學習 |
$ 342 |
客家文化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42 |
台灣研究 |
$ 34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身為Amoy:在臺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之生命敘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芬芳
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族群研究為主要學術關懷,研究專長為族群關係、客家研究以及性別、族群與宗教之交織,研究範圍包括臺灣、印尼與德國。相關著作發表在《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客家研究》、《思與言》等期刊,曾出版專書《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2016)。
蔡芬芳
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族群研究為主要學術關懷,研究專長為族群關係、客家研究以及性別、族群與宗教之交織,研究範圍包括臺灣、印尼與德國。相關著作發表在《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客家研究》、《思與言》等期刊,曾出版專書《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2016)。
目錄
自 序
第一章 臺灣客家跨國通婚與婚姻移民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二、研究對象
三、研究觀點
四、研究資料來源
五、分析架構與各章概述
第二章 跨國通婚與多重交織下的生命經驗
一、跨國通婚理論與研究
二、性別、族群與宗教
第三章 通婚中的女性圖像──「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
一、童年生活─小康家庭與族群互動
二、離開家鄉
三、踏上婚姻之路
四、初入婚姻生活
五、在臺生活
第四章 「文化親近性」與宗教?
一、「文化親近性」⁉
二、移民與宗教
第五章 Amoy,還有別的故事嗎?
參考文獻
第一章 臺灣客家跨國通婚與婚姻移民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二、研究對象
三、研究觀點
四、研究資料來源
五、分析架構與各章概述
第二章 跨國通婚與多重交織下的生命經驗
一、跨國通婚理論與研究
二、性別、族群與宗教
第三章 通婚中的女性圖像──「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
一、童年生活─小康家庭與族群互動
二、離開家鄉
三、踏上婚姻之路
四、初入婚姻生活
五、在臺生活
第四章 「文化親近性」與宗教?
一、「文化親近性」⁉
二、移民與宗教
第五章 Amoy,還有別的故事嗎?
參考文獻
序
序
如果可能,我今天也是印尼客家人……
隨著年紀漸長,逐漸想要回溯自己生命歷程。由於個人的存在無法脫離與父母或其他家人的關係,認識家人也有助於認識自己,再加上有感先父年歲已大,因此在先父(1934-2021)年屆八旬之際,我開始思考,「父親」這個標籤是否限縮了我對他的認識,而應該將父親當成是一個「個人」來了解他。父親出生於廣東梅縣,家中非常貧窮,祖父及家族親戚為了討生活也曾到過印尼,只是當時父親年幼,無法確切得知祖父究竟到達印尼何處。父親只記得,祖父從印尼回家之後,因吸鴉片之故,臥床咳嗽,當時還是個孩子的父親必須幫祖父倒掉痰盂中的痰,父親常覺得這就是他自己肺部病變的根源。因為當時家鄉窮困,祖父在外,需照顧婆婆以及獨立扶養一對兒女的祖母,僅能靠兜售煤炭球維生。即便後來祖父回鄉,因病無法養家並早逝,祖母只好讓年僅十三歲(1947)的父親跟隨國民黨軍隊(操廣東話的部隊),因為至少在軍隊中可以粗飽。1950年從海南島抵達高雄,之後隨著軍隊腳步住遍臺灣各地,最後在臺北落腳生根,直到2021年離世。
除了祖父在20世紀上半葉曾到印尼之外,家族與印尼的情緣則是隨著遠房親戚與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結婚延續。當時因為筆者還是高中生的年紀,對於跨國通婚並未具有任何的敏感度,而之後親戚過世,再也無任何訊息,但當自己要開始進行相關研究時,才發覺原來家族中也曾經因為親戚結婚而與印尼客家女性有著那麼一絲絲的關聯。
或許是因為生命的偶然性,在書寫之際,突然出現了個念頭,「如果可能,我說不定就是印尼客家人呢!」也正因如此,在聽錄音檔與閱讀訪談逐字稿時,不只用感官「聽」與「看」,更透過婚姻移民在述說自身經驗時的聲音感受生命的力道,本書因此得以完成。在此須向所有的研究參與者致上最誠摯的謝意,讓我有幸進入你們的人生經歷!
蔡芬芳
2023年夏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如果可能,我今天也是印尼客家人……
隨著年紀漸長,逐漸想要回溯自己生命歷程。由於個人的存在無法脫離與父母或其他家人的關係,認識家人也有助於認識自己,再加上有感先父年歲已大,因此在先父(1934-2021)年屆八旬之際,我開始思考,「父親」這個標籤是否限縮了我對他的認識,而應該將父親當成是一個「個人」來了解他。父親出生於廣東梅縣,家中非常貧窮,祖父及家族親戚為了討生活也曾到過印尼,只是當時父親年幼,無法確切得知祖父究竟到達印尼何處。父親只記得,祖父從印尼回家之後,因吸鴉片之故,臥床咳嗽,當時還是個孩子的父親必須幫祖父倒掉痰盂中的痰,父親常覺得這就是他自己肺部病變的根源。因為當時家鄉窮困,祖父在外,需照顧婆婆以及獨立扶養一對兒女的祖母,僅能靠兜售煤炭球維生。即便後來祖父回鄉,因病無法養家並早逝,祖母只好讓年僅十三歲(1947)的父親跟隨國民黨軍隊(操廣東話的部隊),因為至少在軍隊中可以粗飽。1950年從海南島抵達高雄,之後隨著軍隊腳步住遍臺灣各地,最後在臺北落腳生根,直到2021年離世。
除了祖父在20世紀上半葉曾到印尼之外,家族與印尼的情緣則是隨著遠房親戚與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結婚延續。當時因為筆者還是高中生的年紀,對於跨國通婚並未具有任何的敏感度,而之後親戚過世,再也無任何訊息,但當自己要開始進行相關研究時,才發覺原來家族中也曾經因為親戚結婚而與印尼客家女性有著那麼一絲絲的關聯。
或許是因為生命的偶然性,在書寫之際,突然出現了個念頭,「如果可能,我說不定就是印尼客家人呢!」也正因如此,在聽錄音檔與閱讀訪談逐字稿時,不只用感官「聽」與「看」,更透過婚姻移民在述說自身經驗時的聲音感受生命的力道,本書因此得以完成。在此須向所有的研究參與者致上最誠摯的謝意,讓我有幸進入你們的人生經歷!
蔡芬芳
2023年夏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