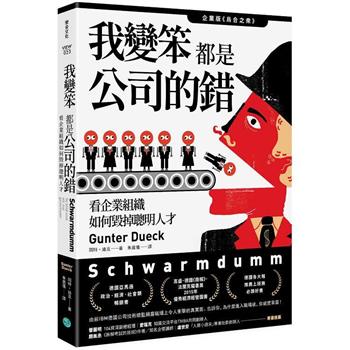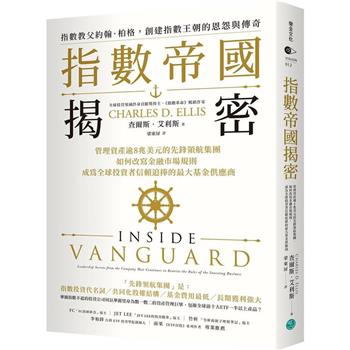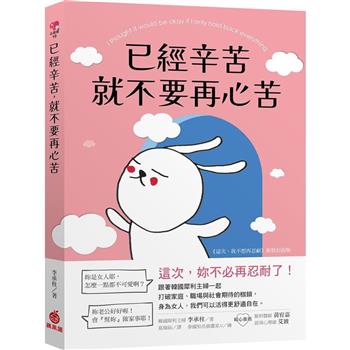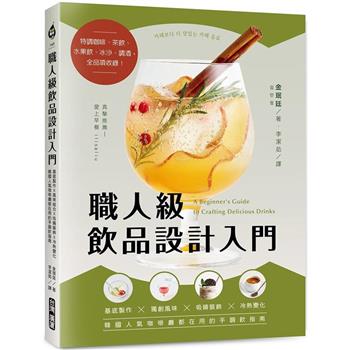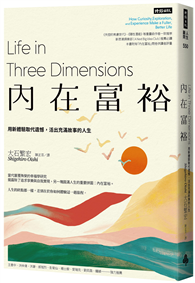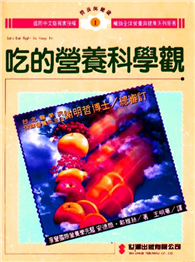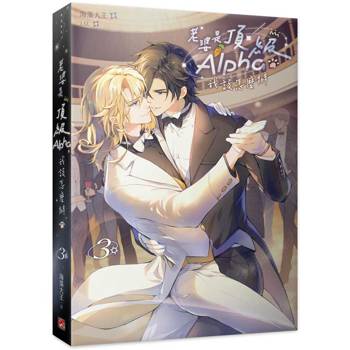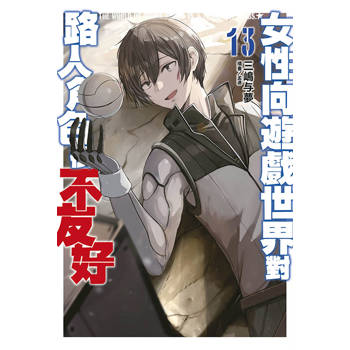色彩中的美
不同的色彩可以帶有不同的象徵意涵,例如「紅」可以是熱情,但也可以血腥,抑或是多刺的玫瑰,端看人們對不同類的紅,以什麼樣的方式形成了具有共同含義的認知概念。朱光潛(1984:149)便提到了不同類型的紅,如「花紅、胭脂紅、人面紅、血紅、火紅、衣服紅、珊瑚紅等等,紅是這些東西所公有的性質。」
人們對於顏色所表示的象徵性會隨著認知上的不同而改變著,而且可以形成一種共同象徵性的能力,從顏色的本質來看,有暖色系與冷色系之分,因而不同的色彩帶給人們的觀感就會有所不同;但有時因社會文化背景因素,也會影響顏色語詞象徵意涵的變化,故同一顏色或有兩極化的觀感,例如「紅」的喜氣與血腥,前者極具暖色的吉祥性,後者則與不吉祥的血光有關;「黃」的九五之尊與色情,前者因中國皇帝龍袍為黃色,代表帝王之尊,後者因西方電話簿中黃色頁面的色情代表而形成的象徵;「藍」的蔚藍與憂鬱,前者給人天空或大海蔚藍般的心情舒暢、開闊的感覺,後者則給人心情鬱悶的感覺,完全的兩極化。「藍」雖為冷色系,但因著大海藍天與蔚藍天空的開闊,可以是正向情緒顏色的代表,相反的,據說西方民謠當中有個「藍魔鬼」(bule devil),他是極度憂鬱的代表,推廣開來,藍色便成了「憂鬱」的象徵。當然,顏色與顏色之間可依照不同的比例而調配出不同的色彩,這與調配者的功力有關,往往一種想望美好顏色的調配,若一次就成功,後來再重新調配時,則不見得可以調得出先前中意的色彩。
南齊謝赫提出繪畫理論的「六法」概念,用以作為衡量繪畫作品高下的標準,其中第四法為「隨類賦彩」,說的是畫作所賦予的色彩變化可以決定一件作品的優劣成敗。一座美麗世界的形成常是由色彩、空間、線條組合而成,而「色彩」的產生則是源自於光源,因著光源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色彩變幻。在西方繪畫體系之下,傳統繪畫著重在室內對象物體的明暗關係,但在十九世紀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其作品則結合自然界的光影而創造了豐富性的色彩效果,這種畫風在當時是大膽而前衛的。印象派的命名起自於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於1874 年展出《印象.日出》作品,此作品尤著重於光影的改變,其色彩則具有自然環境色的柔和之美,具現代繪畫色彩造型上的變革。在荷蘭後印象派畫家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的作品當中,其色彩的運用則更大膽,甚至造成視覺上的衝突,甚而給人一種壓迫感,抑或喚起對於生命的熱情,例如豔黃的《向日葵》、豔黃加暗藍的《星夜》、豔黃加詭異黑藍的《有烏鴉的麥田》。米羅(Joan Miró, 1893-1983)為二十世紀的超現實主義畫家,作品特色在於其畫面常是由不同運動型線條形成了大大小小區塊的形象,其形象在抽象之中又帶有現實感,甚至是現實之外的一種異想世界,例如《哈里昆的狂歡》一畫,在區塊當中由精雅色彩來布局,包含區塊的藍、區塊的黑、區塊的紅,點點式的黃、紅及其他顏色,背景大片沉穩的色彩,加上黑、白弧線式色彩的營造飄揚於畫面之中,極富於夢幻性,形成了一座具有超脫現實的空想與幽默的世界;室內為熱鬧的狂歡,但卻是由一些生活周遭的玩意兒所主導,玩意兒則是由不同線條所構成的不同形狀,加之色塊、線條色彩的經營,更顯得人類在畫作上的角色反而是莫可奈何的獨自悲哀著。
相對於西方繪畫重於色彩的變化,中國傳統山水國畫則以墨色為主,但墨色濃淡的運用卻也顯現出色彩的層次感,尤其在元朝畫作之中以墨色呈現出畫與人對話之間的有我之境,著重於精神層面的捕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曾論及山水畫的特質:「草木敷榮,不待丹綠之采。雲雪飄颺,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此便說明自然色彩甚於人工著色的重要性,而運用墨色的濃、淡、乾、焦、濕等等即可呈現出自然的色彩。
從文學看見美麗的色彩
文學作品當中本就帶有「美」的因子。語言當中的顏色本為形容詞性的,但形容詞與動詞之間常可轉換使用,運用在文學作品中或可收驚人的動態美學效果,例如,宋朝文學家、政治家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一詩中之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據說「綠」字前後改了好幾次才滿意定案,「綠」不僅以動態方式傳達出景色的綠意盎然,更隱含著原本離鄉的思鄉之情因著「皇帝」(春風)的恩賜而使得王安石得以欣喜的回京,此便是「綠」動詞又兼帶形容詞性的文學與美學方面的動態性效果。宋徽宗趙佶善於繪花鳥,他曾出過一考題來考畫家:「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結果許多人畫出了在一片綠意中帶出紅花之點,但最終得到第一名的則畫出在綠樹成蔭的閣亭中,一仕女倚欄而望,只櫻桃小口的一點紅與嫩綠枝頭相互映襯,點出「紅一點」的主題。一首詩中有畫面,有簡單而動人的色彩交織成一幅美麗而感人的景色,殊不知更有賞詩之人有能力加以活化詩的意境,這便是畫家在創作時,面對相同的物件,因體認不同而有不同的畫面呈現,這也包括每個人在「美」方面有不同的想像力、敏銳性與鑑賞力。
張愛玲小說當中對人物五官及其衣著妝扮、家居陳設、景物等等,也都具有豐富色彩美學的體現,色彩的描寫彷彿道出人物角色的特色、處境或想望,似乎也道出一幕幕「悲涼」故事性的畫面。例如「紅」與「白」不過是極為簡單而中立的單音節基本顏色詞,在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透過玫瑰的嬌美與多刺、紅白之間的對比,以及紅給人熱情、白給人聖潔的感覺,以形容男主角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似乎也註定了這兩個女人悲涼的命運。巧妙的是當紅玫瑰以嬌豔的姿態登場時,作者以一系列的綠來形容女子以襯托紅玫瑰盛開的感覺:「她穿著⋯⋯,是最鮮辣的潮濕的綠色,沾著什麼就染綠了。⋯⋯,彷彿她剛才所佔有的空氣便留著個綠迹子。⋯⋯,用綠緞帶十字交叉一路絡了起來,⋯⋯」接著以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手法來突顯女子的嬌豔、刺眼與挑逗,及其帶給男主角心理情慾層面上的不安:「露出裏面深粉紅的襯裙。那過分刺眼的色調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當後文描述了紅玫瑰凋謝、顏色褪去之時,作者仍以豔麗的顏色來形容該女子,但顏色少了許多的生動感:「塗著脂粉,耳上戴著金色的緬甸佛頂珠環,⋯⋯。」但因為該女子已是中年的女人,胖到癡肥的程度,這些豔麗的色彩在作者筆下也就變得俗豔了,前後兩極化的對比,也構成了紅玫瑰最後晚景淒涼的命運。
再如張愛玲短篇小說〈傾城之戀〉中,有一段描寫一個配角印度女人西式時髦的穿著打扮,和色彩有關的部分:「漆黑的長髮,⋯⋯。玄色輕紗氅底下,她穿著金魚黃緊身長衣,⋯⋯,只露出晶亮的指甲。⋯⋯。她的臉色黃而油潤,像飛了金的菩薩,⋯⋯。粉紅厚重的小嘴唇,⋯⋯。」文末這位印度女人再度出場時,張愛玲對同一人物的敘述則明顯少了色彩,剩下的只是暗然顏色的鋪陳:「黃著臉,⋯⋯,身上不知從哪裏借來一件青布棉袍穿,⋯⋯。」形成了前後風光與不風光之間的對比。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以「長長的兩片紅胭脂」來指稱「光豔」伶人的雙唇,與之前印度女人相較,都是形容嘴唇,但韻味感覺卻有所不同,前者帶有一種貴重的亮麗,後者則帶有一種光豔的亮麗,當然這和角色的設定有關。另有一小段約422 字,一段落便出現了15 種和顏色有關的語詞,分別描述了空間中光的感覺,如「堂屋裏暗著」、「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朦朧中可以看見⋯⋯」、「在微光裏」;家居陳設,如「青磚地上」、「紫檀匣子」、「琺藍自鳴鐘」、「綠泥款識」、「硃紅對聯」、「金色壽字團花」、「墨汁淋漓的大字」;人物五官的描寫,如「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甚而時空背景下的色彩,如「硃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這一段乍然像是編織成一幅色彩繽紛的世界,但實際上卻營造出單調與無聊、青春流逝的女人的人生。張愛玲描寫人物的形象可說是一絕,空間感的陳述也是一絕,尤以空間感透露著時間的流逝與人物的悲涼,好比「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陽臺上」來形容人物或場景的落寞;甚至還以色彩來形容聲音,如「聲音灰暗而輕飄」。
在生活周遭當中,「顏色」或「色彩」雖是一種視覺上的觀感,但在文學作品當中巧妙運用色彩學的觀點,則可以令一部文學在視覺之外的聽覺、觸覺、感覺等等,均極具有色彩美學的特質。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客家美學散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49 |
客家文化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客家文化 |
$ 316 |
社會人文 |
$ 316 |
文化評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客家美學散論
在藝術的各類範疇中,顯出客家文化的內涵,是為客家美學。包含以客家主軸談美,或非以客家主軸但將客家元素融入於其中談美。客家美學常見於客家文學、民間文學、建築、音樂、繪畫、工藝作品、美食……等等。如本書創作篇之顏色詞與文學教學、客家建築、客語繪本、繪畫與客家文化、客家文化資產等;研究篇之客語繪本教學、流行語與社會文化、客家傳統與流行音樂等。從各種不同文化與美學中認識客家,也從各種客家美學中認識客家文化。
作者簡介:
賴文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於2023年獲客家事務專業獎章三等。
專書出版計20本,分別為學術著作《臺灣客語語法導論》(2015)、《語言接觸下客語的變遷》(2020)、《臺灣客語語法結構變異新論》(2021)等7本,繪本著作《夜呱愛去哪?》(2013)、《花繪花語:靚靚个花》(2022)、《大海裡肚有麼个?》(2023)、《臺灣正有个生物?》(2025)等8本,語文教材《初級客語講義》(2021)等2本,以及譯作《世界文學客語譯選集》(2024)等3本。
章節試閱
色彩中的美
不同的色彩可以帶有不同的象徵意涵,例如「紅」可以是熱情,但也可以血腥,抑或是多刺的玫瑰,端看人們對不同類的紅,以什麼樣的方式形成了具有共同含義的認知概念。朱光潛(1984:149)便提到了不同類型的紅,如「花紅、胭脂紅、人面紅、血紅、火紅、衣服紅、珊瑚紅等等,紅是這些東西所公有的性質。」
人們對於顏色所表示的象徵性會隨著認知上的不同而改變著,而且可以形成一種共同象徵性的能力,從顏色的本質來看,有暖色系與冷色系之分,因而不同的色彩帶給人們的觀感就會有所不同;但有時因社會文化背景因素,也會影響顏...
不同的色彩可以帶有不同的象徵意涵,例如「紅」可以是熱情,但也可以血腥,抑或是多刺的玫瑰,端看人們對不同類的紅,以什麼樣的方式形成了具有共同含義的認知概念。朱光潛(1984:149)便提到了不同類型的紅,如「花紅、胭脂紅、人面紅、血紅、火紅、衣服紅、珊瑚紅等等,紅是這些東西所公有的性質。」
人們對於顏色所表示的象徵性會隨著認知上的不同而改變著,而且可以形成一種共同象徵性的能力,從顏色的本質來看,有暖色系與冷色系之分,因而不同的色彩帶給人們的觀感就會有所不同;但有時因社會文化背景因素,也會影響顏...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就這樣靜靜的做著一件事情
沒有太多的吵嚷紛擾
只有沉醉與享受
也許是和風的對話
和山的對話
和自在的對話
又也許只是和不同類型的文字在對話
以及和那個流浪在他方的你在對話
從客家角度思維美學,提升美感的層次
本書收錄了作者十八篇美學類作品,含創作類十一篇、研究類七篇。創作類七篇於《美育》刊出,兩篇刊於《客家文化季刊》、《桃園客家》,另兩篇為客語寫成之客家文化紀實,刊於電子報;研究類一篇於通識學報刊出,三篇於研討會發表,一篇於《國文天地》刊出,一篇收錄於研討會會後論文集。時間橫跨2009年∼2024年。...
沒有太多的吵嚷紛擾
只有沉醉與享受
也許是和風的對話
和山的對話
和自在的對話
又也許只是和不同類型的文字在對話
以及和那個流浪在他方的你在對話
從客家角度思維美學,提升美感的層次
本書收錄了作者十八篇美學類作品,含創作類十一篇、研究類七篇。創作類七篇於《美育》刊出,兩篇刊於《客家文化季刊》、《桃園客家》,另兩篇為客語寫成之客家文化紀實,刊於電子報;研究類一篇於通識學報刊出,三篇於研討會發表,一篇於《國文天地》刊出,一篇收錄於研討會會後論文集。時間橫跨2009年∼2024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開場白
壹、創作篇
教學也可以很彩色
從美學觀點談文學欣賞
美的對話
速寫花的婉約
中西繪畫:畫犬或畫鬼易?
我的繪本故事
打開視覺的窗:看見客家建築美學
躲在田野鄉間的山牆馬背
繽紛客家.新屋我庄
文化資產之美:海洋客家文化
文化資產之美:客庄八本簿
貳、研究篇
客語繪本的創作與應用:兼談在地繪本的開發
環扣鏈結策略與客語繪本共讀淺談
海洋生態美學融入客語繪本情境對話式教學策略研究
詞彙語法結合主題性客家文化教學策略研究:從鳥類、花卉、海洋生態繪本談起
臺灣流行語構式類推的文化效應
客家山歌中...
壹、創作篇
教學也可以很彩色
從美學觀點談文學欣賞
美的對話
速寫花的婉約
中西繪畫:畫犬或畫鬼易?
我的繪本故事
打開視覺的窗:看見客家建築美學
躲在田野鄉間的山牆馬背
繽紛客家.新屋我庄
文化資產之美:海洋客家文化
文化資產之美:客庄八本簿
貳、研究篇
客語繪本的創作與應用:兼談在地繪本的開發
環扣鏈結策略與客語繪本共讀淺談
海洋生態美學融入客語繪本情境對話式教學策略研究
詞彙語法結合主題性客家文化教學策略研究:從鳥類、花卉、海洋生態繪本談起
臺灣流行語構式類推的文化效應
客家山歌中...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