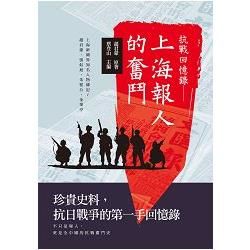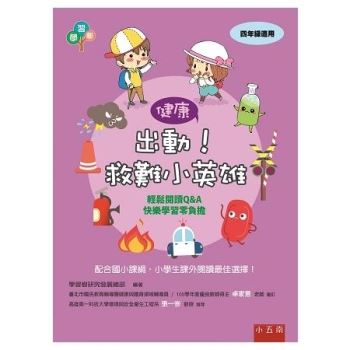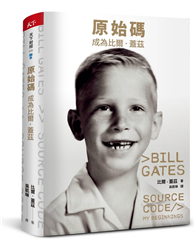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抗戰回憶錄──上海報人的奮鬥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9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社會哲思 |
$ 298 |
新聞傳播 |
$ 308 |
中國歷史 |
$ 308 |
中國歷史 |
$ 315 |
中國歷史 |
$ 315 |
社會人文 |
$ 315 |
歷史 |
電子書 |
$ 35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抗戰回憶錄──上海報人的奮鬥
對日抗戰中有各種不同的回憶錄,上海《申報》名記者趙君豪寫下當年上海報人抗戰的忠實報導,不為日軍威脅利誘,甚至犧牲生命的英勇事蹟。其中有為大眾所熟悉的如《大美晚報》的主持人張似旭被暗殺;《大美晚報》記者朱惺公公然撰文抨擊漢奸,導致頭部遭轟擊而死;《申報》記者金華亭也遭敵偽漢奸狙擊而亡。此外,《申報》被敵偽投彈四次,還有許多報館自己築成堅固的堡壘,自行雇用巡捕在門口巡邏。然而,在這樣戒備森嚴之下,報社依然揮其如椽之大筆,從事忠實客觀地報導,對敵偽作無情的打擊,在世界新聞史上,是空前的。
本書作者趙君豪為知名新聞記者,以忠實的態度以及詳實的新聞手法記述在對日戰爭中親聞的事蹟,內容易讀,歷歷如繪,生動體現動盪大時代的真相,是了解抗日戰爭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