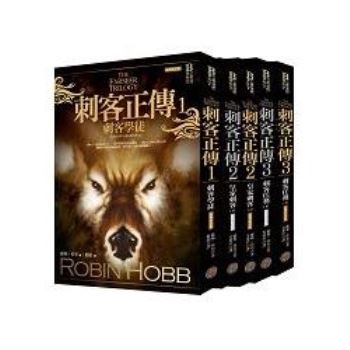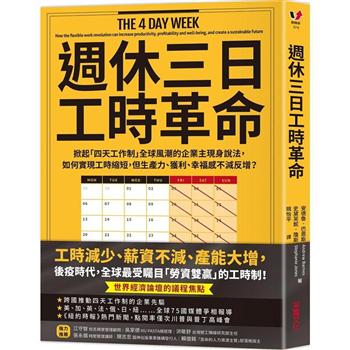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聚聚」是父母為我取的小名。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一、取名聚聚,然我兩歲半就失去親生母親
我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夏天在哈爾濱霽虹橋(南崗通往道裡的要道)旁的中東鐵路局附屬醫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松花江畔的哈爾濱,是我國東北三大名城之一(另兩個是瀋陽和大連),「哈爾濱」三字是滿族語,意思是「曬漁網的地方」。當時的人口二百五十萬。此地從前是荒涼的漁村,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和帝俄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約》,俄取得特權,在東北修築由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東清鐵路」(後改稱「中東鐵路」),哈爾濱遂成為鐵路的重要交匯點和歐亞交通中心,正式成為商埠。
哈爾濱大體上分為三大部分:道裡、道外、南崗。郊區有上號、顧鄉屯、偏臉子、馬家溝、懶漢屯等。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沙皇被推翻。大批俄國人逃亡到歐洲或我國東北,尤以哈爾濱為多,幾乎占哈爾濱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白俄」(「白俄」一詞,來源可能是:蘇共自稱「紅黨」「紅軍」,把帝俄時代的官員、地主、富商以及自由知識份子視為「白」)多屬於上流社會,文化程度高,經濟富足,生活優裕,在哈爾濱從事文化藝術傳播工作,組織音樂、文學社團,成立繪畫、戲劇機構,舉辦演奏、出版、展覽。城裡的學校、書局、畫廊、博物館、教堂、商店、餐館,從建築到室內裝潢完全歐化,尤其是道裡,街道及市容最是俄國化,有一條馬路叫「中國大街」,全部用石塊砌成,路燈明亮,寬敞的人行道上有座椅,兩旁大多是俄國人或歐洲人開的商店及餐館。哈爾濱開風氣之先,最先接觸歐洲的書籍、刊物、影片、唱片、美術、音樂、文學和歌舞,成為中國最為歐化的城市之一。
哈爾濱被國人稱為「東方小巴黎」,歐俄文化在城市裡日益發展,居民尤其是知識份子受到程度不等的潛移默化。俄語成了中國人所學習的第一種外國語。在這座華洋雜處、亦東亦西的都市,我生活了十七年,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初中畢業。我出生後,父母為我取名「聚聚」。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我這一生中最遺憾的事,是對自己的親生母親幾乎一無所知,就連同她的長相模樣都不復記憶了。她去世時我僅僅兩歲半,弟弟復成剛剛出生。我身邊曾經有過一張父親母親和我合拍的照片,後來,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繼佔領東北後向華北進犯,全國人民忍無可忍,奮起展開抗日戰爭。戰亂期間,學校停課,各地學生紛紛向大後方流亡,顛沛流離中,我遺失了這僅有的珍貴照片。
我只知道母親娘家姓李,名字不詳,出生於山東掖縣平裡店東路宿村。她是大姐,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和父親結婚後,到了哈爾濱,在那裡大概住了三四年,生了兩個孩子,年紀輕輕一生就結束了。她故去時有多少歲?因何病而喪生?我都不知道。那年代,從山東、河北到關(山海關)外闖蕩的人,假若在外死亡,靈柩一定要運回老家安葬。就為了這,父親辭去工作,安頓好兩個失去母親的孩子,護送母親的靈柩,離開哈爾濱,往山東老家掖縣平裡店朱由村。這是一段艱辛漫長的路程:得先乘南滿鐵路的火車,自哈爾濱到遼東半島尖端的商埠大連;在大連改乘輪船,橫渡渤海灣,到山東省煙臺;再從煙臺乘汽車沿煙濰公路(煙臺到濰縣)到掖縣平裡店;下車後,換乘由馬或騾子拉的大板車,走二十來裡田埂小路,其間經嬰裡村(晏嬰故里)、麻渠村(孫家世居)、東路宿村(我外婆李家住地)和西路宿村(復鈞兄弟外婆王家住地),最後到朱由村。朱由村是瀕臨渤海萊州灣的一個村莊,屬魯東掖縣(掖縣是軍閥張宗昌的家鄉,因他的胡作非為而聞名全國),大概有三百多戶人家,多半姓張。這裡的居民忠厚、樸實、勤儉、樂天知命。據說我家祖先是明朝張獻忠在四川大屠殺時,逃離成都,幾經播遷,終於定居魯東。到底有幾代在山東掖縣居住,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祖父張吉亨早年喪偶,膝下只有我父親張日高(字升三)和一個叔叔(不知道名字),世世代代以種田為生。
張孫兩家的老人們,大約在清朝光緒廿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前後從原籍魯東,隨著一批批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背著簡單的行李,不顧清廷禁令,千里跋涉,私自出關(山海關),赤手空拳地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東北闖天下。那個時候的東北,是俄國和日本爭吃的肥肉。俄國藉口代我向日本索還遼東半島,要求酬謝,獲得了在東北築鐵路的權利,並且租借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俄人在一八九八年,以哈爾濱為起點,向東、西及旅順大連三方面,分別鋪設路軌,於一九〇三年即以閃電方式建成中東鐵路。中東鐵路全長二千四百三十公里,以哈爾濱為中心,西北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修築鐵路需要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工,而當時山東、河北兩省民眾,因為在原籍謀生不易,紛紛冒險出關另尋生路。我的父親張日高和弟弟,才十七、八歲,有的是力氣,離開家鄉,隨闖關東的大流,到了完全陌生的東北。他們在冰天雪地之中,忍饑耐寒,走遍松花江流域的大小城鎮,胼手胝足,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吃盡苦頭,付出血汗的代價,建立起自己的家園,繁衍後代,家族日漸興旺。
這個開闢草萊的群體,年富力強,敢冒險,能吃苦,其中一部分人將多年積蓄投入工商業,另求發展,風生水起,漸漸掌握了東北經濟的命脈。另外一部分,苦學俄語,在鐵路築成後,成為中東鐵路局的員工。由於精通俄語,很受俄人重視,所獲待遇以金盧布計算,格外優厚。我父親在東北奮鬥了十餘年後,有了謀生技能,也薄有積蓄,遂返回老家成親,帶著新婚的妻子,再度返回哈爾濱。至於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叔叔,不知是和父親同時還是幾年後才動身,千里迢迢去了東北,一去就失去了聯絡,至今渺無音訊。
朱由村雖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長的地方,但是我對這個靠海的小村莊懷著深厚的感情。那是我們張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之處。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我兩次到朱由村去,那時我已就讀北平燕京大學,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山東老家,和從哈爾濱趕回去的父親相聚。我之所以沒有前去父親定居的哈爾濱,是因為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強佔東三省,對中國人百般刁難,對知識份子實行嚴密的控制,無辜者遭逮捕和殺害的消息時有所聞。因此,父親報我「已死亡」,名字從戶籍上取消。
一九三七年六月回朱由村的記憶至今清晰,我在燕大已讀完三年,還差一年就畢業,利用暑假,和父親約好在山東見面。我從北平乘津浦鐵路的火車到濟南,換乘膠濟鐵路火車到濰縣;下車後,改乘煙濰公路局的汽車,行駛三、四個小時,途經掖縣縣城,到平裡店。平裡店是煙濰公路上的一個小鎮,那裡有電報和郵政局。父親先我幾天到家,我抵達時他在平裡店迎接。父女兩人坐上早已雇好的騾拉板車,搖搖晃晃地順著麥田中間的土路緩緩前行,花了一個多小時,遠遠看見了老家那紅磚砌成的圍牆。牆內分三個院子,每個院子裡有一排三間的房子,房子雖老,但都經過整修,印象最深的是屋頂上鋪著一層層曬乾的海草(有人說是海帶),厚厚的,據說這種草產自當地,鋪在屋頂,不漏水不透風,使房子冬暖夏涼,便宜實用。家家戶戶都一樣,怪不得離村莊遠遠的,就聞到鹹鹹腥腥的海草味。記得三個相通的院子外,還有一個小裡院,院裡靠邊堆著燒火用的木頭、枯枝等雜物,不遠處有兩棵枝葉茂密、年年開花結果的桃樹,中間是一個露天的大糞坑(廁所)。一進大門的院子裡,住著大奶奶,她是父親的伯母,伯父早亡,無兒女,她由父親奉養。並排另一院子,兩明一暗的房屋,供父親和我暫住。院子裡還有一口深井,家中用水都由此汲取。夏天,趕集的日子(五天一集)一到,父親便去買些西瓜回來,盛在打水用的木桶裡,放進水井泡著,傍晚時一家子在院中乘涼,就吃上冰涼涼的西瓜。第三個院子裡,住著瞎了眼的奶奶。她不是我父親的生母,我親祖母在我父親十來歲時就故去了。
我所見到的庶祖母是怎樣嫁進我家的呢?我誕生以前,有一年山東幹旱,各地鬧饑荒。一批難民逃到我們村子裡,其中有一個寡婦,從平度那邊過來的,三十多歲,孤苦伶仃,在我家門前乞討。那時我家人口單薄,正需要人來照顧祖父及兩個稚兒,就把她收留了。從此我家就稱她為奶奶,那時她的雙眼還未失明。此後的年月,多虧有她撐持老家的一切家務,父親和叔叔才放心離開,到東北去謀生。祖父去世後,家中破屋她獨自居住,幾畝田地也由她照料,直到父親在東北立穩腳跟,賺了錢。父親陸續把錢寄回老家,把房屋整修重建,老人家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說到我的外婆家,我知道的就更少了,只知道姓李。李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與朱由村相隔十餘裡的東路宿村。外公外婆家中有四女一男,我母親居長。我兩次回朱由村,都到外婆家住一兩天。那時外祖父已去世多年,小舅舅也死了,家中只有外婆和四姨。二姨隨丈夫到東北一面坡經商,我沒有見過她;三姨到哪裡去了,我沒有印象;那時四姨已出嫁,丈夫到關外謀生,一去十幾年沒有音訊,四姨只好回娘家長住,和老邁的母親做伴。外婆的家境十分淒涼,茅屋僅可遮蔽風雨,教我看了十分難受,但我還在求學,並沒有收入,無力濟助。倒是父親時時不忘送點錢過去。那一晚,在外婆家過夜,三人睡在炕上,我和四姨睡一頭,外婆睡在另一頭,合蓋一床棉被。夜裡外婆緊抱著我的雙腳為我保暖,四姨則兩臂摟著我禦寒。唯一的小舅舅,模樣我到現在還清晰地記得。但記不清是哪一年,他大概只有十七、八歲,到哈爾濱投奔父親,父親介紹他去店鋪當學徒。父親第一次帶他進家,他穿藍布長衫,臉面清瘦。父親對我說:「這是你娘的弟弟,你親舅舅啊!」小舅興奮地握著我的小手,不自覺地流下了淚。以後他又來看過我幾次,有一次他咳嗽得很厲害,幾滴鮮血濺到地板上,從此沒有再來,父親說小舅舅有病回山東老家去了,不久聽說他死了。他來去匆匆,在我的記憶中只有這一點點。四姨個子高高的,瓜子臉,眉目清秀,落落大方。我對自己的母親沒有一點印象,直到現在,只要想到母親,眼前泛現的就是四姨的模樣。家鄉的人都說四姨長得很像當年的母親,而我又酷似四姨,這麼說來,我大概很像我的母親。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社會人文 |
$ 237 |
社會人文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歷史人物 |
$ 270 |
女性人物 |
$ 270 |
中國當代人物 |
$ 270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這部自述文稿和照片,記錄了一個在那個思想封建保守的時代,一位民間女子的奮鬥和人生經歷。文字裡有逾半世紀的戰火和動盪,有許多當年大江南北真實的生活民情,有血有淚、有情有愛,雖是筆墨輕談,敘述樸實,那份情真,卻很感人。
情至不嬌,雨潤無聲。最樸實的感情,猶如無聲的雨,悄然染溼天地,淡然如是,真實如是,深刻如是。——杜南發
「多年來,我所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的都是妻離子散或生離死別的人間大悲劇,而這些都是日本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所造成!這血海深仇永烙我心,中華兒女又豈敢稍忘?!」
書中簡單幾句話,凝聚著無數血淚的烙印!
淡然筆墨,血淚心情。文稿寫來,沒有浮爛的悲情,字裡行間,卻都是刻苦銘心的記憶,
永難忘懷的傷痛和義憤。
江山萬里,一片白雲,悠然飛渡;家國在心,天地浩氣,凜然長存。
她是在滿目瘡痍國土上、出生於松花江畔哈爾濱的小女孩;
她是在顛沛流離中讀完燕京大學,懷抱愛國憂民之心的女青年;
她以客觀的筆調,記錄了日寇鐵蹄下的民族之難與家園之苦;
她就是來自白山黑水、原籍山東萊州的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起親歷採訪
—徐州會戰、台兒莊大捷、徐州大突圍、魯南及湘鄂戰地
—武漢會戰、武漢大撤退、長沙大火、重慶大轟炸
—陝北延安、陝甘寧邊區、山西中條山游擊區
作者簡介:
張郁廉(1914-2010),偉大時代的一位傑出女性,其身影已淡出於世,然做為中華兒女在國家有難之際,其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抵禦外侮之事蹟,實為炎黃子孫永世傳承的典範。
TOP
章節試閱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聚聚」是父母為我取的小名。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一、取名聚聚,然我兩歲半就失去親生母親
我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夏天在哈爾濱霽虹橋(南崗通往道裡的要道)旁的中東鐵路局附屬醫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松花江畔的哈爾濱,是我國東北三大名城之一(另兩個是瀋陽和大連),「哈爾濱」三字是滿族語,意思是「曬漁網的地方」。當時的人...
「聚聚」是父母為我取的小名。後來父親告訴我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一、取名聚聚,然我兩歲半就失去親生母親
我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夏天在哈爾濱霽虹橋(南崗通往道裡的要道)旁的中東鐵路局附屬醫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松花江畔的哈爾濱,是我國東北三大名城之一(另兩個是瀋陽和大連),「哈爾濱」三字是滿族語,意思是「曬漁網的地方」。當時的人...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序言: 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 ⊙杜南發
上世紀九〇年代的一天,雕塑家孫宇立來電,約我到他的蘇菲亞山工作室。
蘇菲亞山是座鬧市裡的小丘,學者鄭子瑜住的建安大廈在上山前的路口,斜坡路盡頭是二戰前美術家林學大創辦的南洋美專,孫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間路段。
孫宇立是專業建築師,原任職於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都市重建處,回新加坡創業,為了興趣,毅然決定放棄建築專業,一心從事雕塑。八〇年代藝評家劉奇俊介紹我們認識,那時他正苦思創作路向,想解決西方拓撲學與中國易學之間的問題,多次與我深夜長...
上世紀九〇年代的一天,雕塑家孫宇立來電,約我到他的蘇菲亞山工作室。
蘇菲亞山是座鬧市裡的小丘,學者鄭子瑜住的建安大廈在上山前的路口,斜坡路盡頭是二戰前美術家林學大創辦的南洋美專,孫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間路段。
孫宇立是專業建築師,原任職於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都市重建處,回新加坡創業,為了興趣,毅然決定放棄建築專業,一心從事雕塑。八〇年代藝評家劉奇俊介紹我們認識,那時他正苦思創作路向,想解決西方拓撲學與中國易學之間的問題,多次與我深夜長...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篇 序言: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 杜南發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第一輯 離散歲月 (一九一四|一九三七)
第二輯 記者生涯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三輯 亂世沉浮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四輯 寶島年華 (一九四九|二〇一〇)
第五輯 緬懷母親,感念瓦娃 孫宇立、孫宇昭補記
第三篇 在前線—張郁廉來自前線的報導
編後記 孫宇立
第二篇 張郁廉自傳
第一輯 離散歲月 (一九一四|一九三七)
第二輯 記者生涯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三輯 亂世沉浮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四輯 寶島年華 (一九四九|二〇一〇)
第五輯 緬懷母親,感念瓦娃 孫宇立、孫宇昭補記
第三篇 在前線—張郁廉來自前線的報導
編後記 孫宇立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郁廉
- 出版社: 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6-11-16 ISBN/ISSN:978986579470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5頁 開數:18開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