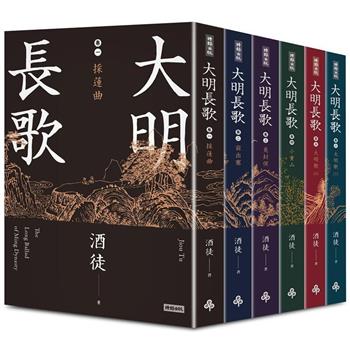從臺灣、韓國、中國、日本,再到新加坡,一個臺灣女子的亞洲行旅與文化思索;從文學、戲劇、藝術,到電視、電影、漫畫、流行音樂,穿透語言與文字的表相,深刻解析各種流行風潮所蘊含的文化底蘊。不管是和風還是韓流,臺灣一直受到不同的文化潮流所濡染,但是從更開闊的觀點來看,做為亞洲的一分子,在彼此不斷涵融與交流之下,或許彼此間的隔閡,並未如想像中來得遙遠。
名人推薦
亞洲重量級學人王潤華、白永瑞、孫康宜、陳芳明、藤井省三 一致推薦!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感觀東亞的圖書 |
 |
感觀東亞 作者:衣若芬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6 |
二手中文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文化研究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感觀東亞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衣若芬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兼中文系主任,並受邀為新加坡《聯合早報》專欄作家。曾經任職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教授。中國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日本國立奈良女子大學特邀訪問學者。日本京都大學共同研究員。
學術研究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行政院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領域為中國文學與圖像藝術、東亞漢文學與文化交流。
著有小說集《踏花歸去》、《衣若芬極短篇》;散文《青春祭》、《春衫舊香》、《紅豆書簡》、《Emily的抽屜》等書。學術論著有《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藝林探微:繪畫.古物.文學》,合著《蘇軾研究史》等書。
衣若芬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兼中文系主任,並受邀為新加坡《聯合早報》專欄作家。曾經任職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教授。中國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日本國立奈良女子大學特邀訪問學者。日本京都大學共同研究員。
學術研究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行政院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領域為中國文學與圖像藝術、東亞漢文學與文化交流。
著有小說集《踏花歸去》、《衣若芬極短篇》;散文《青春祭》、《春衫舊香》、《紅豆書簡》、《Emily的抽屜》等書。學術論著有《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藝林探微:繪畫.古物.文學》,合著《蘇軾研究史》等書。
目錄
序 和風韓流東亞心
輯一 和風
放心
一葉
司馬遼太郎的書畫
蠟筆小新搞什麼
坐在魯迅的座位
松島啊,松島
花信風
三度關西
尖叫在雲端──我的仙台印象手記
IQ84的時空
悲傷時我好想喊你的名字
岡倉天心的理想
大聲告訴他
三個真相.夏目漱石
未夢之夢.早稻田
不必再演了,李香蘭
空中
輯二 韓流
「學歷」與「學力」
很高興不認識你
申師任堂:紙鈔上的 「韓國孟母」
申潤福變性了
申潤福與東亞春畫
奧地裡的博物館
富而好美
看得出來
唯火是新
朝露
哥哥我是江南Style
韓式人生,Fighting!
阿里不是郎
撞臉
你是「國蹦」,還是「國黑」?
八佾舞有點長
安重根的藥指
今夜星兒也被風拂過
輯三 東亞心
小津安二郎在昭南島
鍾梅音的天堂歲月
蓮盡人已去──敬悼王叔岷老師
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
卜派國的英雄
天下誰人不識君
寶島,有一村
卡斯提拉砂糖粒
木魚掉進水裡
共和春炸醬麵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筆談
沈沒/默的船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
大人我要結婚
漢代遺香.蘇門答臘
吳哥沒有窟
後記 地球Sompoton
衣若芬生平與寫作記事
輯一 和風
放心
一葉
司馬遼太郎的書畫
蠟筆小新搞什麼
坐在魯迅的座位
松島啊,松島
花信風
三度關西
尖叫在雲端──我的仙台印象手記
IQ84的時空
悲傷時我好想喊你的名字
岡倉天心的理想
大聲告訴他
三個真相.夏目漱石
未夢之夢.早稻田
不必再演了,李香蘭
空中
輯二 韓流
「學歷」與「學力」
很高興不認識你
申師任堂:紙鈔上的 「韓國孟母」
申潤福變性了
申潤福與東亞春畫
奧地裡的博物館
富而好美
看得出來
唯火是新
朝露
哥哥我是江南Style
韓式人生,Fighting!
阿里不是郎
撞臉
你是「國蹦」,還是「國黑」?
八佾舞有點長
安重根的藥指
今夜星兒也被風拂過
輯三 東亞心
小津安二郎在昭南島
鍾梅音的天堂歲月
蓮盡人已去──敬悼王叔岷老師
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
卜派國的英雄
天下誰人不識君
寶島,有一村
卡斯提拉砂糖粒
木魚掉進水裡
共和春炸醬麵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筆談
沈沒/默的船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
大人我要結婚
漢代遺香.蘇門答臘
吳哥沒有窟
後記 地球Sompoton
衣若芬生平與寫作記事
序
序
和風韓流東亞心
在東京、在首爾、在香港、在臺北,我經常被人問路。我的一本散文集《青春祭》裡有一篇〈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說到了這事,我想,大概我長了一張親切和善的臉,還有隨遇而安的眼神。
日語、韓語、粵語、中文,人們依他們想像的可能,對我說各種話。在新加坡,我被問路時聽到的是英語。「對妳說英語是表示對妳的禮貌。」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語言的使用不只是身份的認同,也是對對方的某種認定。
我慨然接受陌生人對我的認定,我是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
受經濟影響帶動的全球化,已經把世界拉成扁平,滲透我們的生活。韓國的中國餐館過去強調「正統」、「正宗」,現在,炸醬麵成了韓國的國民日常食物。日本發明的「和風義大利麵」頗帶動過一陣子流行,打破了「和食」和「洋食」的界限,在義大利麵裡加進海苔和明太子,沒想到混著奶油白醬吃還別有風味。和「和風義大利麵」同樣原理的,是將中國傳入的拉麵日本化,湯頭換成味噌,配菜鋪上一片乳酪,這叫做「創意料理」、「無國籍料理」、「跨國界料理」。
食物的「無國籍」與「跨國界」,也就是新加坡餐廳標榜的fusion──融合、混搭。廚師調整了我們的味覺,配合不同地區食客嚐新的需求,以及酸、甜、鹹、辣的偏好,使我們吃著「可能合乎口味」的異國風情,比如日本帶甜味的「麻婆豆腐」。有人說:這是食物的「後殖民」,我們被訓練的舌頭,不容易回到及堅持「原汁原味」。
「移動」、「傳播」、「再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吧。人與物的移動,傳播了文化和思想,網路發射的即時訊息,迅捷得讓文化體之間同步無落差,便利的翻譯工具,加強文化思想的吸收轉化再生產,消減了國籍、種族、乃至於語言的隔閡。
這,就是大同世界的境地了嗎?
照理說,人們應該比過去還容易認識彼此,接納彼此,時事的發展卻不然。被趨於統合的味覺,並沒有掌控我們的大腦;我們選擇廚師為我們「本地化」的異國美食,也選擇看見或視而不見周邊的「他者」。
我的工作經常有機會移動於東亞,華人圈之外,就是日本和韓國。古代的日本和韓國,由於官方和上層社會使用漢字書寫,國際間記錄和溝通可以筆談,這一點歷史常識往往造成某些一廂情願和誤解誤用。最常以為的,是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稱做「同文同種」的兄弟友邦,說他們以天朝中國為中心,臣服歸順。誠如葛兆光教授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的,明朝滅亡後的十七世紀東亞,中國已經失去了國際秩序的指揮權。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各國,情勢更為複雜。
再說,即使同樣使用漢字,有的字詞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概念和意義是不同的。我初次聽大陸人說「我的愛人」,覺得挺異樣,知道是指「配偶」,但是臺灣人說的「愛人」是「情人」、「戀人」的意思,和韓國一樣。日本人說的「愛人」(あいじん)則是外遇的對象;「戀人」(こいびと)才是「情人」。
臺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和風」不息。一九九四年衛視中文臺首先推出張東健和沈銀河主演的韓劇「青出於籃」,自此「韓流」洶湧。「和風」與「韓流」吹拂波動著我居住的兩個島嶼──臺灣和新加坡,我沒有征服全球的壯志,我的觀看和寫作,只願安分地守著我的一顆東亞心。
繼續來向我問路,不介意,我學會了說日語、韓語和英語,那句重要的回應:「我不知道」。
和風韓流東亞心
在東京、在首爾、在香港、在臺北,我經常被人問路。我的一本散文集《青春祭》裡有一篇〈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說到了這事,我想,大概我長了一張親切和善的臉,還有隨遇而安的眼神。
日語、韓語、粵語、中文,人們依他們想像的可能,對我說各種話。在新加坡,我被問路時聽到的是英語。「對妳說英語是表示對妳的禮貌。」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語言的使用不只是身份的認同,也是對對方的某種認定。
我慨然接受陌生人對我的認定,我是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
受經濟影響帶動的全球化,已經把世界拉成扁平,滲透我們的生活。韓國的中國餐館過去強調「正統」、「正宗」,現在,炸醬麵成了韓國的國民日常食物。日本發明的「和風義大利麵」頗帶動過一陣子流行,打破了「和食」和「洋食」的界限,在義大利麵裡加進海苔和明太子,沒想到混著奶油白醬吃還別有風味。和「和風義大利麵」同樣原理的,是將中國傳入的拉麵日本化,湯頭換成味噌,配菜鋪上一片乳酪,這叫做「創意料理」、「無國籍料理」、「跨國界料理」。
食物的「無國籍」與「跨國界」,也就是新加坡餐廳標榜的fusion──融合、混搭。廚師調整了我們的味覺,配合不同地區食客嚐新的需求,以及酸、甜、鹹、辣的偏好,使我們吃著「可能合乎口味」的異國風情,比如日本帶甜味的「麻婆豆腐」。有人說:這是食物的「後殖民」,我們被訓練的舌頭,不容易回到及堅持「原汁原味」。
「移動」、「傳播」、「再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吧。人與物的移動,傳播了文化和思想,網路發射的即時訊息,迅捷得讓文化體之間同步無落差,便利的翻譯工具,加強文化思想的吸收轉化再生產,消減了國籍、種族、乃至於語言的隔閡。
這,就是大同世界的境地了嗎?
照理說,人們應該比過去還容易認識彼此,接納彼此,時事的發展卻不然。被趨於統合的味覺,並沒有掌控我們的大腦;我們選擇廚師為我們「本地化」的異國美食,也選擇看見或視而不見周邊的「他者」。
我的工作經常有機會移動於東亞,華人圈之外,就是日本和韓國。古代的日本和韓國,由於官方和上層社會使用漢字書寫,國際間記錄和溝通可以筆談,這一點歷史常識往往造成某些一廂情願和誤解誤用。最常以為的,是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稱做「同文同種」的兄弟友邦,說他們以天朝中國為中心,臣服歸順。誠如葛兆光教授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的,明朝滅亡後的十七世紀東亞,中國已經失去了國際秩序的指揮權。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各國,情勢更為複雜。
再說,即使同樣使用漢字,有的字詞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概念和意義是不同的。我初次聽大陸人說「我的愛人」,覺得挺異樣,知道是指「配偶」,但是臺灣人說的「愛人」是「情人」、「戀人」的意思,和韓國一樣。日本人說的「愛人」(あいじん)則是外遇的對象;「戀人」(こいびと)才是「情人」。
臺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和風」不息。一九九四年衛視中文臺首先推出張東健和沈銀河主演的韓劇「青出於籃」,自此「韓流」洶湧。「和風」與「韓流」吹拂波動著我居住的兩個島嶼──臺灣和新加坡,我沒有征服全球的壯志,我的觀看和寫作,只願安分地守著我的一顆東亞心。
繼續來向我問路,不介意,我學會了說日語、韓語和英語,那句重要的回應:「我不知道」。
衣若芬書於新加坡
二○一四年十月八日
二○一四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