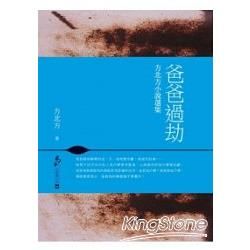【淑德流芳】
一
常太太和善的時候,就是笑得前仰後合,聲浪幾乎可以把窗簾吹開,在她身邊陪著笑的人,最多是嘴巴鬆一鬆,心中還是誠惶誠恐的,因為她變臉的時候,往往也幾乎要把人置於死地才滿意;就是有一隻椅子,偶然絆住她的腳,或者一隻蒼蠅舐了她的皮膚一下,她都要把它們當人一樣,踢它一腳,掃它一手,所以家中那隻人見人愛的小白貓一看見她,也要拼命跑開。難怪不論親疏,都給她起一個不名譽的綽號:虎婆。
常太太知道許多人暗地裡對她這麼稱謂,她恨之入骨。她說:要是給她耳頭耳尾聽見,別怪她無情,刻薄一點,一定要抽他們的筋骨。雖然如此,近鄰遠親,背後還是習慣地那麼叫她。
前天下午,左鄰阿香嫂,因小孩發生急驚,忽然窒息了;她一時慌張失措,便跑進常太太的家,向她求助。
常太太聽見香嫂公然稱她為虎婆,額角上兩顆眼睛,忽然變成了紫紅色的葡萄,滿臉的橫肉,一時不停地抽搐。然後,戟手指著香嫂額頭;如不是臃腫的身軀牽制了她的行動,對方的臉不流血也要受傷。然而她的嘴巴還像噴射器一樣:
「娼婦!什麼虎婆。目無王章,孩子死了,關我屁事。滾開!慢一點,我用掃帚蘸尿,你出去!」
香嫂失神地溜了。
她卻合十起來,口不停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事後,常太太解釋她的嘴巴固然有點潑辣,心地的慈祥卻為人所不知。她說她還是佛教徒,常常在懺悔之中過日子;她每天所以會嘴巴不停地罵人,她說這是心理變態後的一種需要。不這麼做,便用不著懺悔,不懺悔,她就無心禮佛了。
聽了她的話,使人似乎認為她是為了禮佛,才要罵人,因罵人出了名,才惹起不名譽的綽號。
也許是這樣,所以每個晚上,在丈夫下班踏入家門後,她嘴巴自然而然就開動了。比方昨晚,她又把家中的幾位孩子罵得他們心驚肉跳。
常太太的幾位孩子固然頑皮,卻不至於要那麼天天咒罵。因為十個孩子中有九個是好動的,她卻動不動一罵就大半天。孩子們的舉動,不論對與不對,點點滴滴,都加以指摘,一直罵到丈夫認為實在非罵不可,也光起火痛罵,她才技巧地轉了方向,把洩氣的對象移到另一個子侄的身上,大聲說:
「千事萬事,都是大夭壽教壞的!」
孩子們一聽到父母已轉換口氣罵堂兄了,驚魂才會消散,因為憑每次的經驗,咒罵到最劇烈時,堂兄一定是代罪的羔羊,他們就可以安心無事。雖然有時情形嚴重一點,責罰堂兄的藤鞭也可能落在他們的身上,不過是一種象徵式罷了!
其實堂兄雖比堂弟大了一二歲,卻規矩得多。一、他早孤,二、寄人籬下,年齡已經十三四,對人對事,畢竟比弟弟明白一些,只因常太太擔心丈夫真的會盛氣發洩在骨肉的身上,他才被認為是教唆堂弟變壞的主犯。
常太太卻認為她不這麼剿罵,就不能對死去的大伯有所交代,因為孩子不教不成器,所以為了希望別人的兒子好,她給予嚴厲的教育自然也是一種仁慈。
不過好幾次,常太太臥病在床上時,孩子們在姐姐的指示下,走近她身旁,表示對她關心;侄兒也恐懼地躲在堂弟們的背後,問候幾句。常太太卻粗聲厲色,咬牙切齒地罵道:
「夭壽仔,假親熱!老娘用不著你,我有兒女關心就夠,你去死!」
二
二十七年前,常太太還是李家的養女。
常先生娶她時,屈指算來,他來南洋已經十年了。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因為他也已經到達而立之年。
不過十年的苦鬥,對於常先生算是有點成就的。雖然保持完整的人格,與堅守只事耕耘不望收穫的苦處,不是局外人所能領悟,但以一跑街伙計,贏得建生李老闆的青睞,將他提升為司理,甚至獲得老闆娘的愛婢做妻子,在別人看來,確是一件體面的事;最低限度,也羨煞了好些同事,因太太年紀只有二十罷了。
常太太未出嫁時,所以被稱為李家愛婢,是因為老闆娘恐怕觸犯大人關(華民務司政)的禁例,在名義上不能不將她當作養女看待,就因為這樣她也以小姐的身分自視。於是自配給常先生之後,她也處處以為高他一級。何況她自小就看慣了常先生給李老闆呼喚過日,加以常先生又多她十歲,她肯嫁給他,在心理上已經看得起他了。所以常先生處處必須禮讓她三分,她認為是天公地道的。
誰知習慣成自然,就養成了她好強的態度。
記得去年常先生做五十六歲生日的前四天,常家準備好了在紅毛樓大草場開宴席二十四桌。常先生在家中客廳辦事桌上,列下了一張請客的名單,其中大部分都是跟常家在生意上有來往的。常先生看看名額二百四十多位,已經超過預定的,就對身旁的太太說道:「大後天所要請的人,大體就是這些了。」
常太太接過名單,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兩次,都看不到自己兩兄弟的名字,就有點不滿意地說:
「老常,名單上為什麼沒有我兩兄弟的名字?」
「什麼兄弟?」常先生才倒到躺椅上去,便漫不經心地答。
「你昏了,連我有什麼兄弟也不知!」太太認真地,「到底是真不知還是假不知?」
「李家老三與老四麼,怎麼會不知。」常先生雙手叉在腦後,笑一笑說。
「正是!」回答的聲音尖厲冷然。
丈夫也不客氣地說:
「稱呼得這麼親切,他們哪裡是你的兄弟?」
「什麼?老常!」太太暴躁地站起來,趨近常先生的椅邊彎著腰,兩顆紫色葡萄似的眼睛,幾將要跳出了眼眶,恨恨地指著常先生的額角,「你放肆!忘恩負義,膽敢欺負我,我問你,他們不是我兄弟是什麼?」
「雖然名義上是兄弟,」常先生站起來,「但你並不是姓李。」
「哦,原來如此,你想挖老娘痛腳?哪。好,你看我外家落魄了。……」常太太立刻兩手插在腰間睜大眼睛,氣沖沖地,幾乎要把對方吞進肚子去。
常先生一時忽略了太太平日的潑辣,所以馬上站起來,放低口氣巴巴結結地說:
「是,是,是你的兄弟;何必氣成這樣,我只不過說一說而已。」
「豈止說一說,你不是存心要挖苦我麼!忘恩負義的傢伙,沒有我們兄弟,你老常哪會有今日?」
「是麼!」常先生意內言外,故意拉長聲音。
常太太更光了火,聲色俱厲地嚷道:
「怎麼不是!」接著聲音如雷貫耳,「告訴你,老夭壽,我是婢女出身,如今要怎樣!」
「既然知道就好了!」
常先生說後轉身準備走開。常太太卻氣得臉青唇紫,一手巨靈掌似地就刮過去。常先生不提防被刮個正著,眼鏡玻璃都破碎,右瞳被割傷,出了很多血。常太太仍不肯放鬆,又一記從頭上捶下去。常先生的頭顱像頂住樹上跌下的椰子一樣苦楚,於是也粗野起來,反身一腳踢過去,正踢中對方的肚子,常太太一骨碌便倒下去,立刻號啕呼救:
「救命呀!老夭壽打死人呵……」
孩子們和媳婦都圍上來,七手八腳,分別把父親和母親扶住。
父親因傷勢嚴重,由大兒子立刻載進醫院去。大女兒與媳婦便準備將母親扶進寢室。常太太卻不肯起身,還是不停地放聲大哭,一面嚷著:
「我要老夭壽償命,我已經給他踢死了!」
大女兒輕輕地告訴她說:
「媽,爸也給你打傷進醫院去了。」
「該死!老夭壽會死,我才心甘情願。」常太太咬緊牙齦詛咒著。
「婆婆,事已過去了,讓我們扶你進寢室去。」媳婦扶著她的胳肢窩,要求著說。
「我不進去,我要與老夭壽算個清楚。」
大女兒傷心地說:
「媽,爸還重傷呢,要計較什麼?」
「是的,爸爸重傷進醫院去。」媳婦接著說,「計較什麼,婆婆,還是進房去吧!給孩子們看到你這樣,不好意思。」
「什麼不好意思,你竟幫起老夭壽來,也要欺負我是麼?」
「婆婆,姑姑也是這麼講,我哪敢欺負你。」
常太太輕蔑地說:
「哼!姑姑是什麼人,你知道麼?告訴你:她是觀音,你是水鬼!」
媳婦無可奈何地低著頭,沉默下去。但還是站著。常太太卻指著她說道:
「你不要以為你生了兒子就光榮。你豈知?其實是我會生兒子;兒子好,才會跟你生。」
大家都臉紅耳赤,不好意思地聽著,常太太也不厭煩地把常先生毒罵一番後,就轉罵到子侄的身上。
站在門旁的孩子們,一聽見堂兄被咒罵了,大家無不惶惶岌岌,因這一次鞭撻堂兄的藤鞭,很可能要落在他們的身上,甚至也可能不是象徵式的了。
果然那個晚上,堂兄被鞭得皮破血流,他們也同樣滿身藤痕累累。
三
今晨,天色破曉。
常家的傭人照例很早就起床準備料理早點,給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用後上學去。
往日,傭人起身後,常太太也一定出來打開大門,到草場散步、看花,然後回到廳上漱了口,一方面喝咖啡,一方面督責孩子們上學。
但,今早常太太反倒沒出來。
孩子們沒有長輩在身邊囉嗦,大家都吃得自然與痛快,於是七點鐘聲敲後,先後都出門去了。
八點過了,常先生也起床,走出客廳來。他喝完早點後,正想與太太交代幾句話,然後準備上商行去,因見不到人,便叫小孫兒上樓去叫祖母下來。
小孫兒下樓之後,告訴祖父說祖母睡著不動,叫也叫不醒。
常先生感到意外,因太太向來不會睡到這麼遲的,立刻就叫傭人上樓去請她下來。
不料,傭人在樓上驚叫著:
「不好了!不好了!」
常先生與家人馬上趕進太太房裡去,一看,太太眼睛翻白,身心冰冷。原來已僵硬多時。
一時噩耗傳開去,親朋戚友紛紛湧到常府來。不久,常府李夫人治喪委員會宣告成立。
為了敬告知交,預備明天由報上發表出去,於是大家都公推素稱喪訃文字老手的宰先生起草訃告。
宰先生也自告奮勇地承受下來,於是還未到上午二點,這篇堂之皇哉的「敬告知交」的鴻文,便呈獻在治喪委員會諸公的面前。
其中兩位委員素來十分欣賞宰先生的文字,所以要他把訃文宣讀一遍。宰先生也得意地展開金喉,高低抑揚朗誦道:
「新城海上街從興號東主常世德先生德配李夫人,閫號善和,秉性慈祥,尤嫻德婦。出身名族,賢聲卓著。自歸常府,相夫教子,有孟母風;家庭怡怡樂然。世德先生,長袖善舞,於社會商場中,卓著聲譽;子媳繼志述事,擴展基業,皆李夫人所勉勵訓導致之。常府英才輩出,子孫蘭桂,或大學畢業,或赴歐留學,有者服務國家,有者獻身社會,可謂一門俊秀,里黨鄉社,咸皆刮目稱讚。夫人方期克享遐齡,為世閫範,詎意一疾不起,竟於五月四日與世長辭。……」
宰先生朗讀未完,常府最小的兩個孩子,忽然問在場的一位親戚說:
「宰先生到底在念些什麼?」
那位親戚若有其事地答:
「他說你母親,淑德流芳。」
「什麼叫作淑德流芳?」其中一個問堂兄說。
「我也不曉得。」對方答:「大概是說從今起,我們不用挨打了。」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爸爸過劫:方北方小說選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43 |
小說 |
$ 387 |
中文書 |
$ 417 |
小說/文學 |
$ 431 |
小說 |
$ 441 |
小說 |
$ 441 |
現代小說 |
$ 441 |
文學作品 |
$ 441 |
中文現代文學 |
電子書 |
$ 49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爸爸過劫:方北方小說選集
1.作者方北方曾於1989年榮獲馬來西亞第一屆馬華文學獎。1998年獲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學獎。2000年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頒發終身成就獎。方北方一生秉承「文學為社會服務」的文學觀,作為大馬華族集體經驗與記憶的寫實見證人,他希望以自己的文字「為歷史留下點和線的輪廓」。本書是作者的小說集,收錄一系列短篇作品,方北方在故事中塑造了無數華社各階層的典型人物:教師、小文字員、小販、商賈頭家、爛賭的家庭主婦等。他以淳樸的筆調和生動的口語化文字,寫出充滿戲劇張力的短篇小說,一如奧亨利和莫泊桑,述盡了小人物的喜怒哀樂。
作者簡介:
方北方(1918-2007),
原名方作斌,生於中國廣東省惠來縣,1928年隨父南來檳城投靠伯父,同年父親病逝。1948年開始,先後任教於北海中華小學、孔聖廟中華中學、韓江中學、麻坡中化中學,1964年重返韓江中學,1989年卸任韓中校長。
方北方在1946年完成了首部長篇小說《春天裡的故事》(8萬字)。1954年中篇小說代表作《娘惹和峇峇》出版。長篇代表作有「風雲三部曲」:《遲亮的早晨》(1957)、《刹那的正午》(1962)和《幻滅的黃昏》(1976);「馬來亞三部曲」:《頭家門下》(1980)、《樹大根深》(1985)和《花飄果墮》(1991年初版時名為《五百萬人五百萬條心》)。曾任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第一屆副主席(1978-1979)、第二、三屆主席(1980-1984)。1989年榮獲馬來西亞第一屆馬華文學獎。1998年獲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學獎。2000年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頒發終身成就獎。
章節試閱
【淑德流芳】
一
常太太和善的時候,就是笑得前仰後合,聲浪幾乎可以把窗簾吹開,在她身邊陪著笑的人,最多是嘴巴鬆一鬆,心中還是誠惶誠恐的,因為她變臉的時候,往往也幾乎要把人置於死地才滿意;就是有一隻椅子,偶然絆住她的腳,或者一隻蒼蠅舐了她的皮膚一下,她都要把它們當人一樣,踢它一腳,掃它一手,所以家中那隻人見人愛的小白貓一看見她,也要拼命跑開。難怪不論親疏,都給她起一個不名譽的綽號:虎婆。
常太太知道許多人暗地裡對她這麼稱謂,她恨之入骨。她說:要是給她耳頭耳尾聽見,別怪她無情,刻薄一點,一定要...
一
常太太和善的時候,就是笑得前仰後合,聲浪幾乎可以把窗簾吹開,在她身邊陪著笑的人,最多是嘴巴鬆一鬆,心中還是誠惶誠恐的,因為她變臉的時候,往往也幾乎要把人置於死地才滿意;就是有一隻椅子,偶然絆住她的腳,或者一隻蒼蠅舐了她的皮膚一下,她都要把它們當人一樣,踢它一腳,掃它一手,所以家中那隻人見人愛的小白貓一看見她,也要拼命跑開。難怪不論親疏,都給她起一個不名譽的綽號:虎婆。
常太太知道許多人暗地裡對她這麼稱謂,她恨之入骨。她說:要是給她耳頭耳尾聽見,別怪她無情,刻薄一點,一定要...
»看全部
作者序
【代序二 爸爸】方成
爸爸躺臥客廳的床榻上。肖馬,爸爸他今年應該是八十九高齡了。他仰臥,眼神呆滯,雙頰塌陷。許是因為心肺衰竭而長期缺氧,饑渴著空氣便把兩個鼻腔撐開得老大,活像兩個黑風洞。嘴更是一扇撇開的大門,從不閉攏。他就那麼長年累月躺著,已經兩年。
我湊近他的臉龐:「爸,我是阿成!」
爸爸只是乾瞪著我。我湊上去他的耳邊:「爸爸,我是阿成!」
還是那瞎瞪著人的眼神,彷彿說著:「你,是誰,擾我清夢?」
可是爸爸的生命力堅韌頑強。我懷疑那是不簡單的眼神。我極少看過他被什麼擊倒。即使是他...
爸爸躺臥客廳的床榻上。肖馬,爸爸他今年應該是八十九高齡了。他仰臥,眼神呆滯,雙頰塌陷。許是因為心肺衰竭而長期缺氧,饑渴著空氣便把兩個鼻腔撐開得老大,活像兩個黑風洞。嘴更是一扇撇開的大門,從不閉攏。他就那麼長年累月躺著,已經兩年。
我湊近他的臉龐:「爸,我是阿成!」
爸爸只是乾瞪著我。我湊上去他的耳邊:「爸爸,我是阿成!」
還是那瞎瞪著人的眼神,彷彿說著:「你,是誰,擾我清夢?」
可是爸爸的生命力堅韌頑強。我懷疑那是不簡單的眼神。我極少看過他被什麼擊倒。即使是他...
»看全部
目錄
「馬華文學獎大系」總序
代序一 故事/方昂
代序二 爸爸/方成
導讀 動亂時代的人性激流―試論方北方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情懷/金進
儒林劫
淑德流芳
思想請假的人
讓我活下去
這就是生活
發財前後
醫生與病人
六親無親
人臉變化
點秋香
教書先生
不是六月流火
人狗之死
出嫁的母親
喜臨門
自討沒趣
人鬼之間
古屋裡的人
爸爸過劫
殘局
趙李兩家
江城夜雨
人性與尊嚴
吃來吃去
火在那裡燒
走險者言
白燈籠
愛屋及烏
殺妻案
死運
娘惹
代序一 故事/方昂
代序二 爸爸/方成
導讀 動亂時代的人性激流―試論方北方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情懷/金進
儒林劫
淑德流芳
思想請假的人
讓我活下去
這就是生活
發財前後
醫生與病人
六親無親
人臉變化
點秋香
教書先生
不是六月流火
人狗之死
出嫁的母親
喜臨門
自討沒趣
人鬼之間
古屋裡的人
爸爸過劫
殘局
趙李兩家
江城夜雨
人性與尊嚴
吃來吃去
火在那裡燒
走險者言
白燈籠
愛屋及烏
殺妻案
死運
娘惹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方北方
- 出版社: 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2-09-05 ISBN/ISSN:978986597661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