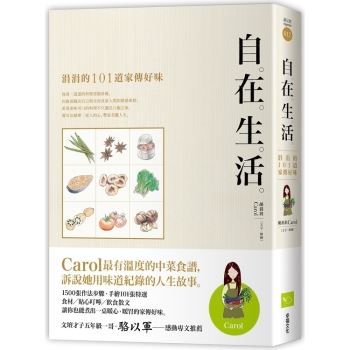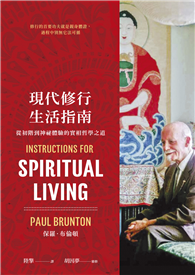二、異類生涯
(一)
一九五八年春天,一股名叫「總路線、大躍進」的強勁罡風吹進了校園。
一開始,天天學習檔,然後開始了行動。學生如何「躍進」?上面提出勤工儉學。班上開會討論貫徹,無奈「勤工」不是耍嘴皮子,需要動手來真格的。結果,議論了半天也沒有拿出一個項目。聽說別的班準備理髮、搞編織,有人提出,不妨六班也照辦。大家一致擁護。可是,事在人為,討論了半天,竟然沒有一個人應聲報名。
我這個人沒有大出息,卻一生興趣廣泛。每次到理髮店理髮,喜歡仔細觀察,認為理髮沒有大不了的難度。我的兩隻手並不笨,難道制服不了一把推子,幾撮頭髮?於是,便毛遂自薦:
「我可以給大家理髮。」
支書于恩光驚訝地問:「你會理髮嗎?」
我毫不含糊答道:「會!」
有人自稱有理髮的「技術」,儘管報名的是個右派,但給班上解決了一大難題。于恩光很高興。立即命人買來推子、剪子、刀子、梳子等一應工具。讓我立即上陣。
我只得臨時抱佛腳,立即跑到學校理髮室理了一次髮。連眼睛都不眨,認真看了理髮師傅的各種操作。回來便成了「理髮師」。支書帶頭,成了第一個試驗品。
不料,我犯下了一個狂妄的錯誤。世間許多事情,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是那回事了。連割草鋤地都是如此,何況是理髮!當我拿起推子,站到毛茸茸的腦袋前,立即產生了悔意。但大話已經說出,此時已無退路,只得硬著頭皮幹下去。儘管我仿照理髮師的動作,用上了全部心思,由於缺乏練習,心到手不到,等到理完了才發現,那「髮型」,就像戴了一頂瓜皮帽子,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萬幸,「試驗品」自己照了照鏡子,不但沒有發怒,指責我瞎吹,反而笑道:
「湊服,湊服,沒關係,熟能生巧。大膽的理就是。」
「你看他理的這髮型……」有人在小聲嘀咕。
于恩光打斷了那人的話:「孰能生巧,他越理,肯定會越好嘛。第二個就給你理!」
那年月,不論在任何地方,黨支部比一級政府的權威都大。支書發了話,那人也就只得勇敢地拿頭來讓我試驗。其實,我報名理髮,並不是故意惡作劇,潛意識裡是一種抗拒:你們什麼技術都不會,而我會理髮,雖是雕蟲小技,說明右派不比左派笨。你們平時昂首挺胸,對右派橫眉冷眼,理髮的時候,可要乖乖地把腦袋伸出來,讓我隨意收拾。
(二)
大躍進的罡風越吹越激烈。到處揷紅旗,放衛星。左派們今天到這裡寫調查報告,明天到那裡辦報。此等革命性極強的工作,右派們自然不配參加。「顧客」不在身邊,我的理髮「技術」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便與伍伯涵,江澤純、傅家訓、甘粹、雷凡、伍士傑、江之滸、朱紹武等難友一起,被安排到系資料室幫忙。任務是翻閱建國前的舊報紙,擇錄與新聞活動有關的資料做成卡片,為編寫《現代報刊史》作準備。具體負責的是新聞系資料室副主任王前。她是副校長聶真的夫人,劉少奇的前妻。不知是否因為遭遇過坎坷,深諳人的命運不可抗拒,人生的不幸難以預料。對右派們不僅沒有疾言厲色,而且溫和關注。對在她手下勞動改造的極右派林昭,更是關懷慈愛。甚至把自身的不幸與憤懣,偷偷向林昭傾訴。我就是在這裡認識了林昭。林昭來自北大,已經畢業,留校監督勞動。據說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人大時,新聞專業的負責人羅列欣賞她的才氣,將她帶了過來。她有肺病,臉色蒼白,咳嗽聲聲,人稱「林妹妹」。但頭髮濃黑,神態莊重。一雙大眼睛,晶瑩有神。我倆說話挺投機,有時在一起竊竊私語,互相傾吐輕信的苦衷,考大學的失誤。
不久,這位二十六歲的姑娘,跟單身漢甘粹談起了戀愛。一個星期天,他們偷偷約我出去玩,在景山公園和團城,給他倆照了幾張照片。二○○九年三月五日,《南方週末》刊出的那篇〈我為林昭拍了一張照片〉,就是寫的這件事。孰料,他們的戀愛,受到了總支書記章南舍的嚴厲批評:「不老老實實地改造,卻耍資產階級情調。你們想造反嗎?」兩人不服,索性申請結婚。章書記大怒:「右派有什麼資格結婚?」 「我們有公民權為什麼不能結婚?」「你們認為給了公民權,就可以為所欲為?笑話!」本想追求幸福,卻招來了大禍。甘粹立即被發配新疆勞改農場,一去二十多年,差一點把小命扔在那裡。不久,林昭因病回蘇州休養,據說因反革命罪被捕,由於拒不認罪,被判無期徒刑,繼續不認罪,再次升格——死刑。一九六八年的一天,當局向她家要五分錢子彈費,父母才知道女兒被秘密處死,但不告訴遺體在哪裡。她的老父親經受不住打擊憤而自殺。當過蘇州市政協委員的老母親被刺激瘋了,披頭散髮,四處遊走,不久後,淒慘地死在大上海的馬路上……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人民大學反右運動親歷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中國歷史 |
$ 316 |
歷史 |
$ 352 |
中國歷史 |
$ 36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人民大學反右運動親歷記
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人民大學反右運動親歷記
1957年,農曆丁酉,中國廣大知識份子,捧出赤誠的心,以主人翁的姿態,獻計建言,勇除「三害」。夢想讓祖國更興盛,執政黨更完美。熟料,耿忠的話音未落,引蛇出洞的「陽謀」,破土而出。忠言頓成毒鴆,獻誠盡是狼心。鐵冠加頂,名入另冊。醜惡的異類,從此墮入苦難的深淵。鄙視勞役,長達二十二年。骨堅者忍辱偷生,苦命者銜恨而去……
本書記載的,都是作者房文齋不堪回首的親身經歷,以及那些才華橫溢、卻無端蒙難的同窗好友,包括岳文伯、伍伯涵、李之傑、潘俊民、甘粹等的不幸往事。其中特別記載了著名「右派」林希翎震撼人大校園的著名演講、林昭及甘粹的戀愛悲劇;並且感嘆同窗潘俊民關注國計民生的泣血之鳴,剛過四十即悲慘死去的慘劇……。生動而翔實的記載,文筆警闢沉重,讀來,令人唏噓深思。
作者簡介:
房文齋
(1932年3月12日出生),筆名魯鈍。中國山東青島市人。1946年任小學教師,後在政府機關任職。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79年到高校任教。退休前,擔任教授。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發表專著《小說藝術技巧》、《揭密金瓶梅》,散文集《莽原霜花》,詩集《燼餘詩存》。及《論鄭板橋》、《論浪漫主義》、《〈金瓶梅〉作者考》等論文。出版長篇小說《鄭板橋》、《空谷蘭》、《辛棄疾》、《紅雪》、《夢斷秦樓》、《朱元璋》、《仰止坊》、《金瓶梅傳奇》等。
章節試閱
二、異類生涯
(一)
一九五八年春天,一股名叫「總路線、大躍進」的強勁罡風吹進了校園。
一開始,天天學習檔,然後開始了行動。學生如何「躍進」?上面提出勤工儉學。班上開會討論貫徹,無奈「勤工」不是耍嘴皮子,需要動手來真格的。結果,議論了半天也沒有拿出一個項目。聽說別的班準備理髮、搞編織,有人提出,不妨六班也照辦。大家一致擁護。可是,事在人為,討論了半天,竟然沒有一個人應聲報名。
我這個人沒有大出息,卻一生興趣廣泛。每次到理髮店理髮,喜歡仔細觀察,認為理髮沒有大不了的難度。我的兩隻手並不笨,難道制服...
(一)
一九五八年春天,一股名叫「總路線、大躍進」的強勁罡風吹進了校園。
一開始,天天學習檔,然後開始了行動。學生如何「躍進」?上面提出勤工儉學。班上開會討論貫徹,無奈「勤工」不是耍嘴皮子,需要動手來真格的。結果,議論了半天也沒有拿出一個項目。聽說別的班準備理髮、搞編織,有人提出,不妨六班也照辦。大家一致擁護。可是,事在人為,討論了半天,竟然沒有一個人應聲報名。
我這個人沒有大出息,卻一生興趣廣泛。每次到理髮店理髮,喜歡仔細觀察,認為理髮沒有大不了的難度。我的兩隻手並不笨,難道制服...
»看全部
作者序
編入本文集的文章,有的選自十多年來的遵命答卷,有的是在耄耋之年記下的殘缺回憶。既然記憶已經「殘缺」,為何還要嘮叨不朽?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倘若開明的當局,稍有愧悔之意,不再掩耳盜鈴,正確對待歷史,何用我輩草民,拙口鈍腮,說三道四?須知,摭拾當年的傷痛,撫摸結痂的傷疤,並不是一件愜意的事。況且往事紛如煙塵,情景難摹,追思不及。往往抓耳搔腮,久久停筆踟躕,實在是一件力不從心的苦差事。往事淒惻,不堪回首。寫到傷心處,難免感歎唏噓,潸然淚下……
我之所以自找苦吃,無他,搶救記憶,保存史料。讓年輕一代知道,...
我之所以自找苦吃,無他,搶救記憶,保存史料。讓年輕一代知道,...
»看全部
目錄
「無冕之王」的夢魘──獻給反右派運動中受傷害的同學/華鳳蘭
第壹章 難以忘卻的往事──我為林昭拍了一張照片
第貳章 躍過龍門是深淵──我的金色大學夢
第叁章 無邊苦海何處岸──「加冕」後的悲喜劇
第肆章 柔腸何曾忘蒼生──記林希翎在人大分校的一次發言
第伍章 獻盡忠悃成魑魅──記幾位落入「網罟」的大學同學
第陸章 無罪者的贖罪──留校右派學生的「賤民」生涯
第柒章 一顆明星的隕落──沉痛悼念潘俊民同學
第捌章 亡命走長白──我在文革中的三年逃亡
第玖章 不盡的思念──難友傅家訓逝世一周...
第壹章 難以忘卻的往事──我為林昭拍了一張照片
第貳章 躍過龍門是深淵──我的金色大學夢
第叁章 無邊苦海何處岸──「加冕」後的悲喜劇
第肆章 柔腸何曾忘蒼生──記林希翎在人大分校的一次發言
第伍章 獻盡忠悃成魑魅──記幾位落入「網罟」的大學同學
第陸章 無罪者的贖罪──留校右派學生的「賤民」生涯
第柒章 一顆明星的隕落──沉痛悼念潘俊民同學
第捌章 亡命走長白──我在文革中的三年逃亡
第玖章 不盡的思念──難友傅家訓逝世一周...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房文齋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05-27 ISBN/ISSN:978986609479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