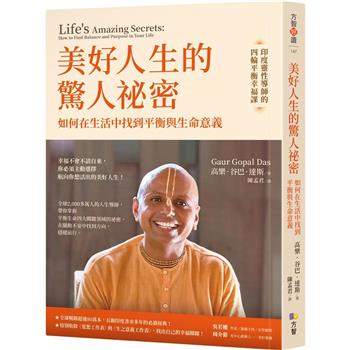一件怪事。長期以來,這個人物一直伴隨著我,同時也伴隨著馬拉美、康托爾、阿基米德、柏拉圖、羅伯斯比爾、康拉德……(而這還沒有探索我們自己國家的名單呢)。十五年前,我寫了一部戲《安提阿事件》,女主人公也叫保羅。性別的變化或許防止了一種太明顯的認同。如果說真話,我認為保羅既不是使徒也不是聖徒。我不在乎他傳佈的福音,也不在乎已形成的保羅崇拜。但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體人物。我讀那些書信時總是要回到已經特別熟悉的古典篇章中去;道路已經踏平,細節已經消除,力量也儲存起來了。當它們觸碰我的那一刻,沒有超驗的東西,沒有神聖的東西,只有這部著作與每一部其他著作之間的完全平等。一個人刻意寫下了這些句子,這些熱烈溫和的話,而我們將隨便地選擇它們,不帶任何誠意或反感。在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由於祖上就不信宗教,我的四位祖父母都是教師,他們甚至鼓勵我去打破神職的醜行。我很晚才看到這些書信,就彷彿遇到了新奇的篇章,其詩意令我震驚。
從根本上說,我與保羅從來沒有真正的宗教上的過往。我長期以來對他感興趣不是由於這個語域,也不是要見證某種信仰,更不是反信仰。說實話,我對保羅的興趣不過與我對巴斯卡、克爾凱郭爾或克勞戴爾的興趣一樣——但印象沒有他們那麼深刻,這是基於他們論述中明顯的基督教內容。無論如何,藝術和思想的原料於這個熔爐中得以冶煉,卻充滿了無名的雜質;包括偏執、信仰、幼稚的困惑、各種變態、不可吐露的記憶、隨意的讀解,還有許多愚蠢的言論和妄想。拆解這樣一個坩堝幾乎毫無用處。
對我來說,保羅是描寫事件的詩人思想家,他所實踐和陳述的不變特性可以被稱作激進人物。他在關於斷裂、推翻的一般觀念與其中主觀物質性的思想實踐之間,建立了完全屬於人類的關聯,而這種人類連繫的命運令我深深著迷。
如果我今天想用幾頁紙追溯保羅書信中這種關聯的獨特性,那或許是因為人們現在正在廣泛尋找一個新的激進人物——即便同時否認了這種可能性——以繼承二十世紀初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所佔據的位置,這可以說是黨的激進領袖。
向前走是時代的潮流,但我們仍然能在最大步伐的後退中找到幫助。於是便有了保羅的這次復活。我並不是第一個冒險把保羅與列寧加以比較的人;列寧的基督將是有待爭議的馬克思。
顯然,我的意圖既不是歷史探討,也不是篇章詮釋。這是徹底的主觀行為。我嚴格地局限於當代學術所認可的、與我思想相關的那些保羅書信。
至於希臘文原文,我用的是《希臘文新約全書》,是一九九三年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出版的Nestlé-Aland的批評版本。
基本的法文版本是我有時稍作修改的一九九三年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出版的Louis Segond的《新約全書》。
保羅書信的引文是按習慣的章節安排的。因此,「羅I:25」意思是羅馬書一章25節。同樣,「加」指「加拉太」,「林前」和「林後」指哥林多前書和哥林多後書;「腓」指腓立比書,「帖前」指帖撒羅尼迦前書。
對於想要深入探討的人,我願意至少推薦兩部關於保羅的重要文獻:
Stanislas Breton的一本非常扎實的小書,Saint Pau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0)。
Günther Bornkamm’s Paul, translated by D. M. G. Stalk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一個天主教徒,一個新教教徒。願他們與一位無神論者構成一個三角。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的圖書 |
 |
聖保羅: 普世主義的基礎 作者:巴迪烏 出版社: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6-25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宗教79折起 |
$ 229 |
中文書 |
$ 229 |
基督宗教 |
$ 229 |
Others |
$ 234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
在本書中,巴迪烏閱讀出保羅思想的政治性,並透過保羅這個人物精彩地詮釋了復活、受難(死亡)、恩典、信望愛等傳統基督教視為重要的主題。巴迪烏認為保羅是一位革命家,而分析出保羅對其所處的環境與世界觀提出激進的反抗思想。他逐步地梳理保羅如何在基督教信仰的復活事件中尋找到一種更新與突破的可能,及其如何區隔並面對與先知(希伯來)、智者(希臘)思想的差異之處。
作者簡介:
巴迪烏(Alain Badiou)為巴黎高等師範院榮譽退休教授、原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當代法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劇作家以及小說家,當今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受過數學和心理學的訓練,關注哲學、政治及現實問題。巴迪烏是法國後結構主義之後,挽救哲學及左翼政治的原創性思想家。他可說是大器晚成,在其著作《存在與事件》發表十年之後才開始受到法國人的關注,而取得世界性聲譽更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事情。他出版了大量著作,廣泛涉及本體論、數學、美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性別政治,逐漸在各領域產生影響。主要著作有:《模式的觀念》、《矛盾理論》、《主體理論》、《哲學宣言》等。
譯者簡介:
陳永國,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發表學術《理論的逃逸》等四部,譯著和編著理論著作30餘部。現從事西方文論、外國文學和翻譯理論的研究工作。
作者序
一件怪事。長期以來,這個人物一直伴隨著我,同時也伴隨著馬拉美、康托爾、阿基米德、柏拉圖、羅伯斯比爾、康拉德……(而這還沒有探索我們自己國家的名單呢)。十五年前,我寫了一部戲《安提阿事件》,女主人公也叫保羅。性別的變化或許防止了一種太明顯的認同。如果說真話,我認為保羅既不是使徒也不是聖徒。我不在乎他傳佈的福音,也不在乎已形成的保羅崇拜。但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體人物。我讀那些書信時總是要回到已經特別熟悉的古典篇章中去;道路已經踏平,細節已經消除,力量也儲存起來了。當它們觸碰我的那一刻,沒有超驗的東西...
»看全部
目錄
【目錄】
中譯本導言…曾慶豹
序 言
第一章 保羅:我們的同時代人
第二章 誰是保羅?
第三章 文本與脈落
第四章 論思理論
第五章 主體的分化
第六章 死亡與復活的反辯證
第七章 對抗律法的保羅
第八章 作為普世力量的仁愛
第九章 希望
第十章 普世性與差異的橫越
第十一章 結論
中譯本導言…曾慶豹
序 言
第一章 保羅:我們的同時代人
第二章 誰是保羅?
第三章 文本與脈落
第四章 論思理論
第五章 主體的分化
第六章 死亡與復活的反辯證
第七章 對抗律法的保羅
第八章 作為普世力量的仁愛
第九章 希望
第十章 普世性與差異的橫越
第十一章 結論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阿蘭‧巴迪烏 譯者: 陳永國
- 出版社: 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7-05 ISBN/ISSN:978986613104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44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基督宗教
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 相關搜尋
卡巴拉生命之樹解密:探索卡巴拉祕要,用古老智慧開啟命運之奧問神解籤萬用書90%宮廟都能用:《神明所教的60甲子解籤訣竅》(暢銷紀念版)+《問神達人雷雨師一百籤解籤大祕訣》(暢銷經典版)+「招財防漏錢母+存摺套」
樂空捷道:至尊金剛瑜伽母那若空行不共成就法生圓次第極密導引
心學大意:內學年刊第1輯
隆根法師開示語錄
打造強韌內在的少林精神:歐洲掌門人給你的13個日常練習
八大神話時代的解讀,重構神話在歷史與信仰中的影響:將神話置於多學科視角,融匯史學、文學與人類學觀點,強調其歷史化與文化基因的意義
尋找上師:師父說
阿彌陀經白話解釋
你的心有一道牆:人生沒什麼放不下,在紛紛擾擾中活出豁達心境的29帖安定禪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