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詩獎」讚辭
揭露俗世的虛假,衝決創作的禁忌,陳克華的情感、思想,既豐
富圓熟,又迭生奇異新穎之姿。近年他以赤裸的現世愛戀,戰慄的劫
後想像,挑逗感官與心靈,在靈與肉、圓與缺、捨與不捨的多重叩問
中,開拓曖昧美學的視野,鑽深語言的表現意境,才華洋溢,顯然是
啟發新世代詩人的風格名家。
年度詩選推行委員會 讚詞
生命的洋葱
─2009年臺灣詩獎得獎感言
陳克華
大學時期從各大報的文學獎踏入文壇,已是近卅年前的
事了。年近知天命,「獎」似乎於我不再像從前那般富有激勵
的作用,反而像是「獎」在凝視著我,檢查著我過去詩的進程
中,又完成了些什麼,又多看見了些什麼,多剝了幾層「生命
的洋葱」。總覺得人生苦短,多些「無止盡」或近永恆的東西
總是好的,詩便是我生命裡少數看得出是「無止盡」的行當。
而其最迷人之處在於他的自然,像嬰兒睜眼,心眼與世界同時
相互看見彼此,像雲停在無波的潭面,上下都是天空。常嚮往
寫詩能寫到這種境界,有如老子說的:「為道日損」,直到什
麼都丟光了,只剩下明亮無礙的心,見山是山,映照萬物萬
象,回歸於一。很高興卅年之後再度與獎相逢,證實自己不是
那種把得獎當作「撈一票」的作者-寫詩,終於可以是件「自
受用」的事了。
寫給複製人的十二首情歌(之二)
陳克華
你擁有和我一樣透明的唇
你擁有和我一樣透明的唇
和一樣渾沌迷離的心
可以說出如身體一般 血肉豐滿的字語和音節
虛空一般纏繞而困頓的語調和氣息──
從你透明的雙唇之間我看見
如根糾結的血管和脂肪
和饑餓而強壯的,濕淋淋的
驍勇的舌──血管裡奔馳的血球
漬染著黝暗如冬葉的血紅素;
脂肪如陰天的雲
因風暴的逼近而迅速堆積─
你靜默著,長久靜默著讓我讀你的唇
我看見布滿細胞的天空瘋狂下著淚
是的,我讀懂了你如電腦螢幕的臉頰
初次浮現出人類的表情
來到人間的第一個感受─
當我不禁深深吻著你的時候
聽見你的唇這樣裂開
天與地一般地裂開
說:
痛。
《自由時報》副刊 2009年8 月24 日
▎作者自述
畢業於臺北醫學院醫學系、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 Massachusetts, USA)、史蓋本眼科中心(Schepens
Eye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員。
現任臺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角膜科主治醫師、國立陽明大學眼
科副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工程組兼任研究員、國防醫學院醫
學系臨床副教授、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曾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
人文中心委員、醫學會中眼會訊總編輯。
▎關於本詩
這是一首藉由科技「複製」人類的情節,反思何謂生命及人的
詩作。全詩由愛欲無明作出發的原點,廣義而言,也可視為原始佛
教「十二因緣」的演譯。
我又問土耳其朋友阿里一個有關身分的問題
李有成
我又問土耳其朋友阿里一個有關身分的問題:
「你究竟是亞洲人,
還是歐洲人?」
時間:二○○八年四月十七日
地點:土耳其伊斯坦堡
場合:一個討論性別身分的學術會議
阿里怔了怔,沉思良久
最後露齒微笑地說:
「我不必是歐洲人,
也不必是亞洲人,
我可以是地中海人。」
我低頭黯然神傷:
我問了阿里一個政客的問題
阿里卻給了我一個學者的答案
《聯合報》副刊 2009年1月31日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2009臺灣詩選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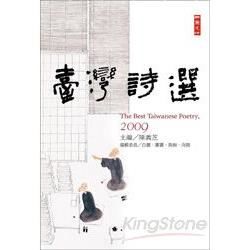 |
2009臺灣詩選 作者:陳義芝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5-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2009臺灣詩選
此書為二魚文化年度詩選,邀請陳義芝為編輯委員,選出2009年台灣老、中、青三代詩作共七十多首,創作題材廣泛,作品雋永而優美,透顯出臺灣詩壇豐富而多樣的面貌。並於每首詩作後附入作者簡介,與作者描述其詩作,豐富了本書的內容。
走過動蕩的2009年,唯有詩讓人佇足片刻。二魚文化推出《2009臺灣詩選》邀請您品味2009一整年老中青三代詩人耕耘一年的成果。
今年入選詩人共75家,首次入選詩人約12人,女性詩人約15人。其中陳克華更以〈寫給複製人的十二首情歌〉獲年度詩獎提名,陳克華嘗試以佛理直觀複製人,觀痛是痛,觀苦是苦,捻出2009臺灣詩特色-「悲憫」。同樣以憐憫之眼觀看世界,江自得看到血淚交織的臺灣殖民史、詹澈端視勞動者的辛酸、吳音寧以反諷口吻工人,曾貴海記台灣五十年大水莫拉克颱風……
從邊緣看向世界,二魚文化僅以本書,獻給動蕩的2009年。
作者簡介:
陳義芝,一九五三年生於臺灣花蓮,成長於彰化。一九七O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並於大學講授現代文學。著有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等,另有散文及論評出版。曾獲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獎、詩歌藝術創作獎、臺灣詩人獎。
章節試閱
「年度詩獎」讚辭 揭露俗世的虛假,衝決創作的禁忌,陳克華的情感、思想,既豐富圓熟,又迭生奇異新穎之姿。近年他以赤裸的現世愛戀,戰慄的劫後想像,挑逗感官與心靈,在靈與肉、圓與缺、捨與不捨的多重叩問中,開拓曖昧美學的視野,鑽深語言的表現意境,才華洋溢,顯然是啟發新世代詩人的風格名家。年度詩選推行委員會 讚詞生命的洋葱─2009年臺灣詩獎得獎感言陳克華大學時期從各大報的文學獎踏入文壇,已是近卅年前的事了。年近知天命,「獎」似乎於我不再像從前那般富有激勵的作用,反而像是「獎」在凝視著我,檢查著我過去詩...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義芝
- 出版社: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5-25 ISBN/ISSN:978986649032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圖書評論 - 評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