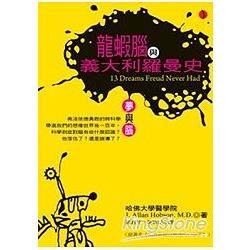作者序
Prologue: Sigmund Freud Imagined
弗洛依德自白想像
一八八五年,當時我只有二十九歲,就開始把對腦的所知寫進心理學。十年後的一八九五年,我三十九歲,我已準備要出一本希望是我的力作《科學心理學的專案》(The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到二十一世紀初,大部分人提到此書,僅以《專案》稱之。我想以深厚腦學為根基的心理學,建立一個「深刻而毫無疑問」的理論。結果事與願違。但我必須說,腦科學(brain science)畢竟突飛猛進,替真正的心智科學(science of the mind)開創新頁。
在醞釀撰寫《專案》時,交叉影響我年少雄心的是許多科學家相信的結果,那就是物質主義終將勝過理想主義。我在維也納醫學院的導師梅爾涅(Theodor Meynert)是最早簽署「反對生機論盟約」 (Pact Against Vitalism)的四君子之一(譯注:生機論者認為,凡生命體都有一種特殊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無法用物理或化學作用的現象來解釋。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就相信此特殊生命力,認為生命源自靈魂)。梅爾涅與我(受他影響)立志要以細胞與分子,來解釋所有的生命過程,包括人的心思。對我們而言,凡事皆有其生理學根據。甚至人類的思想和感覺都起源於身體,而我倆的任務就是展示為什麼會如此。
「反對生機論盟約」合撰者之一是偉大生理學家荷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譯注:科學心理學開山始祖繆勒的幾位弟子中,荷姆霍茲率先發表「反對生機論盟約」,宣稱生理系統根據的是物理與化學定律〕。「反對生機論盟約」讓我們免於把任何部分的人類經驗視為神奇的力量,尤其是空泛而界定錯誤的「生命力」(life forces),以此解釋,不過是迴避問題,而無法說明問題。說這些重話及加入「反對生機論盟約」,都是為了提醒自己別掉進神祕的陷阱,我們許多同儕就受其誘惑。我很自傲屬於這一學派,並誓死堅信,生理學和化學終將取代所有我對心智的看法。
我推崇英國科學家達爾文的許多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書,公然抗拒創造論,而創造論就是生機論的主調。我從小就不信神,不足為奇,因為當時的社會制度禁止人們反對組織性的宗教及宗教對神祕主義的援引。到了一九二七年,當我撰寫《迷幻》(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這本對抗性的小冊子時,我創立了心理分析,並希望心理分析能成為一門新的心智科學。我將心理分析用於宗教,並爭辯說,所有宗教行為與觀念都由神經引起。我甚至進一步說,宗教信仰乃妄想,不僅僅只是表面的神經失常,而是嚴重的精神病。
神經生物學非常投我所好。在維也納大學的實驗室,我們研究淡水螯蝦(crayfish)鉗的開合肌肉。螯蝦的鉗子與人類的思想與感情,看來風馬牛不相及,但我們知道我們是以細胞與分子在分析低等螃蟹的動作,而不是把這些活動歸為神奇的生命力。如果運動可以輕易理解,對我們就非常明白,其他動態的生命程序也能經由神經生物學得到解釋。我們在實驗室或維也納咖啡館喝咖啡與抽雪茄時,講的就是這些事。
如果當時有人給我一個在大學當專任的工作,我很可能就接受了。很不幸,沒人請我去做實證科學的工作。初為人父和丈夫,需要看病患來養家活口。但我從未放棄學術上的野心。我受過良好的神經學訓練,一八八八年時已經小有名氣並受學術圈敬重,夠格受邀撰寫百科全書有關失語症(aphasia)的詞條,此症狀通常發生在左上腦中風受創。失語症及腦傷引起的其他人類較高級心智功能的喪失,完全符合我以腦為基礎的心理學計畫。想望、驅力,甚至夢都應被視為腦的活動,但我們對腦所知少得可憐。
在我剛要開始看神經病患時,在英國工作的牛津大學生理學教授薛靈頓(Charles Sherrington)正好發表著名的反射學說(reflex doctrine)。運動系統(包括淡水螯蝦的鉗開合機制)由反射動能所控制,就當時而言,看來明顯也有用。但我能否僅憑反射學說來建立心理學?我寄予希望,也試了,但不成。
我知道腦就像動物的組織,由細胞組成。德國偉大的解剖學家∕病理學家費爾克(Rudolf Virchow)已提出著名的「所有細胞來自細胞」(omnia cellula ex cellula)的細胞論,就是說所有的細胞來自已存在的細胞,當然是指第一個細胞形成及之後成長發展過程中分化出的後代細胞這種遺傳機制。細胞被視為人體器官包括腦與脊椎神經的基礎。薛靈頓以細胞理論,從興奮與抑制彼此掙扎的觀點,證明反射行動。但我們對神經細胞如何組構所知不多,對它們如何運作更是陌生。
我很自然地被偉大的德國解剖學家希斯(Wilhelm His)與克利克(Rudolf Ko+..lliker)提出的腦網狀理(reticular theory of the brain)吸引,兩人與西班牙後起之秀拉蒙│卡哈爾(Santiago Ramony Cajal)對抗。卡哈爾認為,神經系不是個細胞結成網狀的融合體(syncytium),如網狀學者所相信的。對卡哈爾,腦細胞像網脈般地結合,但每個神經細胞並不相連,而是由薄膜連結。卡哈爾的看法在當時被多數人接受,他的神經元理論帶領許多重要的發現,對我也真的有用,如果我能堅守早先「專案」的路線,雖然專案的命運多舛。但我真的看不出這場神經元的激辯,對我的以腦為主的心智模式有何幫助。顯然做我想做的時機未到。
一八九五年,三十九歲的我陷入知識與個人的困境。我在家看神經病患,通常找不出他們諸多症狀的器質性(organic)病源。病患的抱怨看來多與功能有關,當時,我與耳鼻喉科醫師佛萊斯(Wilhelm Fleiss)往來密切。他相信,數字決定行為,一個人鼻子的大小與性渴望有關。佛萊斯和我一起討論許多個案。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伊瑪(Irma)個案,當發現伊瑪長期的鼻腔病不是由她的生日或鼻子大小造成,而是佛萊斯在替她做手術時留下一片海綿所引起,對我們不啻是個專業打擊。
這次醫療疏失應該讓我警覺,更早切斷與佛萊斯的往來,也應該讓我在解析我夢到伊瑪打針時更加謹慎。但我和佛萊斯因為更相信,許多病患的症狀是由性壓抑引發,而未分道揚鑣。之後我稱此過程為壓抑(repression),進而指出壓抑來自潛意識。性表白在十九世紀的維也納確實受到壓制,尤其是有能力來找我們看病的富家女。
事實上,是我為佛萊斯及他的許多觀念著迷,雖然我生性好強,無法接受他有關數字與鼻子的玄說。他讓我相信,生命的成敗主要繫於星象規則,利用數字理論可加以分析預見。這比生機論更糟。但我竟忽略。我被孤立,需要一位願意接受我自己不夠成熟觀點的同儕。現在回想起來,感覺真嚇人,我竟然真的把他的鼻子與生殖器直接相關的概念當一回事。當佛萊斯替伊瑪動手術時,他認為修改鼻子是在醫治她陰部冷感。真是瘋了。
但佛萊斯是我的朋友,死忠支持者。在我力爭知識事業時,他是我的夥伴。之後,當我走出自己的路,要拒絕心理分析上最重要的夥伴榮格(Carl Jung)就容易多了,因為他相信神鬼(spirits)。當時,榮格也是我的眼中釘,因為他認為,我太重視性對形成正常與異常心理的作用。現在回想起來,我首次拒絕佛萊斯,是因為他的數字與鼻子觀念讓我覺得尷尬,但我從未放棄我倆對性共有的偏執。當榮格拿性壓抑對神經形成時的作用挑戰我時,我則以他的神祕主義駁斥他。根據對自己的描述,我是位嚴謹的科學家,不是巫師。我知道我是個冒險家甚至自稱為征服者。但我從未發現自己會是心靈主義(mentalism)教派的大祭司。這表示我掉進了簽署加入反對生機論盟約本該避開的每一個陷阱。
《科學心理學的專案》寫於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發現大錯,我甚至無意出版。我清楚地看出,對於腦部如何運作我顯然所知有限,不足以建立一個滿意的心智理論。我知道沒有腦學為本,我就像遊走於混沌的主觀世界,但我別無選擇,所以我放棄腦學,或至少盡力與之一刀兩斷。
每天認真看門診,只有在晚上才有時間研究我的「專案」,這是份苦差事,因為我只有極少的科學證據可用;我自以為是扎實的科學,結果都是謬誤的;例如,我對反射動作的看法,一部分借自薛靈頓,是錯的。
根據一八九五年的神經生物學(neurobiology),所有進入腦部的能量與資訊,來自外在世界。我從未想到神經系統本身可以產生能量與訊號。還有,我錯誤地假設,神經系統無法防止外部刺激能量的入侵。想了解這個觀點,不妨假想一棟無避雷措施的房子,在暴風雨來襲時會如何。當閃電撞擊地面,這種房子難擋閃電帶來的熱(與火)的攻擊。
更糟的是,我以為外在能量與訊號進入神經系統,必然留下不走,會像我想的蓄勢待發,直到像做運動一樣得到釋放。所有這些錯誤的看法與幻想,是我的專案的重要部分。難怪我一籌莫展。放棄也就不奇為奇了。我很自傲看出我的專案一無是處。
即使放棄了專案,我仍相信,腦在處理大量外來能量時,會將其導入意識無法進入的迴路。我尋找科學的出口,要告訴世人我的想法,並形成原本期盼專案該有的革命性影響。學術事業受挫更加強我的企圖心,而未能利用當代神經生物學創造科學的心理學,也阻擋不了我的企圖心。多數人這時早已打退堂鼓,但我沒有!
年近四十時,我還靠看更多病患付房租及其他帳單。一方面是透過與佛萊斯的友情,但主要是諸事渺茫,我變得更加相信我的病患,多數為單身中年女性,她們是因為性壓抑而身心不健全。同時,這些女性與抱以同情的醫師如我與布魯爾(Joseph Breue)傾吐後,心情顯然舒緩多了。布魯爾也是我的醫師,他與我分享他的個案,儘管最後他並未追隨我的理論到底
。
我生命中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一八八五年前往巴黎與偉大的神經學家夏爾科(Jean Martin Charcot)共事。夏爾科診所的病患全為巴黎單身中年婦女。他學會利用她們展示神經學上不可能的症狀,並透過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控制這些症狀。據夏爾科說,這些個案的背後原因都與性有關。他說的「全因生殖器而起」(Toujours la chose genitale)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將它與佛萊斯的性理論綜合,幫我解釋了與布魯爾一起觀察到的現象。
十九世紀受到的創傷癒合,我逐步邁向使我成名的心智模型,也就是潛意識心理像一個強大而極為衝動的大悶鍋,多半屬於性的衝動,不斷威脅要侵入意識。為了保護意識,這些衝動得被推回(透過壓抑)、洩放(取代)或轉到身體(身體化,somatized,譯注:經由身體疾病來表示心理問題)。這種防衛機制的重要概念,成了心理分析的基礎,是我所建構複雜的人類心理理論,獨領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風騷。
我的夢理論與神經官能症(neuroses)通論都循此路線建構。簡言之,白天,我們能力阻潛意識這魔鬼入侵意識,但這些防衛機制偶爾鬆綁,表現在說溜嘴、寫錯字及神經變形上。到了晚上,我們防衛潛意識的衝動因為睡眠而放鬆。為了不讓意識遭到大舉入侵,我們的心智訴諸轉化、凝縮、象徵化,使我們的夢千奇百怪。這能用來保護睡眠。
我愈去想下步該做什麼,愈覺得夢是展開建構我心理分析理論的最佳起點。我告訴自己,如果因為沒有腦的知識,我無法建構一個由下而上的理論,那麼從上而下應該可行吧。我能從夢的特性,尤其是被一些人視為夢之怪異(dream bizarreness)的無稽之事,推論出一個動態心理學。我會設法顯示,怪夢就像神經症狀,隱藏著可以解釋的意義。從這些考慮得出的重要概念,那就是幼稚甚或更原始的「願望」,必須主動壓抑,從意識中排除,避免造成精神災難。
就像一些脫線行為,顯示火山般的潛意識衝動,試圖衝出表面,在白天做出不想要的表達;而夢對我而言,就像晚上睡眠時類似的爆發性壓力的證據。夢的祕密,在一八九六年的五旬節主日(Pentecostal Sunday)所顯示給我的,就是夢中顯然無稽之事,其實是心智力圖隱藏湧出之潛意識願望的功能,人的意識因睡眠而放鬆。
回顧我這一生此次重大的轉捩點,以及西方思潮劃時代的一刻,兩個互惠的觀點讓我大感意外。一是,當我自以為是在從事科學發現時,我認真著眼的既非睡眠亦非夢的經驗;另一是,透過強烈表達我的理論,我能說服許多人信其為真。我能寫,能演說;甚至很有人格魅力,如果我真要這麼說自己。
然而我把遭棄的《科學心理學的專案》的許多包袱帶進夢的理論,儘管我盡了最大努力想揚棄它。會發生這一切就是因為我非常堅持與深信自己是對的,在一九○○年我發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後,已不可能再回頭看了。
我從未想到要去觀察或蒐集睡眠與夢的資料。雖然在我這本有關夢的書內討論的片斷,多數是我自己的夢,我從未記錄的夢,也從未請我的同儕或病患做此紀錄。從五旬節得到的啟示(pentecostal revelation),我就知道,夢為什麼奇怪。心智需要偽裝與審查煽動的夢想,以免破壞性的潛意識侵入意識。因此,夢是睡眠的守護神。我一旦手握這把鑰匙,就能打開夢的大門。有什麼必要去蒐集其他人的夢的報告,他們記夢的本事會比我好?
就以我經常提到的伊瑪注射之夢為例:一個大廳──有許多客人,我們準備會診的伊瑪就在裡面。我立刻把她拉到一旁,好像要回她的信,並斥責她不聽我「勸」。我告訴她:「如果妳還疼痛,只能怪妳自己了。」她回答說:「如果你知道我喉嚨、胃和肚子有多痛就好了──我快窒息了。」我聽了大驚失色,看著她。她臉色蒼白帶點浮腫。我心想,我可能忘了檢查她器官上的毛病。我拉她到窗邊,看她喉嚨深處;她有點想抗拒,像個裝了假牙的婦女。我心想她真的沒必要如此。接著她適度張開嘴,在右方我看到一個大白斑點,在另一處我看到一片白灰疙瘩長在十分彎曲的組織上,這些組織顯然長在鼻樑骨上。我立即找來M醫師,他再做同樣的檢查,確定沒錯 ……M醫師看來和平常不太一樣,他臉色蒼白,走路有點跛,下巴刮得很乾淨 ……朋友奧圖(Otto)站在她身旁,另一位朋友李帕德(Leopold)透過她的緊身上衣叩診說:「她的左下方有塊陰暗的地方。」他也指出她左肩有塊皮膚也被感染(我與他同時注意到,雖然她穿著衣服)。M說:「無疑這是感染,但不要緊,接著會拉肚子,毒素會減少。」我們立刻判斷感染源為何。她感覺不適後不久,奧圖就替她打了一針丙基配劑,丙基……丙酸 ……trimethylamin(此處方的粗體字出現在我眼前)……這種藥劑不可輕易注射……或許針筒沒清洗乾淨。
我自然知道這個夢的記憶源頭。此夢反映了我與佛萊斯,以及他帶給伊瑪痛苦的關係;伊瑪也是我的病患。但因為擔心醫療疏失,我完全看不出伊瑪與她耳鼻喉狀況困擾著我。我確實看出,夢的用意就是讓我針對問題改正。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我必須承認,關於我的焦慮或想醫好伊瑪鼻子的心,都不是潛意識。我夢的審查功能還沒好到能偽裝業務中見不得人的地方,清醒時,我學著忽略或將之合理化。老實說,關於我對伊瑪之夢的解析,實際上稱不上有什麼深入或真實的心理分析。當時為什麼我就看不出來呢?
可能是我成了信徒,改信自己的觀點。我就是俗世宗教那位不用心的創造者?只要我能維持自己是名科學家,只要我的理論是科學的,我的「發現」便受世人推崇。當我說,我知道有一天我所有的觀點都會被物理與化學取代,我的真意其實是「被確認」而不是「被取代」。當然,我從沒想到我可能大錯特錯。
我可以替自己辯護,說這並非假科學,只要推說研究睡眠的科學在一九○○年還不存在。但一九二八年,研究精神病的同事柏格(Hans Berger)已描述了腦電波(EEG),我根本沒注意到這項發明。當時我已七十二歲,正在把心理分析推進哲學、心理學、社會科學領域。諷刺的是,我正好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攻擊宗教的書。前一年對宗教的攻擊,未預示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新聞,如果慢一年發表也不會如此。我確信宗教幻想的前景不佳,卻從沒想過自己理念的主要成分就是宗教。
一九三三年我發表〈談夢〉(On Dreams),努力嘗試修改我的夢的理論。但我未提柏格的發明。等一九三六年魯米斯與哈維(Loomis and Harvey)展示睡眠的腦電圖出現循環的變化,我已八十歲了。當時我有更叫人分心的事要爭,捱過納粹迫害與下頜癌;看不出將至的變局,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反而持續全力拒絕以神經學做我的理論依據。既然在我的專案中已放棄了頭腦為基礎,我不想讓神經學主導心理分析。結果是我的門徒未注意到神經學緩慢但持續的成長,還逐步提供一八九五年我的專案所需的材料。到了一九五○年發生我未料到、坦白說也讓我不開心的革命。我死於一九三九年,在我處心積慮建構的不牢靠的房子開始土崩瓦解前許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