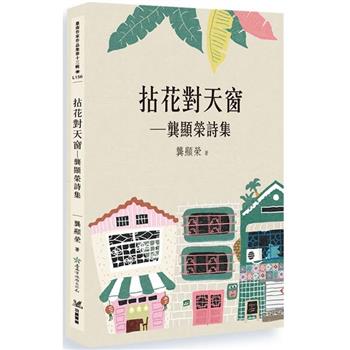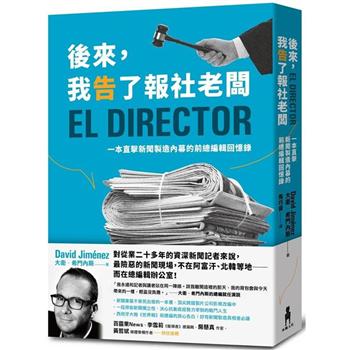死亡
二○○四年三月二日是個美麗的一天,太陽明亮地高掛在晴朗蔚藍的天際,空氣清新又涼爽。我懷著幾乎是篤定情況會有所轉變的心情,出門去做清潔窗戶的工作。瑪姬早上也要到一家名叫「瑪洛繩索」的公司去做新的臨時工作。儘管我仍為她提心吊膽,想到她這一天不曉得會過得如何,胃裡依然有種熟悉的蝴蝶飛舞的感覺,但宜人的天氣倒是令我神清氣爽。
在我們各自上工前,我祝瑪姬好運,並在她的臉頰上印下一吻。「拜拜,親愛的。」我說:「我愛妳。」
「我也愛你。」她說,一如往常。
午餐時,我的手機響了。瑪姬打來的。
「嗨,甜心。」我說:「工作情況還好嗎?」
「喔,那不是我喜歡的(工作類型)。」她回答:「但我需要這份薪水。我現在要去吃午餐,然後回去上班。」
瑪姬的話裡沒有任何怪異之處,但她的音調卻不太對勁,聽起來有一點口齒不清。我可以分辨得出有什麼不對勁了。又來了,我想,準備好要經歷另一段困難的時期。同時,我也納悶有什麼是我可以先發制人的。
「甜心,」我說,「妳要不要我過去找妳?妳聽起來不太好。」
瑪姬堅持她沒有問題,但我也沒有立刻退讓。我說我可以過去和她一起吃午餐,她則語氣堅定地說,一切都好好的沒事。
「我沒事,」她一再說道,「我馬上要回去工作了。你只要今晚回家的時候,把幾顆馬鈴薯連皮一起放進烤箱裡就好。我回家後會準備辣椒。」
這番話讓我安下心來。畢竟她計畫晚餐要吃什麼的方式是如此隨意且正常,或許真的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吧。或許是我太焦慮了。
「好吧,親愛的。」我回答:「我們晚點見。愛妳喔。」
「我愛你,寶貝。」她回答,然後掛斷電話。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瑪姬此生最後對我說的隻字片語。
掛上電話,我再度焦慮不安。我和一個朋友談到我的心情。「別擔心。」她說:「瑪姬不會有事的。」於是我又回去工作。
稍後,我在回家的途中停下來,買了一片CD。聖誕節時,我的女兒放了一張「伊凡賽斯」(Evanescence)搖滾樂團的專輯,瑪姬聽了很喜歡。我想,她回到家時看到這張CD應該會很驚喜,所以毫不考慮的買了。我總是試著做一些會討她歡心的事,希望能藉此減少她對酒精的需求。
回到家後,我先把馬鈴薯放進烤箱,再把CD放進音響裡。一切準備就緒,除了等瑪姬回家之外,已無事可做。我坐下來,想到她走進家門的那一刻,會因為我的小禮物而雙眼發亮,自己也不由得高興起來。
然而,等了一個小時,她還是不見人影。帶皮馬鈴薯已經準備好要料理了,我把烤箱的溫度降低,然後撥打她的手機。沒有人接。喔,天啊!我又湧起那股熟悉的恐怖感。她一定又在外面遊蕩了。舊有的擔憂再度充滿著我。她在哪間酒吧?又要去飯店了嗎?我晚一點會不會接到她的電話?
又過了一個小時,馬鈴薯已經熟透了,我關掉烤箱。真是浪費時間,再打她的手機,還是無人應答。我胃裡的蝴蝶群舞亂飛,開始有種噁心想吐的感覺。瑪姬顯然在某個地方喝酒,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不斷打電話給她,以免她喝到不醒人事。我希望電話鈴聲可以喚醒她,她卻一直沒有接電話。
這一整天的回憶在我的腦中打轉,我開始責怪自己午餐時沒有回家看她。我為什麼不照直覺行動呢?我想。我是對的,一定有什麼事情不對勁。
時間越來越晚。到了十點,我開始在想我到底還能做什麼。要出去找她嗎?我納悶。但我還來不及付諸行動,門鈴就響了。
有那麼一瞬間,我以為是瑪姬回來了。但站在門外的不是她,而是警察。
「我們今天稍早在巡邏的時候看到你們的車。」他們告訴我:「但車子從那時起到現在一直沒有移動過。」
唔,我想,如果瑪姬跑去喝酒,當然不會開車囉。
「所以,車子在哪裡?」我問他們。
「比奇角。」
「不會吧!」我不敢置信地大叫一聲。
「對,它是在那上面沒錯。」其中一位警察說:「但你先別慌,我們會找到她的。」
比奇角是個出了名的自殺地點,不過起初我並沒有意識到警察認為瑪姬可能已經死了。我不確定是為什麼,但我就是沒有那麼想。還有,瑪姬極端的行徑儘管可怕,我總當那是求助的吶喊。她每次都在一息尚存時被人發現。我不認為她真心想死。
接著,警察跟我說,他們已經派一輛直昇機去找她。這時我才開始擔心。我知道那些直昇機飛一小時要兩千五百英鎊,除非情況真的很令人擔心,否則直昇機是不會輕易出動的。他們有一個熱感應裝備,可以找到還活著或剛死不久的人。
警察囑咐我待在家中,以免瑪姬回來或是打家裡電話回家。我把她車子的備份鑰匙交給警察,他們隨即離開。當我看著他們進入巡邏車裡,朝著比奇角的方向開去,我的心充滿了恐懼。這是我從未面臨過的情況。瑪姬不在酒吧,也不在飯店。她沒有在街頭漫遊,她在比奇角,還丟下了她的車。
我驚嚇到不能自己,心裡滿滿都是恐慌,不知該如何是好。我在屋內走過來走過去,開始像風吹著的樹葉般劇烈抖動。我從來沒有抖成這個樣子,而且接連兩個小時抖個不停。然後,大約在十二點三十分時,我往窗外望去。瑪姬的車正沿路開過來。
太好了!我想。他們找到她,帶她回來了,感謝老天!
我衝向門口,卻沒見著瑪姬。我只看到兩位警察從車道上走來。當他們越走越近時,我發現他們手裡拿著瑪姬的手提包和絲巾。我的心跳到了嘴裡,等著他們要告訴我什麼消息。
「車子撞傷了,但還可以開。」其中一位開口說道:「瑪姬一定撞到了什麼。我們恐怕她還是行蹤不明。熱感應直昇機在比奇角上沒有找到人。」
這給了我一線希望,沒在比奇角上找到她是個好消息。典型的瑪姬,我稍稍鬆了一口氣地想著。她又累垮了,大概待在城裡的哪家飯店吧。但是,我又想,她為什麼沒拿手提包?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或許她醉得太厲害,所以思慮不周。
警察告訴我,他們早上會再出動尋人,但目前是無能為力了。他們叫我多少睡一下。什麼屁話啊,我暗忖著。
我坐在沙發的邊緣,整夜未曾闔眼,左思右想瑪姬可能會有的狀況。當第一道曙光出現的時候,我跳上我的車,出發去比奇角。
到了目的地,我在任何瑪姬可能昏睡過去的地方,好比樹叢下和樹林的後面尋找。起初,我沒有走到峭壁邊,但在看過所有的地方之後,我開始到峭壁邊緣仔細查看。我找了幾乎有三英哩那麼長的距離。
什麼都沒有找到。
沒有地方可去了,我決定到小鎮上的飯店找找看。我打電話給我女兒,請她過來陪我一起找。我們首先去了海卓飯店,詢問櫃檯人員有沒有一位藍恩太太住在他們那裡。
「有,有一位。」他們回答。
我的身子一下子全放鬆開來。我們找到她了!我的寶貝瑪姬安全無虞!
「藍恩太太今年貴庚?」櫃檯人員問道。
「五十四,」我回答,「但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住在我們這裡的藍恩太太八十八歲了。」櫃檯人員回答。
我一擊倒地。沒辦法,只能繼續到別家飯店去找。我們又找了三個小時,但卻徒勞無功。我已經連著三十六個小時沒有睡覺,整個人疲憊至極,逼不得已只能返家躺在沙發上。
接著,我被門鈴聲驚醒。
就在這個時候,我知道我太太死了。
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個消息,怎麼樣都不能。
加速沉淪與一線希望
瑪姬死後,我原本滴酒不沾。既然知道酒是殺害她的兇手,我自是不想在生活中再多看它們一眼。但隨著時間過去,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後,我開始會在家裡喝一點威士忌。接下來,我越喝越多,不知不覺間,一週七天,我天天晚上都喝得爛醉如泥。由於酒精可以短暫提振精神,憂鬱的人很容易酗酒,可是這種情況到了最後,卻很諷刺地只會讓你更加抑鬱。這在瑪姬身上已經出現過,現在,我想,又在我的身上重演。
我急速向下沉淪。然而,沒有任何事物阻擋得了我每天早起到比奇角去。這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例行公事。我每週七天、天天都在清晨五點半時上峭壁,沒有一天沒去。每天,我都把車停在停車場,走上比奇角的最高點,然後用我的雙筒望遠鏡觀望整排峭壁,看看有沒有人站在危險的邊緣。如果附近沒有人,我會往峭壁之下張望,想知道有沒有人已經跳了下去。約莫就在此時,一個名叫比奇角院牧團隊的基督教組織,也已經開始從下午六點上峭壁巡邏直到半夜。然而,在院牧團隊結束巡邏之後到我開始巡邏之前,中間相隔了好幾小時,我總是擔心有人會在這段時間尋短,所以峭壁之下也一定要檢視有沒有屍體。在我開始巡邏的初期,若有人跳崖,我會很引以為咎,覺得自己失敗了。
在一個溫暖的六月天早上,我一如往常上比奇角巡邏,巡到大約七點,我注意到一個男人坐在瀕臨峭壁的草地上。因為風化的關係,峭壁邊緣一點一點的掉落海裡,所以有部分看來宛如小小的階梯,沒有懼高症的人可以當成板凳坐下,那個男人就坐在其中一層階梯上看報。當然,那是個風和日麗的早晨,但在我看來,一個人會大清早上峭壁看報著實透著點古怪。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不過,我暫且假定他沒有問題,打算暗中觀察一番,不要直接衝上去打擾他。
我從他的身後走過。確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我繼續往前走了幾分鐘,然後轉身,開始往板凳那裡走回去。當我再度與他擦身而過,我注意到他根本沒在看報。他的視線越過報紙往外看。更誇張的是,我發現他有五分鐘都沒有翻頁。所以,他不是一個閱讀速度很慢的人,就是有什麼不對勁。我在同一塊岩石上坐下,開口跟他說,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然後再以漫不經心的口吻問他好不好。
「很好啊,為什麼會不好?」他回答,完全不為所動。或許是我看錯了。或許我只是打擾到這個男人的平靜和安寧,但既然都打擾到了,何不繼續下去呢?我寧可讓自己是個討厭鬼,也不要錯失一個可能會往下跳的人。
我告訴他我的巡邏,還有瑪姬。我總是會提到瑪姬,因為十次有九次,她的故事會抓住對方的注意力,使他們專心聽我說話,不論他們是否正為了某個問題苦惱。你可以教別人各式各樣的事情,但你無法教他們經驗。我的經驗賦予我某種權威,無論我的故事會不會引起別人的尊重、同情或只是充滿疑問,他們似乎都想聽下去,而這對我來說已經夠好的了。
這個男人似乎被我的話所觸動,對我的經歷表達了遺憾之意,這份關懷引得我思考,我這次大概真的找錯對象了。但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他。
「剛剛從你身邊經過時,我注意到你沒有在翻報紙。請原諒我打擾你,但是……」
他的眼中開始出現淚水。
「你為了什麼事情在苦惱,是嗎?」我又說。
他點頭。
「正如我所料。」我說:「你想談談嗎?畢竟,問題只要拿出來談,就等於解決了一半。相信我,我了解你現在的感受。你覺得自己像在一條隧道中,盡頭沒有一點光亮,是不是?我老婆死後,我也是這種感受。」
「沒錯。」他說,稍微正眼瞧了瞧我。
「我不會要求你從這裡走開。」我向他保證:「我只是提供你一個訴苦的地方。我們為什麼不談談呢?你永遠也不知道,談了之後,你會不會對自己打算做的事有不同的想法。」
聽我這麼說,男人開始談起他的苦惱。他說結縭四十年的妻子半年前過世了,他現在是和新任妻子來伊斯特本度假。他很快再婚,但新的婚姻關係中卻有一個大問題:妻子不准他在家裡放前任老婆的照片。她不允許他談論亡妻,也不讓他分享亡妻的任何事物。當他敘述完自己的故事時,淚水已然潰堤。我環抱著他的肩膀,叫他盡情哭泣。
「你還沒有時間省思和哀傷,不是嗎?」我問。
「沒有,一點都沒有。」他很愛自己的新任妻子,但這並不代表失去共度四十年光陰的女人,已經不再令他感到悲傷。「真該死!」他說:「還好我現在的老婆沒上來看到這個情況。」
這個男人顯然壓抑了太多情感。
「你才失去至親,卻無處宣洩悲慟。你和現在的太太談過你的感受嗎?」
「我很怕和她談,我怕一開口就會吵架。」他說:「我不想讓她討厭我。」
「我可以理解。」我說:「但現在這個狀況當然不是很理想。誰知道呢,如果你對你太太敞開心,解釋這些事情,向她保證你愛她,只是需要時間哀悼,她可能會理解,甚至還能讓你們變得更親近……」
他緩緩地點個頭。好,我想,他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事情了。該是讓他離開峭壁的時候。
「來吧。」我面帶著微笑說:「放下報紙,我們去酒吧喝杯咖啡吧。」
無需再多的好言相勸,他離開峭壁,和我一同到比奇角酒吧坐了一會兒,直到他上了車,我們才互道再見。
我們握了握手,但有那麼一瞬間,他用力到我以為他要甩開我的手!他面露微笑,雙眼中透著一股決心。我看得出來,他終於決定要面對這個令他苦惱到無以復加的情況。
「祝你好運。」我說。
「謝謝你為我做的事。」他眉開眼笑地說:「要繼續加油喔!」
他放開我的手,駕車離去。
天哪!他一走我就想,我那些忠告是打哪裡來的?成功救人當然再度令我振奮不已,但我其實不是很清楚自己怎麼有法子打動他。我一向是個樂於助人的人,總是很懂得關懷別人,也因為我是個很好的聽眾,家庭成員遇到困難時常常會來找我。但是,我的建議從來無法這麼……源源不絕地冒出來。那些話從我的舌尖滾落,我一邊說,一邊有種自己也搞不清楚它們是從哪裡來的感受。我沒有時間省思和考慮,沒有時間先斟酌過再開口,然而能夠阻止一個人輕生的話語,卻自發地從我的嘴裡流洩而出。這實在太美好了,好到不像是真的。我想,這或許是因為當時的壓力所致。或許人在面對生死交關的極端情況時,腦中的什麼會突然動起來,正確的話語便自然湧現。
但我還冒出了另一個念頭。或許那些不全然是我的話;或許有人在暗中協助。那天是我第一次想到,在這樣的時刻中,有人在指引著我。那個人,就是瑪姬。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懸崖邊的守護者:在失去妻子的同一地點,救回29條人命的真實故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懸崖邊的守護者:在失去妻子的同一地點,救回29條人命的真實故事
一個去過地獄又回來的男人,
三年前,他摯愛的妻子從陡峭的懸崖上一躍而下,
三年後,他在同一地點救了29條人命。
他的救人事蹟,得到英國皇家人道協會獎章
他的感人故事,被英國太陽報、BBC等各大媒體大幅報導
知名作家 王浩威、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李明濱、知名主播 李晶玉、知名電台主持人 余秀芷、終身義工 孫越、知名作家 彭樹君、《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導演 楊力州、三立新聞總編輯 陳雅琳、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 賴德仁、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盧蘇偉、兩岸企業內訓名講師 謝文憲 感動推薦 (以上排列按照姓氏筆畫)
絕望,是希望的另一個開端
甜心,當妳從懸崖上一躍而下,我以為世界從此崩解……
但我不想和妳說再見,因為妳,讓我重生,也讓我成為懸崖邊的守護者。
53歲那年,我摯愛的妻子瑪姬死了。
每天沉溺在Pub、酒精、糜爛生活中的我,怎麼樣都無法減輕痛苦。賴以維生的洗窗戶工作、被拍賣掉的房子,統統變得可有可無,我的人生,彷彿跟著瑪姬一起跳下。
瑪姬告別式的前一天,我走上懸崖,想遇見瑪姬,卻遇見一位想輕生的婦人……就這樣,我的生命從此改變。
一本找回人生希望的書,一段從地獄重生的真實故事。
親愛的瑪姬,我好愛好愛妳,讓妳恢復健康是我唯一的希望。
當妳放棄了我,我也想放棄全世界。
我深愛的寶貝瑪姬,從峭壁上一躍而下,躺在下面,死了,不過短短幾個片刻,我的世界卻徹底崩塌。人生儼然從一場美夢變成惡夢。瑪姬迷失了,我也是。
我的經驗絕非獨一無二,也稱不上是例外,但對我來說,在停屍間指認我的太太,是我不得不去做且最困難的事情之一。
當悲傷在懸崖邊徘迴,請讓它掉入萬丈深淵,雖然,我知道未來永遠無法確定,但此刻,我覺得好幸福,已別無所求。
瑪姬跳下後,我親手做了一個小小的木頭十字架,帶上比奇角,一點一點的把十字架釘在瑪姬跳下的地方。忽然,尋死的念頭盤踞著我,但我明白的知道我還不想死。
我轉身凝望那個十字架,開始對瑪姬說話。「唔,甜心,我不會和妳說再見,因為現在我每天都會來這裡。我會保護這個地方的安全,妳不要擔心。」
作者簡介:
凱斯‧藍恩
2004年,凱斯‧藍恩的妻子瑪姬‧藍恩於英國著名的自殺勝地,也是陡峭的懸崖——比奇角跳崖自殺。凱斯‧藍恩在試著接受妻子悲劇性的死亡時,回到她跳崖的地點尋求慰藉,不意卻遇上另一位準備輕生的女人,並成功說服她放下這個念頭。從那一刻起,凱斯即懷著拯救更多人的希望,把巡守這個區域視為他的使命。為了幫助那些自覺已無路可退的人,凱斯奉獻出將近4年的人生歲月。他專心致志,立定決心,不論天晴還是天雨,不論面臨什麼情況,他都會在比奇角上守望相助。沒有什麼事能停止這位英雄的腳步,他曾經成功阻止了29個人跳下懸崖。
譯者簡介:
澳洲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畢業,曾任路透新聞編譯與伊甸基金會海外公關,現為專職譯者。譯作繁多,包括《中國怎麼想》、《自由寫手的故事》、《不專業偵探社》、《蘇格拉底的咖啡館》、《療傷的對話》、《劈腿是天性?愛與性的25個迷思》、《黑暗姊妹》、《創業致勝的第一本書》、《是你製造了天氣:全球暖化危機》、《天使遺留的筆記》(春光出版)等。
章節試閱
死亡 二○○四年三月二日是個美麗的一天,太陽明亮地高掛在晴朗蔚藍的天際,空氣清新又涼爽。我懷著幾乎是篤定情況會有所轉變的心情,出門去做清潔窗戶的工作。瑪姬早上也要到一家名叫「瑪洛繩索」的公司去做新的臨時工作。儘管我仍為她提心吊膽,想到她這一天不曉得會過得如何,胃裡依然有種熟悉的蝴蝶飛舞的感覺,但宜人的天氣倒是令我神清氣爽。 在我們各自上工前,我祝瑪姬好運,並在她的臉頰上印下一吻。「拜拜,親愛的。」我說:「我愛妳。」 「我也愛你。」她說,一如往常。 午餐時,我的手機響了。瑪姬打來的。 「嗨,甜心。」我說...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凱斯‧藍恩 譯者: 林雨蒨
- 出版社: 春光 出版日期:2011-11-04 ISBN/ISSN:97898665727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靈雞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