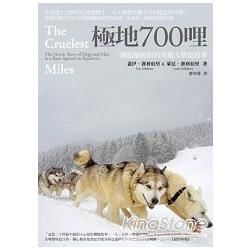歷史上動員最多雪橇犬的一次極地救援!
在長達700哩的白色險路上,由人類與雪橇犬共同締造的奇蹟!
這個故事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都更為悲傷,但也給人積極面對的勇氣。「這是二十世紀中最扣人心弦的驚險故事。一九二五年,舉國的情緒隨著這故事起伏超過一週,全球都屏息以待,關心救命血清是否能及時送達阿拉斯加那冰封的諾姆鎮。」──《紐約時報》
這場救援行動,至今仍持續感動全球──*紐約中央公園以巴爾托──最後一支接力狗隊領袖犬的形象做成雕像,紀念這場救援行動,上面寫著:這座雕像要獻給奔至諾姆的的雪橇犬們,牠們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耐力、忠誠和智慧。
*史蒂芬.史匹柏已監製改編成動畫《雪地靈犬》,至今仍讓全球無數師長與孩童感動。
*本書已售出電影版權!將由電影《姐姐的守護者》、《納尼亞傳奇》團隊傾力製作,奧斯卡最佳外語導演蓋文胡德(Gavin Hood)執導。
【故事簡介】
真實還原一九二五年,那關鍵六天的救援現場──靠近北極圈的阿拉斯加諾姆,是個與世隔絕的小鎮,每年冬季,大地冰封,諾姆就成了一座冰雪打造的監獄,只能靠狗拉雪橇的方式與外界連絡,連距離最近的城鎮,來回都必須花上25天。
一九二五年冬天,當最後一班對外連絡的運輸船駛離,諾姆爆發足以滅絕整個小鎮的白喉傳染病,但諾姆並沒有足夠醫治的血清,為了搶救諾姆,20名狗雪橇駕駛,和他們忠心的哈士奇,在零下四十度的低溫下不分晝夜接力奔跑。暴風雪影響了他們的能見度,冰雪互相擠壓的冰脊不斷產生變化,更增加了危險的程度,甚至有駕駛冒著破冰的危險穿越結冰的海灣,只為了早一刻送達。最後,他們在6天內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個多禮拜的路程,將血清成功送達,他們的勇氣、智慧和毅力,克服了地表上最嚴酷的七百哩路。
是他們的勇氣,拯救了一整個小鎮──小鎮上唯一的醫生柯提斯.威奇+英勇的領袖犬東鄉&巴爾托+傳奇的趕狗人比爾.夏儂、萊昂哈德.塞帕拉、甘納爾.卡森+守護居民的梅納德鎮長……這本書記錄了那一場人與狗超越極限挑戰的真實見證!
在一九二五年的那六天,全美國人的心情都跟著諾姆的這些狗隊跌盪,心繫著狗隊是否能將血清送到諾姆,拯救諾姆人的性命。二月二日禮拜一清晨五點半左右,血清送達諾姆。見證這場精彩好戲的人說,他們看見救援隊的最後一棒──甘納爾.卡森搖搖晃晃地走下雪橇,踉蹌走到領袖犬巴爾托跟前,然後整個身軀癱軟,口裡喃喃說著:「你這條該死的好狗。」
這些狗兒深深感動了美國人,直至今日,每年還有數千人湧入紐約中央公園為了瞻仰其中一隻領袖犬的雕像,他們的勇氣與毅力,將永留人心。
作者簡介:
蓋伊‧賽利伯里(Gay Salisbury)
為基礎讀物出版社的前任副社長。她目前在阿拉斯加費班克和紐約間奔波往返。
萊尼‧賽利伯里(Laney Salisbury)
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曾於非洲、中東和紐約進行報導。兩位作者為堂親。《極地700哩》是他們的第一本書。
譯者簡介:
廖素珊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雙子城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有《米開朗基羅之山》、《霧中回憶》等書。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人類對抗自然的經典故事,在傑克‧倫敦的〈白色寂靜〉那令人心碎的冰封世界中上演。」
──莎拉‧威勒,《紐約時報書評》
「文筆優美,讀來讓人不禁對堅毅的領狗人和他們的狗兒肅然起敬。」
──《出版人週刊》
「賽利伯里寫了一本有關毅力和勇氣的精彩故事。」
──《書單》
「描述狗拉雪橇的細節扣人心弦,人與野獸的關係令人動容,而優秀領袖犬的重要性讓這本書有著傑克‧倫敦的韻味。」
──大衛‧史崔斯,《西雅圖週刊》
「多虧有人類的最佳伙伴,才能成就這個扣人心弦的生存故事。」
──《西雅圖時報》
「令人不忍釋手……如果你在找這類精彩故事,讀這本就對啦。」
──巴德‧波康,《AKC報》
「考據精細,書寫精密,不失為一本絕妙的冒險故事。」
──愛莉絲‧金,《娛樂週刊》
「扣人心弦的冒險故事。」
──莎莉‧愛考夫,《今日新聞報》
「賽利伯里不僅寫了一個接力競跑的故事,他還描述了我們的阿拉斯加歷史以及乍抵當地的堅毅人民,不管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他們使我們的歷史如此豐富多樣。」
──薇瑪‧華利斯,《兩個老女人》之作者
「引人入勝的史詩。」
──《克科斯書評》
「緊湊動人的故事。」
──金‧卡薩達,《圖書館學刊》
「精彩刺激。」
──凱薩琳‧奈爾森,《波士頓地球報》
「考據精確,資料翔實,《極地700哩》同時是史書和動人的冒險故事。」
──亞倫‧坎納,《Dogfancy雜誌》
「《極地700哩》是本精湛好書。」
──羅伯特‧S‧霍普金三世,《貝勒大學醫學中心院刊》
「閱讀《極地700哩》是個激勵人心的經驗──這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目前的舒適生活,以及和我們分享這類生活的狗兒。」
──《Bark雜誌》
「這是個激勵人心的故事,資料搜尋齊全,描述手法高明。」
──賽巴斯頓‧楊格,《完美暴風》作者
媒體推薦:「人類對抗自然的經典故事,在傑克‧倫敦的〈白色寂靜〉那令人心碎的冰封世界中上演。」
──莎拉‧威勒,《紐約時報書評》
「文筆優美,讀來讓人不禁對堅毅的領狗人和他們的狗兒肅然起敬。」
──《出版人週刊》
「賽利伯里寫了一本有關毅力和勇氣的精彩故事。」
──《書單》
「描述狗拉雪橇的細節扣人心弦,人與野獸的關係令人動容,而優秀領袖犬的重要性讓這本書有著傑克‧倫敦的韻味。」
──大衛‧史崔斯,《西雅圖週刊》
「多虧有人類的最佳伙伴,才能成就這個扣人心弦的生存故事。」
──《西雅圖時報》
「令人不...
章節試閱
序曲 冰封世界
「我們是冰雪監獄的囚犯。最後一艘船已然駛離,這個小鎮變得遺世獨立,只有北方的暴風、黑暗和寒風相伴。」 ──《諾姆記事報》
在這綿延數百哩、偏遠孤絕的白令海沿岸,柯提斯.威奇是唯一的醫生。過去十八年來,他看著冬天陡然降臨,在遙遠的北方季節遞嬗總是迅速無比。人們說,這裡只有兩個季節:冬季和七月四日國慶日。在諾姆,冬季至少長達七個月,其他季節在短短幾個禮拜內來了又去,倏忽即逝。從七月到十月,白令海面冰雪消融,蒸汽船和縱桅帆船紛紛從西雅圖駛來這個小鎮。西雅圖是離此最近的主要港口,位於南方大約二千四百哩遠,約需十四天航程。十一月初,白令海將會冰封,直到翌年春天,這裡幾乎完全為黑暗包圍。按照慣例,維多利亞號是第一艘在春天抵達,最後一艘在秋天離開的客輪,它會卸下所有的貨物,然後遠離這個遺世獨立的小鎮。它的對外道路只剩下一條路線:一條從小鎮穿過阿拉斯加內陸區,直抵東南部幾座不凍港的狗拉雪橇路徑。
嚴峻的酷寒總是來得突然猛烈,暴風雪持續數日,帶來極度的孤絕,連最堅毅不撓的靈魂都無法承受。每年秋天,將近半數的鎮民會搭最後幾艘船離開,直到春天才回返。但是威奇留了下來。除了有年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奉召到美國本土服役,擔任短期軍醫以外,他每年冬天都會留下。從一九○七年抵達阿拉斯加起,威奇便深深愛上這片土地,而他的熱愛只有與日遞增。他曾經有次寫信給他住在康乃狄格州新哈芬家鄉的妹妹,他說,這片廣闊的土地提供他無盡伸展靈魂的空間。
威奇自從年輕時起,就覺得與周遭強烈的格格不入,他發現,就連最微小的社交禮數都讓他渾身不自在—他以在談話正熱絡時便匆匆離開晚宴而聞名—因此,阿拉斯加廣闊無垠的空間對他來說簡直是天賜之物。他寫道,他最後終於在此找到他的自我。他現年五十歲,原本一頭燦爛的金髮轉為蒼蒼白髮,濃密蓬亂。他期待小鎮每年的大量離境,讓他可以一個人自處。
不管在任何季節,諾姆都是個遙遠之地,只是美國地圖上位於邊境的小小一點。阿拉斯加的遼闊土地延伸將近六十萬平方哩,佔地之大,約為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面積加起來的總和。位於東南部的一端是首府朱諾,以及這地區的幾座全年不凍港。在西北的另一端則是諾姆。阿拉斯加比你能想像的還要不可思議。在西方,有活火山在崎嶇不平的北太平洋海岸吞吐騰騰煙霧;在東方,如羅德島大小般的冰河漂浮於峽灣內。在內陸區,即阿拉斯加的心臟地帶,北美洲最高峰,麥金利山在無邊的廣闊森林地中直聳入雲。一九○○年代初期,一位旅行家曾說,你得在阿拉斯加住上一輩子才能完全瞭解它,捕捉四個氣候帶的季節變化,或在結冰的海洋上聞到颼颼冷風的甜美氣息。也許,你在這輩子的盡頭終會抵達諾姆。
在一九二○年代早期,諾姆是北美洲最西北的城鎮。淘金熱時期,它曾是個繁榮小鎮,但好久以前便已失去它的熱鬧繁景。它位於北極圈以南兩個緯度處,西華德半島(Seward Peninsula)的南部海岸。西華德半島是片飽受狂風侵襲的土地,凸出白令海中兩百哩。諾姆比阿拉斯加任何主要城鎮都要靠近西伯利亞,再往北一點,如果在這個迷霧籠罩、暴風肆虐的世界中有幸碰到罕見的清澈晴日,你可以越過白令海峽看見五十五哩外的俄羅斯。國際換日線離半島的最西點只有數哩遠,你可以名符其實地看到明天。
在法朗街,礦商銀行的二樓是一間樸素的公寓,威奇和他的妻子露菈正坐在椅子上,觀看小鎮為即將來臨的冬季仔細準備。維多利亞號此時早已駛離,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最後一艘船,阿拉米達號正載著滿滿的冬季補給品進港。它沉重地端坐在離海岸一哩半遠的「近海錨地」,船只能駛到這麼近,不然就恐怕擱淺。諾姆既無碼頭也無安全港,裝貨的駁船和汽艇得在浪濤中穿梭前進,駛到大船旁,然後載著珍貴的物資駛回岸邊。
在與海洋平行的法朗街上,幾群愛斯基摩碼頭工人卸下物資,沿著海邊疊放,準備儲藏。舉目可見好幾箱的水果乾和冷凍火雞,成山的煤炭,還有滿裝著奶油和茶的板條箱。工人們從早到晚忙著卸貨,馬車和手推車隆隆駛下法朗街,直抵蜿蜒城鎮西邊的蛇河(Snake River)河岸,岸邊排著一列簡陋的木造倉庫,這裡儲藏的物資足以供應諾姆一千四百多位居民,以及住在西華德半島和周邊散落村莊和小採礦場的上萬名阿拉斯加人。
這個小鎮早已成為此地區的商業樞紐,許多阿拉斯加人在冬季旅行至此,添購各類補給品,從五金到窗簾、煤炭等。如果他們生病了,他們會住進梅納哥倫布醫院,接受威奇和四名護士的照顧。這家醫院有二十五張床位,被視為阿拉斯加西北部設備最佳的醫療機構。
最後一艘船駛離前,是法朗街最忙碌的時候。木板吱嘎作響,人行道因前往岸邊的人們雜遝的腳步而下陷。雞蛋浸泡在裝鹽水的大桶裡,冷凍火雞則堆放在家家戶戶後面的儲藏所中。如果哪家太太發現儲藏的空間不夠用,她可以走下法朗街,在最後一刻租下貿易站的小房間使用。
小孩子們手裡提著桶子從凍原回來,裡面裝滿這個季節最後的野漿果;這些會被做成果醬,或更棒的是,釀成甜酒,但自從禁酒令實施以來,這在技術上算是非法行徑。趁夏季在諾姆後方山丘探勘金脈的礦工穿著及膝的橡膠靴和毛織馬褲,在飯店或咖啡館裡等著搭船離開。那些決定留下來過冬的礦工則用他們的靴子向原住民交換溫暖又能防水的海豹皮靴。
美國聯邦法院執法官核發出政府批准離境的藍票,也就是所謂精神病患、貧窮人家和罪犯的離境簽證。在這裡嚴禁延誤時間,因為阿拉米達號是唯一的出路,而船長可不願冒著被冬季困住的風險而有所拖延。大家都要依天氣做事,沒有哪個政府當局比冰雪更有力。
諾姆的愛斯基摩居民居住在離小鎮西方一哩外處,一處位於蛇河河口的沙地,稱為「沙嘴」的地方,他們仍用數世紀以來流傳下來的方法過冬。那些在諾姆爭取不到勞動工作的愛斯基摩人提著漁網旅行到白令海岸一帶捕捉最後一批鮭魚或嘉魚。女人們用彎曲的鋼鐵刀,也就是「烏魯斯」(ulus),將魚剖開掛在架子上,在寒冽的海風中吹乾醃漬。如果他們在往北的定期遷徙中遇見海
豹,就會開槍射殺牠,將牠放進寬大的皮艇(「烏米阿克」〔umiaks〕)中,航駛過洶湧的海浪將牠帶回家。他們會將海豹皮剝下來作成皮靴,切下皮下脂肪食用,或製成油,當作食物或燃料。
今年冬天來得晚,儘管如此,法朗街、濱海區及商店仍舊加緊腳步。男人們將鬆散的木板釘在特定的位置好強化房屋,使它們能夠抵禦寒風吹襲。月泉自來水公司關掉兩條從安維爾溪接過來的粗糙水管,它們是鎮裡唯一的管道設備。牆壁上的破洞都補好以對抗暴風雪,而當地美國海岸防衛隊駐守站的救生員則準備移往海岸,拖走諾姆的小划艇、縱桅帆船和載貨駁船。
北極浮冰愈來愈漂近狹窄的白令海峽,白令海海岸邊的冰層開始成形。一位小鎮居民兼自然學家,法蘭克.杜佛瑞說,海洋變成「一大片泥濘汪洋,不斷緩慢笨重地翻滾上沙灘,劇烈碰撞,在所有它碰到的東西上塗上一層閃耀冰釉。」
在阿拉米達號的甲板上,船長知道他必須馬上撤往南方,不然就要冒著被愈來愈逼近的浮冰撞沉的危險。他認為封艙的時候到了,他下達清楚的指令:現在上船,不然就留下來過冬。
當汽笛聲在海岸邊迴盪時,木匠丟下槌頭,家庭主婦在街道上停下腳步,遊蕩在法朗街上的雪橇狗抬起頭,配合著阿拉米達號的笛聲,發出悲傷的吠叫。
最後一艘駁船急忙駛向大船,裝載貨物,返回岸邊。黑色的蒸汽煙霧裊裊從阿拉米達號的煙囪冒出,船錨收起,最後,船首緩緩轉南,諾姆所有的人深吸了一口大氣。
他們得靠自己了,至少到春天為止。
「看起來好像諾姆一半的人口都擠上了那艘老舊的蒸汽船,」杜佛瑞說,「我有一股被拋棄在浮冰上的感覺︙︙那是我在阿拉斯加感覺最沉鬱的一天。」
在數週內,凍原的河川和溪流就會結冰,閃閃夜星反射在晶瑩剔透的冰面上,就像「從深淵亮起的點點小火炬」。小鎮上,白霜覆蓋一切,白令海上由於海水化身為厚厚一層冰床而顯得風平浪靜。冰床一路伸展到遙遠的南方,即五百五十哩外的普列比羅夫群島。
在海岸邊,浮冰層層堆疊,形成高聳的冰丘;再往北一點,海冰的壓力更大,足以堆起巨大的冰丘,冰丘可以被壓力彈上海岸五十呎處毀掉路徑上所有的事物,因此而聞名。西北部的愛斯基摩人稱此為「伊烏」(ivu)—即「跳動的冰塊」。
幾週過後,太陽西沉的身影愈來愈低於地平線,冰雪連天的原野從純白轉化為燦爛金黃,最後變成幽微的紫光。白晝越來越短,日照僅剩四個小時,氣溫也急促下降。最後,深邃幽暗的沉靜降臨海岸,「萬籟俱寂」。
晚上,冰寒籠罩大地,諾姆所有的野生動物、狗兒和牠的主人都會蹲伏下來。因為極冷的空氣會放大所有聲音,就連最細微的動作都會劃破北極的寂靜。人們可以聽到海洋遠處浮冰彼此撞擊的雷鳴巨響,大地上的獵人可以聽到幾哩外,馴鹿踩在乾硬雪地上的答答腳步聲,或狗兒咬嚼骨頭的喀喀聲響。
然後,暴風雪降臨。一位居民曾如此描述,下雪時的窒息疾風像會「扼住你的呼吸,風灌滿你的鼻腔,然後又將空氣灌回你的喉嚨深處」。另一位居民言簡意賅地說,諾姆的暴風雪感覺起來「像是一隻緊扼住我喉嚨的無形之手」。人們得盡全力和諾姆冬季呼嘯的狂風對抗,用力挺起肩膀,身軀向前傾,鼓起全身的重量往前艱辛邁進。穿越小鎮的短短旅程往往變為一個小時的漫長掙扎,而且你很容易便會迷路,最後凍死在小鎮後方的凍原上。
這簡直就像重回冰河時期。
那年秋天,就在阿拉米達號駛離前的最後幾日,威奇醫生重新審視他的購物清單。上面包括有棉花球、乙醚、壓舌器、體溫計和需要替換的藥物。雖然大部分的醫療補給品都平安運達,但卻漏掉一樣東西。稍早時,也就是一九二四年的夏天,威奇發現他的抗白喉血清已經過期,於是他向位於朱諾的衛生事務委員局訂購一批新藥。白喉是一種致命的孩童疾病,但他在西華德半島行醫的十八年中,他從未碰過一件白喉的確定病例。他需要抗血清的機會幾乎可說是微乎其微,但誰知道呢?人算總不如天算。
但現在,海岸邊一片靜寂,威奇忖度,他的訂購不是被忽略,就是遺失。他只能等來年春天再想辦法。
大約在阿拉米達號離開小鎮的時候,一個有四個孩子的愛斯基摩家庭從荷里克羅斯,一個靠近育空河河口的村莊,輾轉抵達。最小的孩子才兩歲,生病了。當威奇檢查小孩時,他發現,他「異常疲憊和憔悴」。孩子不肯進食,威奇發現孩子的嘴巴有種嚴重的腐臭味。母親告訴他,孩子在荷里克羅斯曾接受扁桃腺炎的治療,但這個診斷無法解釋他的極度消瘦和羸弱。威奇小心翼翼地詢問父母,他們村莊內是否有其他小孩感染扁桃腺炎,或喉嚨劇痛?──這些症狀都與白喉類似。
那對父母向他保證沒有。
讓威奇鬆口氣的是,孩子的三個兄姐看起來都很健壯,因此他將他的疑慮置於一旁;白喉是傳染性極高的疾病,如果其他孩子感染到白喉,他們無庸置疑地會出現病徵。因此,他猜測這孩子得的是較不嚴重的傳染病。
「過去十八年間,我觀察到許多非常可疑的案例,但時間總是證明,它們不過是各種的喉嚨發炎罷了,」威奇在他的醫療記錄中如此寫道。
但隔天早上,那名小孩死了。
第二章 白喉爆發(摘錄)
「我們遺世獨立。現在,最後一艘船已駛離,簡單直說,『我們只能自求多福了』……」──《諾姆金塊報》
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更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傳來:據報,另外兩個住在沙嘴的原住民小孩也相繼死亡。威奇開始懷疑起最糟糕的情況。
一月二十日禮拜二下午,情況變得明朗,但卻不是好消息。威奇在梅納哥倫布醫院巡房時,他檢查了比利.貝奈特這個三歲的小男孩,比利在大約兩週前出現喉嚨痛、淋巴腺腫大、發燒和疲憊的徵兆,威奇因此讓他住院。比利住院數日後,出現令人憂心的新症狀:他的喉嚨和鼻腔黏膜上有一層厚厚的灰膜。
比利扁桃腺和口腔中的灰色潰瘍是一種古老、可怕的細菌疾病特徵,數世紀以來,它是奪去無數小孩生命的殺手。它常被稱之為「勒死者」不是沒有原因的。它的官方名稱是白喉。
白喉是種經由空氣傳染的細菌,它在喉嚨和鼻腔的潮濕黏膜上繁殖,毒素極強,能使病患疲憊、全身無力。兩到五天內,其他更致命的症狀會一一出現:包括輕微發燒,以及喉嚨深處和口腔中生成紅色潰瘍。細菌增生、釋出更多毒素時,潰瘍會變厚,面積擴大,形成一個由死細胞、血塊和死皮構成的偽膜,粗硬的得幾乎像皮革一樣。偽膜在口腔和喉嚨中不斷擴張,直到沒有空間,進而進犯氣管,緩緩使病患窒息而死。
這樣的死亡緩慢,痛苦,而且令人恐懼。大部分的病患是一歲到十歲間的小孩。一位醫生曾經描述說,他看見傳染爆發中受到感染的小孩,「在窒息逐漸逼近的陰影下,出現憂慮、掙扎,和可憐的表情」,令醫生感到深深感到不忍。
「最令人痛苦的畫面永遠銘刻在我腦海中的記憶之牆上。」十九世紀時,白喉肆虐的密西根村莊出現「各種可能出現的併發症和後遺症」後,一位醫生如此寫道。在世紀之交,發明抗白喉血清前,醫生無力回天,他們能做的只有照顧病患和不斷祈禱。
抗白喉血清取自免疫的馬的血清,它被證實能治癒白喉。問題是,威奇手上的血清數量有限,而且年代久遠。他擔心抗毒血清已因時間過久而變得不穩定,而不管任何醫生,一定避免傷害病患一定是黃金法則,因此,威奇決定不為比利注射抗毒素血清。他心裡仍微微希望比利不是感染白喉。「我不認為我該使用抗毒素,」數週後,威奇在醫療報告中寫道,「我不曉得它會造成什麼後果。」他和護士們也決定先不透露他們目前的診斷,以免小鎮陷入恐慌。
反之,威奇在他的藥局裡搜找,想找出一八九一年抗毒素發明前,醫生們用來治療白喉的老式藥物。他開始為比利進行一連串的治療:毒素會藉著血液循環攻擊主要器官,所以他先為比利注射強化心臟的刺激物,以抵禦可能的毒素侵襲。接著他將氯化鐵塗抹在比利的喉嚨上,這個收斂劑能有效抑制偽膜。這些都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加上病患自身的免疫系統,它們也許能提供病患與疾病放手一搏的機會。
這個治療方法似乎奏效,但只維持了短暫時間。威奇在比利喉嚨上塗抹氯化鐵數小時後,灰膜脫落,男孩的雙頰也恢復血色。他睡得較為安穩,身體似乎愈來愈強壯。威奇記得,男孩的狀況幾乎快要回歸正常。
然而,到了禮拜二下午四點左右,比利的情況迅速轉壞。醫生看著他的年幼病患,他不得不面對他最糟糕的恐懼。毫無疑問,這是白喉。男孩呈現的徵兆完全是白喉的末期症狀:雙眼凹陷,臉上絕望的表情,唇色深的得像小孩們從凍原那裡採來的野漿果。每當比利.貝奈特要想將空氣吸入肺部時,便會咳出鮮血。
下午六點,護士們將威奇叫回男孩床邊,他看見比利的臉因缺氧而發青,呼吸變得更為費力。他已經快要不行了,除了用抗毒素,威奇束手無策。但現在,考量到診斷過遲和疾病已發展到末期,即使注射新鮮抗白喉血清,也不見得能救回這孩子。威奇毫無選擇,只能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男孩死去。比利充滿恐懼的眸子回瞪著他。死亡接近時,因為孩子的氣管阻塞,他們聽到一聲微弱的高昂顫音,彷彿有人慢慢放掉氣球內的空氣一樣。
結束了。威奇安排好屍體的處理事宜,然後回家。那晚,他沒什麼能做的,但隔天一早,他得向小鎮父老提出完整報告。那個裝著四十磅屍體的棺材只有三呎多長。
從位於C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的醫院走回法朗街的家,路程雖然短暫,卻令人感到嚴寒與疲憊:夜已深沉,氣溫只有零下十四度,諾姆大部分的居民早已返家,坐在火爐旁,閱讀為漫漫冬季準備的書籍和舊報紙,或玩橋牌。護牆板嘎嘎作響;你可以聽到海洋中冰塊互相推擠的劈啪爆裂聲。街道上傳來馬兒的噠噠蹄聲,那是艾利.尼可利正在做他每晚的慣例行工作,傾倒戶外廁所的蜂蜜吊桶。
威奇並非第一位對白喉措不及防的醫生。白喉的最初病徵和其他咽喉疾病相當類似,尤其是扁桃腺炎;而且它的症狀多變,端看病情的嚴重性和孩童的健康狀況而定。在社群中爆發白喉,對任何小鎮醫生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即使他手上有足夠的抗毒血清也一樣;醫生們的第一反應一般都是否認。一八九六年,一位愛荷華州的醫生曾寫道:「有好幾個病例是我在試圖說服自己相信這是『扁桃腺炎』後,卻必須改變診斷,使用抗毒血清。」。對許多人而言,這個診斷過於可怕,他們無法接受。
一九二五年時期,大部分的醫生是仰賴視診來診斷白喉。如果他們無法確定,就進一步做咽喉培養,來正確辨識白喉棒狀桿菌,決定毒素的存在。威奇幾乎沒有視診白喉的第一手經驗,在咽喉培養方面更是經驗不足。雖然梅納哥倫布醫院是此區設備最佳的醫院,但它的科技相當原始,資源極為有限,電力時有時無,也沒有實驗室或咽喉培養用的細菌培養皿。威奇已經多年沒做過這類工作,他自己也承認,「我不覺得我有足夠的能力」。
在他的醫療日誌中,威奇記載了美國各地數度爆發的白喉疫情和症狀的資料。儘管已研發出抗白喉血清,白喉傳染病在一九二○年代仍舊持續發生,只是傳播速度較慢,每年約有十五萬人感染,共奪走一萬五千條性命。
在抗白喉血清發明前,白喉奪走的性命數字相當高,它是美國的主要死因之一,更是孩童的首要殺手。白喉曾在歐洲和中東掃滅整個社區;一七三五年,當時還是殖民地的美國爆發「喉嚨瘟疫」,並持續五年之久,相當致命。一位歷史學家估計,每一萬人中有兩千五百人死於這場傳染病。這個死亡數目導致人們開始恐慌疾病可能會毀滅他們的殖民地;有些小鎮失去將近半數的孩童。
虔誠的殖民地開拓者試圖破解白喉是如何侵襲社區,以及他們染上疾病的原因。但這疾病似乎任意出擊,沒有特定目標,當時沒有人瞭解健康的帶菌者也能傳播白喉。當不管是徹夜不眠的祈禱或善良行徑都無法解救孩童時,不止一位牧師宣稱,這場神秘的瘟疫是「原罪的天譴」之一。
麻薩諸塞州的強納生.狄更森是殖民地影響力頗劇的宗教領袖,他曾如此描述他的病患所承受的痛苦:
一開始往往只是身體微恙,類似一般感冒,伴隨著有氣無力,緩慢、若有似無的發燒,喉嚨稍感疼痛,扁桃腺腫脹:也許還流鼻水,臉色慘白,眼神無光和沉重。病患並沒有未被隔離,數天內也未出現任何危險症狀。直到逐漸演變成高燒,整個喉嚨,有時甚至口腔上方和鼻孔都包覆著一層硬殼……當肺部受到感染時,病患剛開始會發出重濁的乾咳聲,然後立刻發展成奇特、令人憂慮的氣喘症狀,進而呼吸困難。悲慘可憐的病患不斷掙扎,直到完全窒息,或呼吸停止,才得到解放。
對那些在狄更森的照顧下倖存的少數人而言,康復之路同樣漫長艱辛,就算白喉痊癒了也往往也留下嚴重的次要感染和併發症。「所有我見過熬過這個可怕疾病的人……,」牧師寫道,「永遠都在咳嗽,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斷從肺部吐出數量驚人的白色粗硬瘡痂。另一方面,我也看過
在嚴重咳嗽時,從肺部撕扯下來的大片硬殼,有幾吋長,近一吋寬……。」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白喉繼續在病患和醫生心中造成恐懼。這個疾病在很多城市變成地方性疾病,不時爆發。醫生和研究學者花了不少時間研究白喉,但不管他們有多瞭解它詭譎多變的病程和各種徵兆,它仍是不治之症。在全國的病床和醫生的辦公室裡,一個小孩喉嚨痛都會成為恐懼和恐慌的來源。
醫生們嘗試過用各種找的得到的藥膏,但它們大部分只是延長病患的痛苦,或加速他或她的死亡。有些醫生為病患注射水銀,其他則在偽膜上塗抹或注射碳酸,或試圖勉強用鑷子拔除偽膜,結果留下鮮血淋漓的發炎表面供細菌繁殖。最死馬當活馬醫的手法是吸出偽膜,為即將窒息的孩童清除氣管。
一八二○年代早期,醫生開始嘗試一種叫氣管切開術的新治療手法,就是將頸部和肺部氣道的肌肉切開,這方法往往和疾病本身一樣致命。直到一八八○年代,一位紐約醫生,約瑟夫.歐德威,研發出用中空的小管子從嘴巴插入氣管的方法後,氣管切開術才被停用。歐德威的中空管降低了咽喉白喉,一種嚴重白喉病的死亡率,死亡率從百分之百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百分之七十五的死亡率還是不足告慰。而且中空管使用困難;加上能用管子呼吸的孩童仍然可能得忍受由毒素循環所導致的腎臟、呼吸和肺部系統衰竭的痛苦。醫生們努力想找出治癒方針,而眼睜睜看著心愛小孩承受痛苦的母親們寫信給路易.巴斯德在法國的機構,敦請他找出解藥。「你完成了那麼多造福人類的研究,」一位母親寫道,「如果你盡力的話,你一定也能找到治癒白喉這個可怕疾病的方法。我們會跟我們的孩子說,你是他們的大恩人,他們的生命屬於你。」
最後,一位普魯士陸軍醫生,愛米爾.貝林,在巴斯德機構研究期間,研發出一種能中和白喉毒素的「抗毒素」。一八九一年,它首次注射在一位孩童身上,結果救了小孩一命。
威奇知道,如果他無法得到新鮮的抗白喉血清,他將陷入困境。白喉的傳染性極高,細菌的生命力頑強,可以在糖果、廚房流理台面,或手套上生存數週。透過單一接觸,細菌就能從一個溫熱的身體傳染到下一個;打個噴嚏或咳嗽一聲都能透過空氣散播病菌;稍微吸一口氣便可能意味著死亡。在諾姆的每一個角落,都有細菌正靜靜蜷伏著,等待接觸孩童的大好機會;每個窗台或課本都是潛在的登陸地點。
威奇也知道,這疾病能迅速翻越小鎮邊界,擴散到其他沿海村莊。他身為美國公共衛生局的代理助理外科醫生,以及此地區的衛生助理委員,他的責任是照顧阿拉斯加西北部大約一萬人的健康,他的管轄範圍北至北極沿岸,南至育空河三角洲。
大部分住在西北部的阿拉斯加人是愛斯基摩人,他們的危機最大。他們沒有天然抗體可以對抗水手或礦工帶來的細菌或濾過性病毒引發的疾病。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自從他們與歐洲人首度接觸後,他們的人口因麻疹、肺結核,和感冒而大幅減少。
威奇見證了一九一八至一九年的那場流行性感冒把西華德半島的村莊和聚落全數滅絕。「原住民完全沒有抵抗力。」那時的阿拉斯加州長,湯瑪斯.里格說。等這場災難結束時,共有百分之八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百分之五十諾姆原住民死去。而那些存活下來的人持續承受免疫系統下降所帶來的後遺症。
在天花、麻疹和傷寒傳染期間,威奇的前幾任醫生設立了隔離病房和傳染病院,以監控和照顧生病的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有充分的理由對疾病感到深刻恐懼。愛斯基摩人相信死靈,他們害怕如果有一個人在家中死亡,死靈就會找上家中下一個成員。死亡通常使家族成員驚恐、逃跑,但如此一來,疾病反而更會擴散出去。威奇擔心諾姆的原住民也將如此反應,他們一旦試圖逃跑,病菌將會散播到整個小鎮和沿海城鎮。
…
翌晨,一月二十一日禮拜三的早上,威奇天亮前就被從極不安穩的睡眠中被搖醒。亨利.史坦利是住在沙嘴的愛斯基摩人,他的女兒生了重病,需要立即看診。這個家庭住在一哩半外;威奇決定走路可能要比準備狗拉拉雪橇要快,所以他急忙收拾好醫藥箱,穿上松鼠皮派克大衣和紅色滾邊的白色棉質外套,匆匆跑下樓,衝到街上。
沙嘴是條狹長的海灘,連接小鎮西部的蛇河河口。大部分原住民住的單房間草皮小屋,是由漂流木、鯨魚骨、草、錫片,和任何他們能從海灘上撿來的材料蓋成的。有些房子仍然用海豹油燈照明,室內瀰漫著濃重的海豹、鮭魚乾、汗臭,和潮濕的皮草味。威奇早已習慣這種氣味,多年來他學會,甚至欣賞原住民「堅毅粗獷」的天性,他曾這般寫道:「他們知道如何忠心待人,如何去愛,即使他們不會用刀叉用餐,」
七歲的貝西.史坦利躺在圓頂小屋的後側,雙頰凹陷,深色眼眸空洞地凝望前方,胸部在看不見的重壓下費力地起起伏伏。威奇量了她的體溫,發現女孩正在發高燒。她奶油色的皮膚上布滿粒粒汗珠,如涓涓小河般劃過骯髒的污垢。
威奇俯身檢查女孩,他一撬開她的嘴巴,立即聞到一陣腐臭味。貝西的口腔內已變成「一大塊惡臭燻天的偽膜」。當他觸碰偽膜時,馬上噴出大量鮮血。
女孩熬不過傍晚,這下威奇心中再沒任何懷疑,他們正面臨一場災難性的傳染病,小鎮正一步步邁向深淵邊緣。
他返回公寓時,露菈正在準備午餐,他坐下來,將臉埋在雙手中。他花了一會兒才理清思緒,恢復他的專業和鎮定。他告訴露菈發生的事情,然後拿起電話,請接線生盡快幫他接通喬治.梅納德鎮長。之後,他請梅納德召集所有鎮議員,立即前往醫院開會。他們沒有時間拖延了,必須立刻採取行動。
序曲 冰封世界
「我們是冰雪監獄的囚犯。最後一艘船已然駛離,這個小鎮變得遺世獨立,只有北方的暴風、黑暗和寒風相伴。」 ──《諾姆記事報》
在這綿延數百哩、偏遠孤絕的白令海沿岸,柯提斯.威奇是唯一的醫生。過去十八年來,他看著冬天陡然降臨,在遙遠的北方季節遞嬗總是迅速無比。人們說,這裡只有兩個季節:冬季和七月四日國慶日。在諾姆,冬季至少長達七個月,其他季節在短短幾個禮拜內來了又去,倏忽即逝。從七月到十月,白令海面冰雪消融,蒸汽船和縱桅帆船紛紛從西雅圖駛來這個小鎮。西雅圖是離此最近的主要港口,位於南...
作者序
作者跋
我們之間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抗拒狗兒友善的臉龐,或是狗故事裡的精彩細節;而在一九二五年,為了解救白喉肆虐的諾姆,人和狗兒合作接力傳送血清,這個故事堪稱是最高潮起伏的狗故事。我們可以在紐約市的中央公園找到此故事證明,每年計有數千人湧入公園就是為了瞻仰這隻狗的雕像。
巴爾托是一九二五年,冒著暴風雪,領著最後一支接力狗隊進入諾姆的狗兒,這使牠成為全球最聞名遐邇的狗,和電影明星任丁丁齊名。在紐約,欣賞牠勇氣的人關心、追蹤報紙頭條新聞中有關狗和人的傑出功績,並出錢捐贈製作巴爾托的大型雕像。一九二五年,雕像豎立在離第五街不遠、靠近孩童動物園的入口。巴爾托花崗石雕像上的匾額寫著:這座雕像要獻給奔至諾姆的雪橇犬們,牠們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耐力、忠誠和智慧。
我們兩人是堂親,一起在紐約長大,每當我們在中央公園玩耍時,就像其他數百萬名孩童一樣,喜歡攀爬巴爾托的雕像。孩童對巴爾托的熱烈喜愛顯而易見,由於孩童們喜歡拍拍牠的頭、撫摸牠的耳後或爬上牠的背部,因此這些地方的青銅表面早已被磨成一片金光。中央公園管理局的管理員估計,巴爾托的雕像經過這麼多年來被孩童爬騎,已經縮小了四分之一吋。雖然我們對巴爾托的認識和其他小孩一樣無知,但我們都聽說過白喉的可怕故事,而在我們的孩童時期,我們特別害怕其中的一個故事。
我們的祖父,愛德華.賽利伯里醫生是著名的熱帶病專家,當我們的父親們在一九三○年代一起長大時,他是哥斯大黎加東部、加勒比海海岸上一處偏遠地區的鄉村醫生。蓋伊的父親,約翰.賽利伯里在四歲時感染白喉,我們的祖父發現他手上沒有抗毒素,而整個國家境內竟也遍尋不著──這和九年後諾姆唯一的醫生面臨的困境幾無二致。約翰的病況非常嚴重,大家都認為他撐不過幾個小時。當時醫院護士,桃樂絲.布斯──此書謹獻給她──從未離開他身邊。在最後一刻,賽利伯里醫生和飛行員飛到巴拿馬,找到一批新鮮的血清,然後和狂烈的熱帶暴風搏鬥,終於及時趕回醫院,救回小孩一命。不管我們從我們的祖父、祖母和桃樂絲(我們家族深愛並尊敬這位女性)那裡聽過這故事多少遍,每次最讓我們毛骨悚然的一段,都是在抗毒素抵達前,神父已主持過臨終祈禱儀式,工人也蓋好不到四呎長的小孩棺材,準備供葬禮使用。
當我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愛德格.諾納的優雅訃文時,心生了撰寫此書的靈感。他是一九二五年那場接力傳送中最後一位過世的趕狗人,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以九十四歲高齡辭世。報紙標題封他為「傳染病肆虐中的英雄」,但《紐約時報》也寫到,諾納一直宣稱他冒著看不見自己狗隊的風險,在暴風雪中前進二十四哩路,不過「是普通的日常工作」。根據《紐約時報》所言,「這是二十世紀中最扣人心弦的驚險故事。一九二五年,舉國的情緒隨著這故事起伏超過一週,全球都屏息以待,關心救命血清是否能及時送達阿拉斯加那冰封的諾姆鎮。」諾納是這個故事的最後關係人。現在,這個故事已成為「褪色的記憶」,但諾納曾一度幫助「在雪中雕刻出傳奇。」
沒有路通往阿拉斯加的諾姆,這個小社區大約有四千位居民,住在白令海岸邊,距離北極圈以南兩個緯度。自它在一八九○年代的淘金熱中誕生後,超過一百年以來,諾姆就一直是全球最偏遠的小鎮之一。每年,至少有七個月的時間,諾姆都因為結凍的海洋成為一個冰封世界。「我們不啻是冰雪監獄的囚犯。」一位報社編輯在一九○○年發出哀嘆。在天候狀況良好下,飛機現在能在任何季節將諾姆和外面其餘世界連接起來,但它仍舊缺乏聯外道路,甚至到了今日,開車到諾姆就像開車到夏威夷一般不切實際。除非,你是站在一隊狗隊的後方。
每年三月,將近一千兩百哩長的伊迪塔羅德小道狗橇賽如期在安哥拉治和諾姆之間舉行,號稱是「全球最後的偉大競跑」。伊迪塔羅德的路徑橫越阿拉斯加的蠻荒地帶,組合了肯塔基賽馬大會和戴通納五百車賽的刺激元素。它有全球跑得最快的狗兒和駕駛,在考驗技巧、速度和耐力的艱困比賽中拼個你死我活。一九六七年,想保存趕狗傳統的阿拉斯加人創辦這個伊迪塔羅德比賽,宗旨是要提醒人們,狗隊會永遠沿著阿拉斯加的路徑狂奔。這個比賽向聯繫起阿拉斯加孤絕村莊的拓荒者致敬,並試圖使人們記得史上最英勇的狗拉雪橇競跑,也就是一九二五年的諾姆白喉抗毒血清接力傳送。
許多童書都描述過巴爾托和血清接力的故事──史蒂芬.史匹柏甚至還曾以此為主題創作一部廣受歡迎的動畫片──但唯一一本涉及一九二五年前歷史的優秀書籍成書於將近四十年前,即坎尼斯.A.恩格曼所著的短篇故事《跑向諾姆》(The Race to Nome)。自那之後,政府文獻、新的口述歷史、家族記錄、醫療檔案、新聞記載,和未出版的照片一一浮現,這些讓我們得以拼湊出在一九二五年,當世界隨狗兒的動向起伏時,在那關鍵六天內所發生的完整故事。真實故事比任何小孩所能想像的更悲傷、更能啟發人向上。故事的開端就在伊迪塔羅德結束之處,在那片冰封的白令海海岸。
作者跋
我們之間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抗拒狗兒友善的臉龐,或是狗故事裡的精彩細節;而在一九二五年,為了解救白喉肆虐的諾姆,人和狗兒合作接力傳送血清,這個故事堪稱是最高潮起伏的狗故事。我們可以在紐約市的中央公園找到此故事證明,每年計有數千人湧入公園就是為了瞻仰這隻狗的雕像。
巴爾托是一九二五年,冒著暴風雪,領著最後一支接力狗隊進入諾姆的狗兒,這使牠成為全球最聞名遐邇的狗,和電影明星任丁丁齊名。在紐約,欣賞牠勇氣的人關心、追蹤報紙頭條新聞中有關狗和人的傑出功績,並出錢捐贈製作巴爾托的大型雕像。一九...
目錄
序曲 冰封世界
第一章 金子、人和狗
第二章 白喉爆發
第三章 全面隔離
第四章 與狗長征
第五章 飛行機器
第六章 北方獵人
第七章 四十度的法則
第八章 育空河岸
第九章 官場縟節
第十章 冰工廠
第十一章 寒冷的榮耀
第十二章 得救!
終曲 路徑的盡頭
作者跋
附錄A 人物小傳
附錄B 一九二五年血清接力傳送競跑參加者次序及涵蓋哩數
序曲 冰封世界
第一章 金子、人和狗
第二章 白喉爆發
第三章 全面隔離
第四章 與狗長征
第五章 飛行機器
第六章 北方獵人
第七章 四十度的法則
第八章 育空河岸
第九章 官場縟節
第十章 冰工廠
第十一章 寒冷的榮耀
第十二章 得救!
終曲 路徑的盡頭
作者跋
附錄A 人物小傳
附錄B 一九二五年血清接力傳送競跑參加者次序及涵蓋哩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