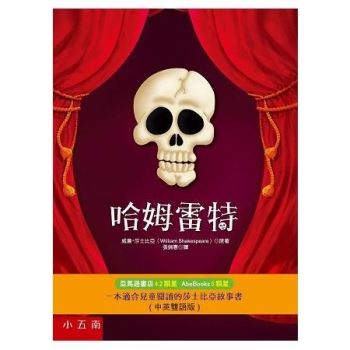推薦序
〈德意志國──一段包圍下的擴張史〉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
這是一本非常深刻的歷史書,將一八七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德國現代史上最精彩的一段娓娓道來,讓人對德國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由哈夫納來講述,更是不二人選。哈夫納對歷史與社會有獨到的觀察角度,而且思考深刻,寫德國的深層文化、社會結構與內心世界,常見人所未見。過去看他《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就解了我心中不少疑惑,曉得,喔,原來那個時代德國年輕人是這樣想的。現在閱讀這本《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也是一樣,一邊閱讀,一邊咀嚼作者的分析,就像在享受一頓豐盛的知識饗宴,掩卷之時但覺齒頰留香。
俾斯麥是德國名相,在他輔助之下,威廉一世統一日耳曼,建立德意志帝國。其實說他輔助威廉一世,用字並不準確,因為俾斯麥不只是「名相」,他根本是「權相」,很多時候是他用個人去留為要脅,逼著威廉一世答應他的要求。有一次君臣二人分別以遜位與掛冠相逼對方,最後威廉讓步,他告訴左右:「德國人可以沒有威廉,但不能沒有俾斯麥。」因此換個角度來看,俾斯麥的行為又不像「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某種程度的「君臣知遇」。這種知遇是千古難逢的,也唯有如此,才成就了普魯士一統日耳曼的霸業。
可是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後,柏林的外交迴旋空間卻一下子消失了。在普魯士時代,由於幅員不大,掌控資源也不多,所以不會成為大家交相攻擊的對象,外交上也可左右逢源。一旦統一了日耳曼,國家變大了,對周邊的威脅也大了,整個世界就跟著變了。因此德國必須想出新的方法,來面對新的世界。這就是本書的開始。
書中引用俾斯麥一八八二年在國會的講話說:「數以百萬計的刺刀主要就直直指向歐洲中央,而我們就站在歐洲中央。我們由於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因為歐洲整體歷史的緣故,遂優先成為其他強權結盟對抗的對象。」幾句話點出了鐵血宰相內心深處的恐懼。其實德意志帝國成為攻擊目標的原因,固然出在她的地理位置(如果沒有統一日耳曼,就不會占據中歐這麼一大塊位置,所以才有人懷疑當初的統一是否有必要)、出在歐洲的歷史,但更出在德國向外擴張的行為。
作者在書中說:「德意志國看起來簡直是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推向毀滅。其權力擴張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國為自己創造出一個由敵人所構成的世界,最後被那個敵對的世界擊破,並且在敵國之間遭到瓜分。」作者是把從普魯士統一日耳曼之後的德意志帝國,到威瑪共和國,再到後來第三帝國這一段時期,稱為「德意志國」。而這一段話,也剛好點出德意志國的宿命。
作者從德國歷史學家的角度返回去思考:為什麼德意志國會不斷擴張?這也是我們外界很想知道的。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的外交其實是採守勢,他與奧國結盟,但拒絕給奧國一張空白支票。他告訴奧國,「如果俄國打你,我會幫你抵抗。但如果是你打俄國,我就不會幫你。」除了很少數情況之外,俾斯麥也不在海外擴張殖民地。他寧可把殖民地作為緩衝,將列強在歐陸可能發生的衝突,轉到海外殖民地去相互補償。從外界來看,這是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典型的以鄰為壑,但從德意志帝國的角度來看,這卻是一種小心戒慎。
俾斯麥的戒慎,也反映在他對過去行為的反思。書中指出,早在日耳曼甫一統一之際,俾斯麥就對一八七○∕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拿下法國的亞爾薩斯、洛林兩省感到後悔。研究西洋外交史的人都知道,法國丟了這兩省,對法國造成很大的創傷,讓法德從此結仇,並發展出此後五十年法國矢志復仇奪回兩省的外交政策。如果德國當初沒有占領這兩省,後面歐洲的發展可能完全不同。只是我們不知道俾斯麥曾因此後悔,並向法國駐德國的外交官表達了這樣的感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哈夫納在書中說,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不斷強調,德意志國已經是一個「飽足」的國家,不會向外擴張。但是一直到俾斯麥下台之後,人們才發現德國其實完全未曾飽足。「隨著普魯士的色彩日益減少,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成分不斷增多,那個(未曾飽足的)現象就益形顯著。」哈夫納指出,「當普魯士依然在德意志國境內享有支配權的時候,她實際扮演了煞車而非發動機的角色。」
將德意志國中普魯士的成分,與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成分加以區分,並以此詮釋歷史可以說是相當深刻的。
德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科技進步及工業發展所帶來的自信也密切相關。德國的工業發展速度超過英國、法國,更不用說俄國了。他們可以打電話、可以開電燈,以非常快的速度現代化,邁向一個超出預期的新世界。哈夫納說,德國人那時在許多領域成為領先全歐的力量,並且是以德國人的身分進行的。這讓他們自戀、自負,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並因此認為應該成為未來世界的霸主。這些描述鮮活地讓我們進入當時德國人的內心世界。我們可以想像,當德國工業發展領先英國時,他們該是如何欣喜若狂,也解釋了德國後來為什麼要去發展海軍,要與英國相抗,在歐洲又如何被奧匈帝國牽著走而失去外交彈性,最終在一次世界大戰後被協約國擊敗。
德國戰敗後,背負著鉅額的賠款,又被限制不准擴張軍備,因此德國如何掙脫這兩道枷鎖,也成為讀者關心的焦點。哈夫納在書中說,當初剛好碰到國際大蕭條,而時任總理的布呂寧就順勢用事,蓄意讓德國的經濟完全崩盤,並以這個手段擺脫賠款的要求。那時德國還積欠三十億馬克的戰費沒有賠償,最後居然不了了之。布呂寧因經濟崩盤而下台,但德國卻獲得喘息空間。這一部分書中描述得相當精彩。
德國簽訂羅加諾公約那一段也很出色。作者描述了一九二五年時,德國如何利用簽訂羅加諾公約,巧妙限制了法國的外交行動。這是外交布局的傑作,也是談判的絕佳案例。同時並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一個戰敗國如何掙脫枷鎖?德國人的心態又是如何改變?如果當時德國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結果是會更好還是更壞?還有,德國在一戰之後所處的歐洲環境,居然比戰爭前更好,這又是為什麼?
這些問題都很深刻,可以從中找到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德意志國發展的一條脈絡。也可以由此反思,現在的德國處境,和當初德意志國的發展,有什麼不同。經由與哈夫納的精神對話,我們對歐洲、對德國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謹以此書,推薦給所有對德國這段歷史,並對歐洲外交史有興趣的朋友。
導言
如果我們彷彿透過望遠鏡一般地來回顧德意志國的歷史,馬上可以發現三個奇特之處。
首先是這個國家的短暫壽命。它只在前後共計七十四年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具有行為能力的整體:從一八七一到一九四五年。即便有人寬宏大量,將其前身的「北德意志邦聯」 一併列入,同時在尾巴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四大戰勝國還願意將德國視為一個整體來管轄的短暫時期,所得出的總和也只有八十或八十一年(一八六七至一九四八年),僅僅相當於一個人一生的歲數。就一個國家存在的期限而言,這個時間未免短得可怕。我幾乎不曉得還有任何別的國家會如此國祚短促。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國在此非常短暫的生命期限內,至少有兩度(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三三年)──但實際上是三次(還包括更早的一八九○年)──徹底更改了自己的內在性格與外交政策路線。這八十年的時間內於是出現過四個涇渭分明的階段,而且我們甚至可以如此表示:德國在其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變成了另外一個德國。
第三個奇特之處則在於,這段如此短暫的歷史是以三場戰爭做為序幕,然後以兩場駭人聽聞的世界大戰收尾,而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多或少脫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此看來,德意志國的歷史簡直就像是一部戰爭史,而且難免會有人設法把德意志國稱作「戰爭之國」。
人們自然會想問個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莫非德國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加好戰嗎?我倒並不這麼認為。若將德國人的歷史看待成一個整體,亦即著眼於一千年出頭的時光,便可發現德國人在俾斯麥的時代以前很少發動戰爭,而且幾乎沒有發動過侵略戰爭。德國自從近代初期以來就位於歐洲的中央,成為一個巨大而呈現出多元面貌的緩衝地帶,不但時而有外力介入干預,德境內部也爆發過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諸如「施馬爾卡爾登戰爭」、「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等等 。但是這些內部紛擾並未演變成對外侵略的行動,不像德意志國在二十世紀的時候卻有兩次那麼做了,並且隨之走上末路。
德意志國究竟為何覆亡?它為什麼會偏離其創建者俾斯麥的初衷,變成了一個向外擴張、侵略成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