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書包含了三部分。
第一部稱為「初遇(一九三九?一九六七年)」,是我久遠以前在帝國居留的報告書,其中談及蘇維埃大軍開進我位於波蘭波雷西亞區的家鄉,一場橫越大雪覆蓋、孤絕荒涼的西伯利亞的旅程,遠征至外高加索,並達中亞共和國,換句話說,就是到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邊境,充滿了異國風、衝突和滿載感情與感傷的獨特氛圍。
第二部稱為「鳥瞰(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是我在帝國衰微及最後的瓦解(至少在一九九一年左右還存在的形式範圍內)期間,在它廣闊的土地上做較為長久的漫遊。我一個人走過這些行程,避開官方的機構和路線,走布列斯特(前蘇聯和波蘭邊界)到太平洋的馬加丹,以及沃爾庫塔橫越北極圈到鐵爾梅茲(與阿富汗交界處)這些遠征路線,總長約六萬公里。
第三部叫做「餘波盪漾(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是在旅遊、對話和閱讀空檔間反省、觀察和筆記結集。
本書是以多聲複音的形式寫就,意即穿梭在頁間的人物、地點和主題在不同的年份與章節間可能會重複出現多次,然而相對於多聲複音的宗旨,整體並非總結於一個更高且絕對的總合,相反的,反而是分解與散落,會有這樣的理由源自於我寫作的過程中,主旋律,也就是偉大的蘇維埃超級大國是潰散的。在其領域內,新國度紛紛崛起,而俄羅斯這個住著幾世紀以來,都受帝國野心驅動和統一的民族的龐大國家也身在其中。
這本書不是俄羅斯和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不是共產主義在這國度中誕生與隕落的歷史,也不是帝制的知識概要。
這是份根據我橫越這國家(甚或說是世界這一部分)廣闊幅員旅程的私人報告,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
導讀
他給了我們一個寶山∕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而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到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00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0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而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如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譯者序
見證痛苦,也見證希望∕ 胡洲賢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我與家人聚餐,不是刻意,卻湊巧碰上台灣政黨的再次輪替,餐桌上杯觥交錯,窗外煙火燦爛,然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想起三月初才交出去的一份譯稿,一份譯了近半年,直到交出去的那一刻,依然不斷牽動著心緒的稿子。
每當別人問起我從事的行業,總很難在一時半刻中說個清楚,明明是單純的文字工作,以翻譯為主,卻經常心虛的口吃,只因為比誰都清楚,這實在是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
這樣的感覺,在初次接觸到卡普欽斯基《帝國》的英譯本時,格外深刻。如果說,平常的英譯,已經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那麼翻譯從波蘭文翻譯過來的英譯本,是不是雙重的「不可能」?更何況,卡普欽斯基雖是舉世公認堪為波蘭國寶的記者、作家與詩人,在其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見證過二十七次革命事件,四度被判死刑,曾經連續多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成為大有希望獲獎的候選人,惜終未如願,但國內卻從未得見他的作品,身為一個總是站在幕後的譯者,到底要如何下筆,才能承擔起卡普欽斯基作品首本中文譯作這樣的千斤萬重?
我在網上搜尋,看到了與卡普欽斯基一樣從「記者走上文學之路」的好友張翠容,在二○○八年二月四日發表於她的部落格「真實筆記」中,悼念剛於一月二十三日過世的他的一篇文章,書都還沒譯呢,我已經拿起電話打到香港去,告訴翠容我是多麼的榮幸,卻又是多麼的惶恐……同時也在心中暗暗決定:等譯稿完成後,一定要拜託翠容寫篇序。
之後,我出了場小小的車禍,雖曰小,卻無可避免的影響了日常的生活與排定的工作,但也因為行動不便的關係,讓我能夠定下心來將《帝國》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一次看,都讓我恨不得腳傷快好,可以早一天回到電腦前開機工作,這樣的心情,對於翻譯已久的我而言,已經多時不見了。我相信,那是卡普欽斯基字裡行間的感染力所致。
等到開始翻譯後,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天,我不是帶著激動的心情敲擊著我的鍵盤,只恨十指的速度永遠趕不上腦筋的輪動,而每一天工作的結束,幾乎都是因為我覺得當天的「震懾量」已經過度,熱燙的眼眶讓我無法再面對螢幕上的文字,這哪裡只是單純的文字?每一個字、每一行、每一段、每一頁,你都可以看到佔地超過兩千兩百萬平方公尺,陸地邊界線綿延四萬兩千公尺長,遠比赤道還長的蘇聯境內的苦難和痛楚,那些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哈薩克人、阿爾及利亞人、布里亞特人等等的鮮血與眼淚。
每每我關了電腦,走出房間,還是甩脫不開卡普欽斯基筆下的「帝國」,那個在他七歲便初逢,卻跟大部分的世人一樣,完全無法相信有生之年會看到她崩潰瓦解的龐大政治體。而糾纏著我,甚至追到深夜夢裡的也不僅是卡普欽斯基和英譯者克拉拉˙可羅茲瓦斯卡雖然淺顯,卻訴說著最深刻真相的文字,還有因為資料的不足,那一長串的人名、地名、種族名和宗教派別,更遑論背後的故事和歷史了。
這,到底是蘇聯長期的對外封鎖消息,或是我們島內近年來的鎖國所致?
而我的才疏學淺,自然是無法推諉的最大原因。(特別感謝高鈺茹、繆靜玫、張孝仁及王懿琴四位好朋友在資料查詢上的大力幫忙,譯本中參考資料的周全,全靠他們不吝協助。)
就在這樣複雜的心緒之中,我跟著卡普欽斯基的文字,將帝國下的大地走過一遍,面對他所見所思,他從來不加一字批判,永遠冷靜與客觀,反而是我這個「二度」譯者因為他說及幼時經歷同胞的被驅逐出境後,人人自危的恐懼:
「晚上母親就不再讓我們脫下衣服,鞋子可以脫下來,可是要一直擺在我們身旁,外套放在椅子上,以便眨眼間就可以穿上,原則上我們是不准睡著的……理所當然的,在掙扎和推擠之間,我們都陷入了夢鄉,但母親是真的沒睡,她會一直坐在桌邊,耳邊盡是街上的沉默,要是在這沉默中響起了某人的腳步聲,母親就會一臉蒼白,這個時候出現的人是敵人……」
因而情緒翻騰,光是想像著若是周遭的孩童得夜夜懷著隨時有人來撞門的驚悸入睡,就已經坐立難安,或者看到他為種族衝突所做的以下描述: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個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個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對照於島上長期操弄出來的民粹與種族對立情結,讓人對於總是無法反省的人類歷史,終究都只能無言以對!但我始終相信,他的一顆心比誰都還要熱燙,還要溫柔。
雖然,卡普欽斯基還未來得及等到中文讀者認識他,便告別他多姿多采的人生,但幸而透過他的文字,我們還來得及認識他;如今,卡普欽斯基已然是個傳奇,我的譯文必有無數未及周詳之處,卻仍奢望中文讀者能透過本書,認識這位波蘭人稱:「人類痛苦的見證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見證人。」
推薦序
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 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礡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的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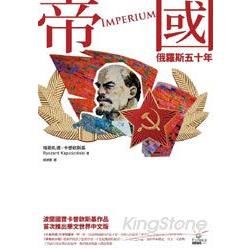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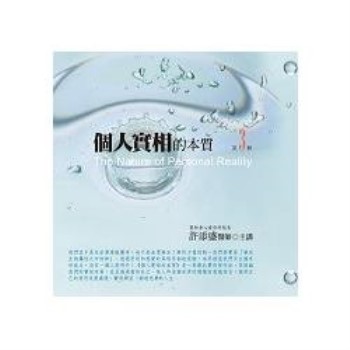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五十年前,本書波蘭作者引用一位波蘭詩人Adam.Mickiewicz 的文字對西伯利亞的描寫:「沒有座位,而因為我的傷口還沒有痊癒,他們塞給我一袋稻草,還指明我是秘密囚犯,只有號碼,沒有名字,這樣的囚犯對他們而言是最重的罪犯,背負著最嚴厲懲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交談,連知道他的名字或他被關的理由都不准。」 「我聽到隔壁牆後傳來的毒打聲,酷刑的聲音以及鎖鏈的叮噹聲。」 在舊日的蘇聯,他們受不了囚犯的尊嚴,這也是極權國家統治者的心態,08年入秋後的台灣,鷹犬爪牙的黑暗身影似乎有點清晰地顯影了。 「西伯利亞適合被放逐與拘禁在於她的廣闊無邊,對於異已放逐不只是時空的錯置,還伴隨著消滅人性的過程;那些如果沒有死在路上終於抵達終點的人,已經被剝奪了之所以成為人的一切。沒有姓氏;不知身在何處;不知道他們要拿他怎麼樣,他的語言已經被奪走了;沒有人會跟他講話,他只是個寄送的貨品…..」 作者花了五十多年的時間大量大範圍的採訪泛俄羅斯這個古老帝國,從1937到1992年,用他的眼睛與筆寫出了一個不同角度的「舊帝國」,我們看過許\多美國人的角度,應該也看過舊日國民黨給我們的「反共抗俄」的角度,也看過昔日俄羅斯文豪過度吹捧的自我角度,當然更遭糕的是近幾年充斥在市場的「投資銀行」角度;這本書提供了我們一種不同的角度看俄羅斯,他從邊境的昔日屬國如亞美尼亞、喬治亞去看看被世人所忽略的不一樣面貌,他對於西伯利亞的描寫,相當生動: 「而那白,無處不在的白,眩目、難測、絕對,一種會把人拉進去的白,要是一個人任由自己被引誘,任由自己被攫住並走得更遠,深入那雪白當中,他唯有死路一條。這片雪白摧毀了所有企圖接近它、試圖解讀其秘密的人….」 「火車不斷開過不同時區,一個人理應持續調整錶上的長短針,但要那幹麻,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改變的知覺在這裡萎縮;也不需要改變…..。」 俄羅斯這片大地,一方面無邊無盡,另一方面卻又具備了另人屏息的全面壓倒性,不留空間讓人用力吸上一口氣,我們台灣是太小的想要出走,俄羅斯是太大的以致於走不出去,閱\讀這本書不時產生這樣的窒息感。 我喜歡本書的「南方」一篇對亞美尼亞的描寫: 「亞美尼亞一切不幸的源頭皆來自於她災難性的地理位置,一個人得學著不是從我們有利的位置去看地圖,而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要從亞洲南部那些決定亞美尼亞命運的人的方向來看。亞美尼亞盤據在地中海、黑海與裏海等三海之間,命運真的不可能把他們的國家放在一個更不幸的位置了,波斯、土耳其、阿拉伯與拜占庭都曾統治過這裡,蒙古與俄羅斯也征服並屠殺過這裡,在過去千年多以來的歷史中,這些不同時空所產生的鄰國強權看著亞美尼亞與週邊的地圖,他們的君王與軍頭們會想到什麼?極端且貪婪的擴張主義會對亞美尼亞做出什麼舉動?….持續千年的被入侵者掠奪。」 羅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成為亞美尼亞的詛咒,除了政治問題以外還有更嚴重的宗教問題。這個國家的歷史讓我想起咱們的家-台灣,幾百年來被荷蘭人、西班牙人、中國海盜、滿清、日本人與中國軍閥不斷地入侵;如今又要面對強大的歷史怪獸。 什麼是歷史怪獸? 許\多國家都曾經有其強大的過去,如蒙古曾經統計三分之二個亞洲與一部份歐洲,法國拿破倫曾經統治過半個歐洲直到莫斯科,德國希特勒除了征服半個歐洲以外還一度佔了北非和中亞,中古時期的土耳其或波斯,她們所建立的版圖一點都不遜於蒙古,五十年前的日不落帝國-英國,一百多年前控制過整個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六十多年前佔據整個東亞與東南亞的日本…..這些國家如果都根據她們的歷史史觀,主張所有她們所曾經統治過的地區都屬於她們的話,恐怕這個世界至少打上一千年的戰爭都無法平息,然而,從這本書的一些俄羅斯昔日屬國的觀點來看,這種強國的歷史怪獸史觀造成了幾千來的流離,這讓我不禁想到台灣的史觀在哪裡?她國對台灣的史觀又是什麼?到底有沒有那頭讓人不寒而慄的歷史史觀怪獸呢? 或許\我們都只是從「投資」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從舊帝國解放出來的國家,我們只會去用「油田利益」、「油氣管運輸」與「原物料蘊藏」的思路去解讀這些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糾紛,而不用她們的角度或她們昔日的角度去詮識,一如台灣許\多無根的媒體言論,我們習慣性地污衊或汙名化「意識型態」,我們更鄉愿無知地被教導要原諒「歷史加諸在我們身上的過錯」。我節錄一段書上的精華: 『在帝國時期,跟人接觸的第一句話,是確認彼此的國籍,因為很多事情會取決於此。』 『如今隨著蘇聯的解體,這些人也正在找尋他們的新身份,新蘇維埃人是舊蘇聯的歷史產物,其中一大部份是由不斷、密集及大規模的遷徙、配置、運輸和流浪人口所組成。』當然我們都曉得,「民族清洗」是這些勾當中最有效的辦法。 『結果就是整個民族的人都發現自己在陌生的國度裡,陷入貧窮與飢荒中,這樣運作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所有人都離鄉背井,讓他們都成為無根的人,剝奪他原來的文化、環境與家園,之後無力反擊的他們就只好任其專制政權支配。』 『一個專制的官員驅趕一整隊的人去勞改營,這些不幸的奴隸沒有一個敢反抗,畢竟他們大可以把這官員殺了,再逃進森林,但不,他們就是順從的走著,聽著官員的口號,默默承受他語言的暴力。…..官員象徵著專治政府的威權,令他們膽戰心驚,這些統治者盤算過,被殖民者到了最後,恐懼會凌駕仇恨…..』 沒錯!恐懼會凌駕在仇恨之上,從拉薩到圓山,我怕了! 評: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