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和老師不見了
班上率先不見的是帕維,因為冬天快來了,老師提說帕維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沒來,這時我們開始明白永遠不會再來了。不久以後,我們看到傑內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們很難過,因為他們兩個開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師才會安排他們兩個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級的孩子一樣消失不見,而且越來越頻繁,很快的就沒有人再問為什麼他們沒來,或者他們到哪裡去了,學校變得空空盪盪的。放學後我們依舊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況有異,球變得沉重,捉迷藏時,也沒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在玩棍球時,每個人都用老手法揮動棍子,搞怪的爭論和激烈的纏鬥一下子就洩了氣,之後每個人都走了,氣呼呼、悶悶不樂或者無精打采。
有天我們的老師也不見了,大家一如往常的在八點以前到校,鐘聲響過後,在我們都坐到座位上時,校長魯柏崴基先生出現在教室門口,「孩子們,」他說:「回家去,明天再來,你們會有位新老師,一位女士。」打從父親離開後,我首度感覺到心臟一陣緊縮,他們為什麼要帶走我們的老師?他一直都很緊張,經常往窗外探看,他會說:「啊,孩子們,孩子們,」同時搖著頭,一直那樣的嚴肅,又好像非常憂鬱,他對我們很好,要是學生在讀列寧的書時結結巴巴的,他也不會大吼大叫,甚至還露出淺淺的微笑。
*****************************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
我問一個站在公車站的女孩如何到火車站去。「我帶你去!」她提議。雖然這是市中心,泥巴卻深及腳踝。今天是陰天;冷冽的寒風呼呼吹著。
頓內次克是烏克蘭煤區的中心;在某些社區裡頭,一堆堆的煤炭和煤渣就直接堆在路上。牆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許多外型相似的建築物,一棟接一棟地延伸了好幾公里,營造出黑色的條紋,灰色的水漬,褐色的鏽狀地衣。
「你喜歡頓內次克嗎?」女孩怯生生的問我。大家對這類問題都很敏感,如果說了一些批評的話語,恐怕會傷害感情。我開始竭力找些正面的字眼來描述這個城市,但口氣似乎少了真誠,因為我停頓下來的時候,女孩便用堅定又近乎驕傲的口吻回應我:「但在夏天,我們的城市會開滿玫瑰花。一百萬朵。你可以想像嗎?一百萬朵玫瑰花耶。」
晚上有一半的時間被我花在頓內次克車站等火車。傍晚時刻,這裡所有的店都已經打烊:包括賣甜茶的唯一一家酒吧、報攤,以及售票亭。大廳裡的燈光昏暗,乘客或相依而坐或躺下來,睡在木頭長條椅上。經過旅途的奔波和漫長的等待,疲倦的他們睡姿都異於平常,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包著披肩和頭巾、裹著大外套、戴著禦寒耳罩,從遠處看來,好像一排排鼓脹的綑包、背包、包裹,一動也不動。
這裡寂靜無聲,窒悶得一點風都沒有,而且黑暗無光。
突然間,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從這些行李之一看不見的深處傳來尖叫聲,一名婦人跳起來繞著大廳轉,無助的跳著。「Vory!Vory!(小偷!小偷!)」她絕望的大叫,大概是醒過來發現皮包不見了,她在長椅間找了好一陣子,嘴上不斷哀嘆:為什麼,為什麼是她的皮包?她向上帝乞求幫助。但是大家毫無動靜,她只好再來回尋找,最後她頭髮凌亂,一臉倦容地回到位子上坐了下來,蜷起身子來,陷入沉默。
然而一會兒之後,又從另一個角落出現同樣可怕恐怖的叫聲,「小偷!小偷!」另一位婦人在我們之間找來找去,讓我們看她雙手空空,但是人人依舊視若無睹;照樣縮著身體藏起來,蜷成了一團。
只有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睜開眼睛,或許是對我,也或許是對她自己說:「Zyt掇trashno(生活太可怕了!)」邊說邊把她的油布袋子抱得更緊,再度回到她警醒的淺睡中。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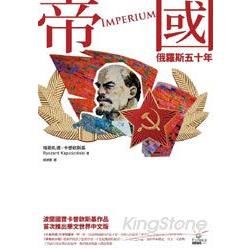 |
$ 250 ~ 334 | 帝國:俄羅斯五十年
作者: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 / 譯者:胡洲賢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08-10-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52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帝國:俄羅斯五十年
當撰寫《古拉格群島》的索忍尼辛在日前去世,當俄羅斯就在2008年八月進軍喬治亞共和國,我們對於俄羅斯了解多少?
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六次之多的卡普欽斯基,這是他橫越俄羅斯的私人報告,他訪談的是一般老百姓,捕捉了蘇聯帝國即將崩壞之際,那塊土地滿載的衝突與情感,以及人們對於未來的恐懼與希望。
在身為外國通訊記者的生涯中,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親眼見證了二十七次的革命與政變。
《帝國》是一個帝國的故事:有一群國度,這一整個世紀大部分都潛伏在一個單一象徵,也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官僚及難以歸類的一團混亂下。在柏林圍牆倒塌那一年,也就是帝國撼動及死亡期間,卡普欽斯基和好幾百個平凡百姓談及他們非比尋常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浮現的驚駭。
《帝國》是一個民族與時間對抗,讓人折服的結果:在一九八九年那極棒也極可怖的事件遠逝成為過去之前,捕捉了人們的記憶,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恐懼。
章節試閱
同學和老師不見了 班上率先不見的是帕維,因為冬天快來了,老師提說帕維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沒來,這時我們開始明白永遠不會再來了。不久以後,我們看到傑內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們很難過,因為他們兩個開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師才會安排他們兩個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級的孩子一樣消失不見,而且越來越頻繁,很快的就沒有人再問為什麼他們沒來,或者他們到哪裡去了,學校變得空空盪盪的。放學後我們依舊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況有異,球變得沉重,捉迷藏時,也沒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
-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08-10-02 ISBN/ISSN:9789867247803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西方歷史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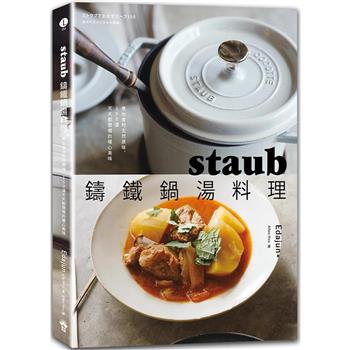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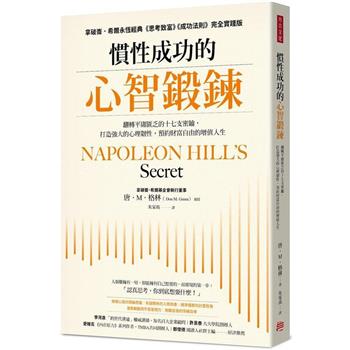










五十年前,本書波蘭作者引用一位波蘭詩人Adam.Mickiewicz 的文字對西伯利亞的描寫:「沒有座位,而因為我的傷口還沒有痊癒,他們塞給我一袋稻草,還指明我是秘密囚犯,只有號碼,沒有名字,這樣的囚犯對他們而言是最重的罪犯,背負著最嚴厲懲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交談,連知道他的名字或他被關的理由都不准。」 「我聽到隔壁牆後傳來的毒打聲,酷刑的聲音以及鎖鏈的叮噹聲。」 在舊日的蘇聯,他們受不了囚犯的尊嚴,這也是極權國家統治者的心態,08年入秋後的台灣,鷹犬爪牙的黑暗身影似乎有點清晰地顯影了。 「西伯利亞適合被放逐與拘禁在於她的廣闊無邊,對於異已放逐不只是時空的錯置,還伴隨著消滅人性的過程;那些如果沒有死在路上終於抵達終點的人,已經被剝奪了之所以成為人的一切。沒有姓氏;不知身在何處;不知道他們要拿他怎麼樣,他的語言已經被奪走了;沒有人會跟他講話,他只是個寄送的貨品…..」 作者花了五十多年的時間大量大範圍的採訪泛俄羅斯這個古老帝國,從1937到1992年,用他的眼睛與筆寫出了一個不同角度的「舊帝國」,我們看過許\多美國人的角度,應該也看過舊日國民黨給我們的「反共抗俄」的角度,也看過昔日俄羅斯文豪過度吹捧的自我角度,當然更遭糕的是近幾年充斥在市場的「投資銀行」角度;這本書提供了我們一種不同的角度看俄羅斯,他從邊境的昔日屬國如亞美尼亞、喬治亞去看看被世人所忽略的不一樣面貌,他對於西伯利亞的描寫,相當生動: 「而那白,無處不在的白,眩目、難測、絕對,一種會把人拉進去的白,要是一個人任由自己被引誘,任由自己被攫住並走得更遠,深入那雪白當中,他唯有死路一條。這片雪白摧毀了所有企圖接近它、試圖解讀其秘密的人….」 「火車不斷開過不同時區,一個人理應持續調整錶上的長短針,但要那幹麻,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改變的知覺在這裡萎縮;也不需要改變…..。」 俄羅斯這片大地,一方面無邊無盡,另一方面卻又具備了另人屏息的全面壓倒性,不留空間讓人用力吸上一口氣,我們台灣是太小的想要出走,俄羅斯是太大的以致於走不出去,閱\讀這本書不時產生這樣的窒息感。 我喜歡本書的「南方」一篇對亞美尼亞的描寫: 「亞美尼亞一切不幸的源頭皆來自於她災難性的地理位置,一個人得學著不是從我們有利的位置去看地圖,而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要從亞洲南部那些決定亞美尼亞命運的人的方向來看。亞美尼亞盤據在地中海、黑海與裏海等三海之間,命運真的不可能把他們的國家放在一個更不幸的位置了,波斯、土耳其、阿拉伯與拜占庭都曾統治過這裡,蒙古與俄羅斯也征服並屠殺過這裡,在過去千年多以來的歷史中,這些不同時空所產生的鄰國強權看著亞美尼亞與週邊的地圖,他們的君王與軍頭們會想到什麼?極端且貪婪的擴張主義會對亞美尼亞做出什麼舉動?….持續千年的被入侵者掠奪。」 羅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成為亞美尼亞的詛咒,除了政治問題以外還有更嚴重的宗教問題。這個國家的歷史讓我想起咱們的家-台灣,幾百年來被荷蘭人、西班牙人、中國海盜、滿清、日本人與中國軍閥不斷地入侵;如今又要面對強大的歷史怪獸。 什麼是歷史怪獸? 許\多國家都曾經有其強大的過去,如蒙古曾經統計三分之二個亞洲與一部份歐洲,法國拿破倫曾經統治過半個歐洲直到莫斯科,德國希特勒除了征服半個歐洲以外還一度佔了北非和中亞,中古時期的土耳其或波斯,她們所建立的版圖一點都不遜於蒙古,五十年前的日不落帝國-英國,一百多年前控制過整個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六十多年前佔據整個東亞與東南亞的日本…..這些國家如果都根據她們的歷史史觀,主張所有她們所曾經統治過的地區都屬於她們的話,恐怕這個世界至少打上一千年的戰爭都無法平息,然而,從這本書的一些俄羅斯昔日屬國的觀點來看,這種強國的歷史怪獸史觀造成了幾千來的流離,這讓我不禁想到台灣的史觀在哪裡?她國對台灣的史觀又是什麼?到底有沒有那頭讓人不寒而慄的歷史史觀怪獸呢? 或許\我們都只是從「投資」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從舊帝國解放出來的國家,我們只會去用「油田利益」、「油氣管運輸」與「原物料蘊藏」的思路去解讀這些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糾紛,而不用她們的角度或她們昔日的角度去詮識,一如台灣許\多無根的媒體言論,我們習慣性地污衊或汙名化「意識型態」,我們更鄉愿無知地被教導要原諒「歷史加諸在我們身上的過錯」。我節錄一段書上的精華: 『在帝國時期,跟人接觸的第一句話,是確認彼此的國籍,因為很多事情會取決於此。』 『如今隨著蘇聯的解體,這些人也正在找尋他們的新身份,新蘇維埃人是舊蘇聯的歷史產物,其中一大部份是由不斷、密集及大規模的遷徙、配置、運輸和流浪人口所組成。』當然我們都曉得,「民族清洗」是這些勾當中最有效的辦法。 『結果就是整個民族的人都發現自己在陌生的國度裡,陷入貧窮與飢荒中,這樣運作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所有人都離鄉背井,讓他們都成為無根的人,剝奪他原來的文化、環境與家園,之後無力反擊的他們就只好任其專制政權支配。』 『一個專制的官員驅趕一整隊的人去勞改營,這些不幸的奴隸沒有一個敢反抗,畢竟他們大可以把這官員殺了,再逃進森林,但不,他們就是順從的走著,聽著官員的口號,默默承受他語言的暴力。…..官員象徵著專治政府的威權,令他們膽戰心驚,這些統治者盤算過,被殖民者到了最後,恐懼會凌駕仇恨…..』 沒錯!恐懼會凌駕在仇恨之上,從拉薩到圓山,我怕了! 評: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