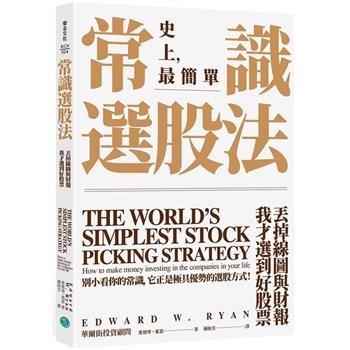這次勒卡雷將寫作的觸角深入北高加索山區,從過往的英、俄兩國之間的間諜大戰轉而關注俄國境內糾葛難分的種族衝突。藉由提姆‧克藍瑪步步追索昔日一手訓練出的反間諜-萊瑞‧裴第佛的過程,凸顯出勒卡雷高超的描繪間諜行動過程的高超功力,更透過萊瑞‧裴第佛觀察之眼、敘述之口,展現出更深層的人道關懷。
作者簡介:
約翰‧勒卡雷,原名大衛‧康威爾,1931年生於英國。18歲時,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之後於伊頓公學教授法文與德文。1959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工作,先後於英國駐波昂及漢堡的大使館服務,同時開始寫作。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舉成名,被知名小說家葛林盛讚說︰「這是我讀過最好的間諜小說!」從此奠定文壇大師地位。
勒卡雷一生得獎無數,包括1965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1964年獲得、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1988年更獲頒CWA終身成就獎(另外分別在1963與1977年獲頒金匕首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2005年C.W.A更是將象徵最高榮譽的「金匕首獎中之獎」頒給約翰‧勒卡雷。至今已出版的19部作品,不僅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的矚目與讀者的歡迎,更因充滿戲劇元素與張力,已有11部被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譯者簡介:
薛絢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專事翻譯。譯作有《福爾摩啥》(大塊)、《費正清論中國》(正中)、《植物的秘密生命》、《空間地圖》、《美學地圖》、《意象地圖》(以上臺灣商務)、《烏托邦之後》、《生生基督世世佛》、《夢:私我的神話》、《長生西藏》、《和平》、《幸福》(立緒文化)…等。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1.史上唯一獲頒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CWA)「金匕首獎中之獎」的大師!2.讀者若曾擔心冷戰結束會影響勒卡雷的題材,現在可以放下心上的石頭了。如果冷戰結束真有影響,不過是使他的可用題材更豐富、更新奇。——《紐約時報》(NewYorkTimes)3.勒卡雷的布局手法教人歎為觀止,掌握當代語言似無還有的弦外之音不輸任何戲劇家。不分喜劇、驚慄、哀歎、笑鬧,該給的資訊無不精確入微,但絕無冗詞賣弄。是一本不凡的小說。——《觀察者》(Observer)4.勒卡雷依舊走在新聞的前面,絕不老調重彈。……一
得獎紀錄:1.史上唯一獲頒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CWA)「金匕首獎中之獎」的大師!2.讀者若曾擔心冷戰結束會影響勒卡雷的題材,現在可以放下心上的石頭了。如果冷戰結束真有影響,不過是使他的可用題材更豐富、更新奇。——《紐約時報》(NewYorkTimes)3.勒卡雷的布局手法教人歎為觀止,掌握當代語言似無還有的弦外之音不輸任何戲劇家。不分喜劇、驚慄、哀歎、笑鬧,該給的資訊無不精確入微,但絕無冗詞賣弄。是一本不凡的小說。——《觀察者》(Observer)4.勒卡雷依舊走在新聞的前面,絕不老調重彈。……一
章節試閱
在往凱瑞堡的末班火車未到之前,我還有兩個鐘頭時間可耗。也許我是步行來的。雖然我厭惡晚報,但是一定在途中某處買了一份。因為第二天早上我發現風衣口袋裡有揉成一團的晚報,油印字跡模糊了。報上的填字遊戲卻做完了,長而尖的大寫字母不大像是我寫的。我一定還喝了幾杯威士忌,因為火車上的事我全忘光了,只記得窗外一片黑暗的玻璃上映出來的影像,有時候是萊瑞的臉,有時候是我的,有時候是愛瑪的,頭髮往上紮起,戴著在她把鋼琴凳子帶來蜜川邸園那天,我送她的十八世紀珍珠項鏈。我腦中一團亂,什麼也想不清楚。萊瑞偷了三千七百萬英鎊、CC是我的同謀、我被認為是另一個共犯。他帶著贓款跑了,愛瑪追他去了——這個萊瑞會偷竊、會翻抽屜、會撬門鎖、會把文件拍照、會把資料背下來、會耐心等待時機,如果必要,會逃走躲起來,都是我一手教的。弗洛迪亞•佐林上校本來是莫斯科派在英國人員中的佼佼者,現在被軟禁了。走在凱瑞堡車站的月台人行橋上,耳邊響起學童的皮鞋,走在這座十九世紀鐵橋上的噠噠聲,我恍惚中覺得嗅到蒸汽和燒煤的氣味。我好像回到少年時代,費力地提著住校生行李箱走下鐵橋的石階,再一次來與巴布伯父共度孤獨的假期。
我那輛精美的古董「日光」轎車,仍停放在我來時的車站停車場位置上。他們來動過手腳了嗎?給它裝上竊聽器和追蹤器了嗎?還是用什麼最新發明的魔術漆噴了一遍嗎?現代科技對我而言是莫測高深的,我從來就沒懂過。開車途中有一對汽車燈緊緊尾隨在後面,我雖然生氣,但曉得,只有呆子和醉鬼會在這條彎路上超車。我繞過路脊穿過村子。教堂有時候會用泛光燈照明,但是今天晚上沒有。村舍窗戶透出來的,尚未關掉電視的光,就像餘燼般地閃動。後面的車燈加速向前,忽而偏斜,忽而直對著我。我聽見按喇叭聲,就讓到旁邊,讓這車子超過去,我看見路寶裡坐著的是西麗亞•都吉森,正興高采烈向我揮手。我也興高采烈向她揮手。西麗亞是愛瑪出現以前,我在本地征服的芳心之一。那時我是蜜川邸園不住在家的地主,也是教區裡,最有身價的週末現身離婚男子。她住在靠近史巴克福的大片地產上,生活清貧,常參加騎馬放獵孤犬的活動,一手策畫區內兒童的假期休閒。某個星期日我邀她來吃午餐,不料酪梨醬還沒上桌,我就和她上了床。我後來仍然擔任她那個委員會的主席,在雜貨店遇見她仍然會閒聊。我再沒和她上過床,她似乎也不會吃愛瑪的醋。有時候我想,她說不定根本忘了我們有過那一次。
蜜川邸園的石頭門柱進入視線。我把速度慢到像爬行,打開黃銅色霧燈,打起精神檢查車道上的輪胎痕。先是約翰•葛皮的郵務麵包車。別人開車到這兒會向左拐,避開凹地裡三個大坑。葛皮不然,儘管我再三請求,他還是要往右拐,因為他四十年來都是右拐,其結果是擠扁了花壇的植草邊緣,輾壞了水仙的球莖。
葛皮的輪胎痕旁邊是藍克森的腳踏車清楚的細瘦胎痕。泰德是幫我栽培葡萄的人,是巴布伯父留給我的,明令我把他用到累垮倒斃為止,他卻絕不會垮,要永遠延續我伯父的各項錯誤。在這一切之上的是陶勒姐妹那輛迷彩噴漆的速霸陸,輪胎痕斷斷續續,時而著陸時而騰空。她們是葡萄園的兼職幫手,泰德對她們又恨又愛。壓在陶勒姐妹車痕上的,是外來的送貨卡車。應該是來送貨的吧。送的是什麼?我們訂購的肥料?星期五送來了。新的空瓶?上個月送過了。
房子前面的這片砂礫路面上乾乾淨淨,這毫無痕跡卻令我不安起來。砂礫地面上為什麼沒有輪胎痕?陶勒姐妹往圍牆的果園的途中,難道沒輾過這裡?葛皮投信時,車子難道沒停在這兒?還有那輛不知何人開的卡車,它大老遠跑到這兒來,之後就垂直起飛了嗎?
我把車燈開著,下車走到砂礫路面上來回找胎痕或足印。這路面有人用耙子掃過了。我回去關了車燈,走上進屋的台階。搭火車回來的路上,我的腰疼發作了。但是此刻走上前廊,疼痛全消失了。門口踏墊上有十來個信封,大多是牛皮紙的。沒有愛瑪的來信,沒有萊瑞的來信。我細看郵戳上的日期,全都遲到了一天。我再檢查黏膠的封口處。都黏得太緊了。局裡的人永遠是這麼笨手笨腳。我把信封都放在門旁的大理石桌面上,不開燈,走上六級台階,進到前廳裡。
我豎起耳朵聽。嗅著空氣。靜止的空氣裡有一縷前不久留下的東西。是汗味?防汗劑?男人的髮油?我雖不能確定是什麼,卻知道它在。我緩步走上通往我書房的走廊。走到一半,又嗅到了:是那防汗劑的味道,還有一絲極淡的陳舊菸味。不是在現場抽的菸——再蠢的人也不會這麼做。也許是在酒館或汽車裡抽的,未必是衣服上帶菸味的這個人自己抽的,但總之是外面來的菸味。
今早我動身前往倫敦之前,並沒有布下陷阱,沒在鑰匙孔上貼一根髮絲,沒在門絞鏈上搭一根線,沒有先拍下核對現場用的原景。我不必做這些,因為我有灰塵。星期一是班波太太休息的日子,她的朋友庫克太太,只在她來上班的時候一起來打掃,趁這個時候數落愛瑪。所以,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二早晨這段時間,沒有人打掃房子,除非我自己來。通常我都會打掃一下。我喜歡做一點家事,星期一,我喜歡把我收集的十八世紀晴雨表擦亮,也擦擦一、兩件得不到班波太太眷顧的其他東西:我的中國式奇本戴爾腳凳和我更衣室裡的古董布告板。
今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但是,我那似乎自童年就開竅的諜報技能告訴我,不要去動灰塵。大廳壁爐和會客廳壁爐燒一夜的圓木,星期一早上就會有一層細灰塵。到星期一晚上,灰塵更多。此時,我一走進書房,就看見我的胡桃木書桌上沒有灰塵。整個桌面上沒有一點老實的灰塵。抽屜的銅把手乾乾淨淨,我能聞到亮光油的氣味。
所以,他們來過了,我想,情緒並不激動。我已經知道他們來過了。梅瑞曼把我召到倫敦去,趁著我被他看住的時候,派他的偵察人員開著搬家具的車,或是電力運貨車,或是他們現在會使用的任何貨車,到我家來闖空門大肆搜查。他算準了星期一是好機會,知道泰德和陶勒姐妹工作的地方,在距離房子五百碼遠,有圍牆的果園裡,除了抬頭看天,完全與牆外的世界隔斷。梅瑞曼派人查我的住處之外,順便檢查了我的郵件,現在八成也查了我的電話通聯記錄。
我走上樓。又是菸味。班波太太不抽菸。她丈夫不抽菸。我不抽菸,而且厭惡抽菸的習慣和菸味。如果我外出回家時衣服上帶著菸味,就會把衣服全換掉,一定要洗澡、洗頭。如果萊瑞到我家來,只要天氣不太冷,我都會把門窗大開著。走到廂房中間的過道口上,我又嗅到了一陣菸味。我的更衣室和臥室的菸味更重。我越過樓廊,來到愛瑪的這一廂:她的一邊,我的一邊,樓廊是隔在我們中間的一把劍,萊瑞的劍。
我手裡拿著鑰匙,站在她門口,和昨晚一樣猶豫著,不知要不要進去。這門是橡木的,鑲有乳釘,本來是一扇大門,不知怎麼移到這兒來用了。我用鑰匙開了門走進去,然後迅速把門關上鎖好,要防什麼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她走後我把這兒整理過一遍,自那一天起,我沒再踏入雷池一步。我緩緩吸一口氣,鼻子和嘴同時吸。有一點點香味爽身粉和我們都不用的麝香味。原來他們派了一個女人來搜,我心想。也許是兩個女的。也許是六個。反正一定是女人:這是局裡堅持的某種頑固體統,不允許已婚男人來亂翻年輕女性的衣物。我站在臥室裡。左邊是浴室,前面是她的工作室。她床旁的小几上沒有灰塵。我拎起她的枕頭。下面放著一件纖柔的純絲連裙睡衣,是我在倫敦龐德街上的「白屋」買的,我為她裝進耶誕禮物的襪子裡,卻從未見她穿過。她離我而去的那天,我發現這睡衣仍包在買來時的細紙裡,塞在衣櫥抽屜的後端。按照諜報特工該做的,我把睡衣拿出來,甩開了,再放到她枕頭底下當作偽裝。☆班波太太,愛瑪小姐北上去聽她的作品演奏了……班波太太,愛瑪小姐過幾天就回來……班波太太,愛瑪小姐的媽媽病得很嚴重……班波太太,愛瑪小姐還在地獄邊緣不上不下……☆
我拉開她衣櫃的門。我買給她的所有衣服,都整整齊齊掛在吊桿上,和她消失的那一天我開櫃看見時一模一樣:輕軟如絲的針織長洋裝、訂做的套裝、她堅決不肯試穿的黑貂皮披肩、高檔名店的皮鞋、更高檔名牌的皮帶皮包。我注視著這些,不知道買這些東西的時候,自己是何許人也?自以為在裝扮一個的,是個什麼樣女子。
是一場夢,我想著。但是,一個男人在現實裡有了愛瑪,何需做夢?我在黑暗中聽見她的聲音:「提姆,我不壞。我不需要不停地改變和偽裝。我覺得我本來的樣子就可以了嘛。真的。」我聽見萊瑞在曼迪普山上的黑夜中,譏嘲我的聲音:「提摩,你不會愛人。你會創造人。但那是上帝做的事,不是你做的。」我又聽見愛瑪的語聲:「需要改變的不是我,是你,提姆。自從萊瑞走進我們果園的圍牆,你的言行就像個在逃亡的人。」我再度聽見萊瑞說:「你搶走了我的人生。我搶走了你的女人。」
我關上櫃門,走進她的工作室,開了燈,瞟了一眼,是怕看見不該看見的,而準備隨時閃避的一瞟。但是,我並沒有看見需要避而避不著的。一切都是原樣,是我在她離去後重建過的原樣。她那張安妮女王時代的書桌,是我送她的生日禮物,經我悉心整理後,變得有條有理。抽屜全都清理過,放進了新買的紙筆文具。壁爐柵擦得亮晶晶,擺好了舊報紙和火種。愛瑪喜歡壁爐生火。她會像貓一樣慵懶地蜷曲在火旁,一邊臀部躬起,頭側枕著手臂。
我的這一遍巡查,幫我暫時釋下重負。假如一整隊的搜查員帶著照相機、橡膠手套、耳機跑進來,除了他們應該看見的,還會看到什麼?☆克藍瑪的女人不值得再查。她會彈鋼琴,穿絲織的長裙洋裝,坐在淑女用的書桌上寫著鄉村的事務。
她的往來文件資料,她重新燃起的,要袪除全世界弊病的那股決心,她的電動打字機不分黑夜白晝滴答不停打的東西,他們完全不知道。
同時,我也承襲了「鄉紳」的頭銜,以及本區受俸牧師的舉薦權。這位牧師要坐鎮的即是小聖雅各教堂,一所袖珍型的早期哥德式座堂,位於我的地產的東側邊界上,一併包括的有門廳、筒形穹頂、袖珍的六角形鐘塔,以及一對漂亮的大渡鴉。由於地點偏僻,人對宗教的熱忱衰退,這教堂已經廢棄了。
那時我剛從倫敦來到蜜川,充滿面對鄉村新生活的責任感。我下定決心,教區當局也完全贊同,要重振我這所教堂的會聚崇拜活動。
如此一個月後,教區當局和我都不得不承認,這樣做是吃力不討好的。
但是我並未就此扔下它不管。我天生就有那麼一點管家的性情,沒多久就發現,我在這七百年歷史的私人教堂裡拖木板地、撣座椅灰塵和擦亮燭檯,都帶給我安慰的滿足。而那時候我也有了要長此以往的另一個理由:聖雅各能給我精神安慰之外,也提供了我踏破鐵鞋也難以覓得的一個最理想的「安全屋」。
我說最理想,不是指其中的聖母堂的鑲壁板鬆動,可以塞進整批檔案而不會被人發覺。也不是指地下室容量大,裡面曾埋葬以往歷任務農住持的毀棄石板棺,可以當作祕密傳遞訊息的地方。我說的是這座六角形的無窗鐘塔,入口是聖器室的一個法衣櫃,櫃子後面接著一道狹小的螺旋樓梯,盡頭的另一扇門後便是古時候教士的祕密藏身處。當初是因為,我覺得鐘塔的六角形外觀和內部的大小不符,誤打誤撞發現了這個祕道,我深信我是數百年來踏進這裡的第一人。
我說「無窗」,其實是鐘塔天才設計師,在六個角的托樑上方的壁上,各留了一條細長的垂直箭孔。所以,藏在這兒的人——不論是為了避難或縱慾——只需站直了身子,就可以從不同角度的箭孔完全掌握來人的動向。
至於透光的問題,我已經試驗過十多次。在我自己安裝了簡陋的照明系統後,在教堂四周反覆觀察,近遠距離都試過。只有在貼著塔牆的時候,而且要仰起頭來,才看得見有昏黃燈光,投映在托樑支起的木頂篷天花板上。
我如此詳細地描述這個祕密藏身所,是因為我的內在生命少不了它。不曾有過陰暗生活的人,不能領會這種生活有著毒癮似的威力。已經捨棄密諜世界的人,或是被那個世界捨棄的人,都無法排遣一股被剝奪之感,有時候會按捺不住,渴望重拾那種生活的情緒,再度投入它懷抱的夢想則是時刻都在的。
每次進到這個教士藏身處,我的心境也一樣。我到這兒來看我的紀念品寶藏:有我不該寫卻寫了,而且仍在繼續寫的日記;有舊的「交心」記錄;有尚未消除不妥內容的任務日誌,是在冷靜密謀時匆匆寫下的;有未被沒收的任務內容彙報錄音帶;還有一份頂層指示銷毀的完整檔案,是確認已銷毀的,其實被我偷偷挾帶出來,存入我的私人檔案庫。保存這些的目的,既是給後代留下確實證據,也是未雨綢繆,準備在我一直害怕的狀況發生時拿來用:例如,我的上司對我有所誤解,或是我自己幹下某種蠢事,以至於損及我曾留下的漂亮記錄。如今,這種狀況發生了。
文件記錄之外,還有我個人的逃亡急救包,這是準備在一切(包括舊記錄)都不能保護我的時候用的。那是我待用身分「白爾斯多」的證件,包括一本護照、信用卡、駕駛執照,都是為了某次半途取消的任務合法取得的,被我保存下來,我自己還動了延期手腳,經過一試再試,確定局裡的後勤官不知道這些東西還在,所以還能使用。這些可不是專門賣假證件的人,為了某一次冒險而偽造的膺品,而是局裡境內工作主管部門的成果,每一件都餵進該餵的電腦系統,信用度核定無誤,已證明不會再被外界查詢了。持有這個急救包的人,只要具備特務的本領——這是我有的,而且有錢——這個我也有,就可以過另外一個新生活,比做他自己更安全。
在往凱瑞堡的末班火車未到之前,我還有兩個鐘頭時間可耗。也許我是步行來的。雖然我厭惡晚報,但是一定在途中某處買了一份。因為第二天早上我發現風衣口袋裡有揉成一團的晚報,油印字跡模糊了。報上的填字遊戲卻做完了,長而尖的大寫字母不大像是我寫的。我一定還喝了幾杯威士忌,因為火車上的事我全忘光了,只記得窗外一片黑暗的玻璃上映出來的影像,有時候是萊瑞的臉,有時候是我的,有時候是愛瑪的,頭髮往上紮起,戴著在她把鋼琴凳子帶來蜜川邸園那天,我送她的十八世紀珍珠項鏈。我腦中一團亂,什麼也想不清楚。萊瑞偷了三千七百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