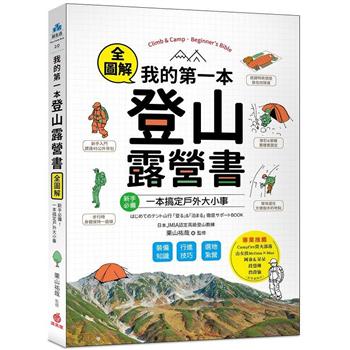伊斯坦堡,1590年代末期,蘇丹祕密委製一本偉大的書簎:頌揚他的生活與帝國。他找來當時最優秀的畫家,以歐洲的風格為此書作畫。然而,在激進宗教基本教義運動盛行的當時,這是一項危險的計劃。任何具像藝術的作品皆被視為對伊斯蘭教的砥觸。為了自身的安危,參與繪畫的藝術家們必需暗中進行計畫。
然而,一位纖細畫家失蹤了,唯恐已遭殺害,這時他們的大師不得不尋求外援。遇害的畫家究竟是死於畫師間的夙仇、愛情的糾葛、還是宗教的暴力?蘇丹要求在三天內查出結果,而線索,很可能就藏在書中未完成的圖畫某處……
奧罕‧帕慕克,土耳其最重要的小說家,名聲響譽全世界。在《我的名字叫做紅》中,他不僅編織出一個驚悚的謀殺之謎,對於愛情與藝術創作,更有深刻迷人的闡釋。
作者簡介: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06.07~)
出生於伊斯坦堡,除了花三年的時間待在紐約之外,他在伊斯坦堡科技大學主修建築以及在伊斯坦堡大學念新聞研究所;自一九七四開始有規律的寫作起,至今從未間斷。
一九七九年第一部作品Cevdet Bey ve Ogullari得到Milliyet小說首獎,並在一九八二年出版,一九八三年再度贏得Orhan Kemal小說獎。
一九八三年出版第二本小說Sessiz Ev,並於一九八四年得到Madarali小說獎;一九九一年這本小說再度得到歐洲發現獎(la Decouverte Europeenne),同年出版法文版。
一九八五年出版第一本歷史小說Beyaz Kale(The White Castle)這本小說讓他享譽全球,紐約時報書評稱他:「一位新星正在東方誕生--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這本書得到一九九○的美國外國小說獨立獎。
一九九○年出版Kara Kitap(The Black Book)是一個里程碑,這本小說讓他在土耳其文學圈備受爭議的同時也廣受一般讀者喜愛。一九九二年他以這本小說為藍本,完成Gizli Yuz的電影劇本;並受到土耳其導演Omer Kavur的青睞。
一九九七年Yeni Hayat(The New Life)一書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轟動,成為土耳其歷史上銷售速度最快的書籍。
一九九八年Benim Adim Kirmizi(My Name is Red)出版,這本書確定了他在國際文壇上的的文學地位;獲得二○○三年都柏林文學獎,這個獎獎金高達十萬歐元,是全世界獎金最高的文學獎。
推薦序
〈導讀〉 故事的拼圖 廖炳惠
到過伊斯坦堡的遊客,都會被那宏偉的氣象所震懾:海天一色、紅河波光粼粼,來往船隻萬紫千紅,猶如一幅奇美無比的圖畫,而整個城市裡,寺院教堂的黃金圓頂掩映成趣,交織出迴腸蕩氣的雄渾瑰麗景觀。不過, 真正精采而值得一再玩味的卻是那蜿蜒曲折的巷弄及多重阻隔的牆面,從斷壁殘垣的歷史古蹟到細膩精緻的牆面圖案,充分顯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橫看是嶺側成峰」的百般變化。
在當代最出名的土耳其小說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筆下,「百萬個細密畫學徒眼睛的牆壁紋飾;懸掛於門和牆上的花紋小盤子;祕密寫入插畫邊框的對句;藏匿於牆底、角落、建築外牆紋飾中、腳跟底下、灌木叢裡和岩石縫隙間的卑微簽名」(一二八頁),任何一個圖案、色彩、空隙、陰影、磚瓦都在牆面上留下歷史、人物、貓狗、飛禽、雲朵、花卉、草木的印記、銘刻及線索,「重複出現在千萬幅畫中」,一片片編織出帖木兒、塔哈瑪斯的往事。歷史故事以牆面一再被印刻繪畫的謄寫方式(palimpsest)呈現出真相與虛構、藝術與政治、美學與宗教之間的穿梭縮影與萬花筒。
享譽全球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是六本小說的作者,《我的名字叫紅》於一九九八年推出後,已被譯成至少二十種語文之多,可算是帕慕克最享盛名的代表作。整部小說以色彩、景物、圖畫為背景,道出十六世紀鄂圖曼帝國的秘辛。透過一位遭到謀殺的畫家(鍍金師高雅‧埃芬迪),去鋪陳各種敘事聲音,由死者本身到兇手到周邊的各種人物及動植物:姨丈、小孩奧罕、守活寡的莎庫兒及追求她的布拉克,或以斯帖、奧斯曼、三位畫師(除了橄欖,還有蝴蝶、鸛鳥)、撒旦,乃至馬、狗、樹、金幣、死亡、紅色等。帕慕克不斷就謀殺事件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個人與國家、藝術與宗教、公共與私人、個別境遇與共同命運,扣緊三本書的插畫(尤其針對蘇丹特別屬意的《慶典之書》及主角正在進行的「一本秘密編纂的書籍」),去「圖」顯政治、愛情、美學信仰的衝突及其暴力。這部作品與其說是以謀殺與偵探情節為主軸,不如說它是個故事拼圖、歷史縮影及權力重新被騰寫的版面,一再以新色彩、布局、主題、人物去再度建構、理解,讓個別敘事者的真相再現方式化入更大的圖畫展軸的縫隙之中。一方面運用有如電影的「縫合」(suture)技巧,連結情節, 擴充人物心理之發展面向,另一方面則又引爆更多的問題,把敘事體的完整、封閉性予以質疑和解除,以便讀者仔細玩味,看出景物在細部鋪寫(detail)、小節複製(miniature)、背景秘辛揭露、重新謄寫的過程裡,一再以新的面貌出土。每一位敘事者的故事真實性也因而成為水中明月,不斷引發漣漪作用,跟著其他繼起的敘事角度而起伏、波動、蛻變、破裂、瓦解。
以「紅」這個主色調為例,它充斥了全書的篇幅,由鮮血(王子弒父兄、畫師殺同事)到紅地毯、紅蠟燭、紅墨水、紅衣裳、紅絲紗、遠方紅船,或紅色所象徵的熱情、真誠,可算得上是既能與各種歷史謀殺篡位、情色角逐、劇烈痛楚等聯想在一起,但也與個人的死亡、記憶、作畫活動,乃至喜悅、自由等情感彼此輻輳。如在一二九頁,「我的思想,我面前的事物,我的記憶,我的眼睛,全部,融合在一起,化為恐懼。我分辨不出任何單一顏色,接著,我才明白,所有色彩全變成了紅色。我以為是血的,其實是紅色的墨水;我以為他手上的是墨水,但那才是我飛濺的鮮血」。不過,到一三八頁,色彩則是「眼睛的觸摸,聾子的音樂,黑暗吐露的話語」,紅色是「炙熱、強壯」的象徵,與情欲、純正幾乎劃上等號,「紅」這位敘事者更透過兩位畫家的對話,問「紅」的感覺、意義及氣味,視紅為對阿拉的狂熱信仰,及對伊斯蘭藝術的堅定理念(本土藝術超過威尼斯的藝術)之表徵,「紅」的意義在於「它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無法向一個看不見的人解釋紅色」,一如「受撒旦誘惑的人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堅持說我們無法看見真主」(一四 ○頁)。反諷的是,這兩位熱烈討論紅色的畫家卻是盲者!在高雅這位鍍金師靈魂飄上天際之時,他肉身所染上的血污卻引導他迎向陽光、天使,他突然察覺到自由的真諦,「頓時,驚懼狂喜之中我明白了自己就在祂身旁。在此同時,我感覺到四周湧入一股無以匹敵的紅」。「短短的一瞬間,紅色染透了一切。這豔麗的色彩溢滿了我和全宇宙」,但是血污的深紅也令他在被帶到衪面前時「感到羞恥難堪」。
紅色是物質與精神兼具,世俗而又神聖的色彩,透過紅色,敘事者將一五九○年左右的伊斯蘭世界日常生活的細節予以著色、勾勒、再現,每一種色彩就像小說中的人物及其觀點一樣,也瀰漫了紅,但大致是血污、熱情與孤獨,只有在純正的紅加以照亮之下,也就是與真主產生信仰接觸之時,才綻放出紅色火花。小說是在這兩種文本技巧(多元聲音彼此交織及紅顏料與純紅之對照)之下展開它的歷史魔幻情節,成為既富偵探色彩又具文學、政治、宗教、自傳、浪漫、流浪、成長,乃至後設小說(metafiction)各種文類的故事拼圖。
《我的名字叫紅》是文類混雜、多音交響、各種畫面不斷重疊的故事拼圖。「故事」的大畫面是以一個歷史重要轉折場景為其視域中心,也就是十六世紀的帝國與宗教、政治、藝術興亡史,而這幅畫的遠近交點(vanishing point)則放在東西文明的橋樑伊斯坦堡,因此可說極具關鍵地位。一五○一年到一七三六年是薩非王朝統治時期,伊斯蘭什葉派為當時的國教,如火如荼地展開對其他教派及其教義的擠壓排斥作用。一五一四年鄂圖曼蘇丹在察地倫擊敗了薩非王朝的軍隊,大舉掠奪波斯大不里士的宮殿,將精美的細密畫、書籍帶回伊斯坦堡,於一五二○年至一五六六年締建鄂圖曼文化的黃金時期,將帝國的版圖加以擴充,往東西方延伸。繼位之蘇丹穆拉德三世登基,《我的名字叫紅》便是在蘇丹三世的任內(1574〜1595),以鄂圖曼蘇丹在伊斯坦堡下令編纂《技藝之書》、《慶典之書》、《勝利之書》的繪製工作此一歷史事件為背景,深入鋪陳細密畫家奧斯曼大師及他的徒弟(橄欖、蝴蝶、鸛鳥、高雅)的作畫工程。
故事一開始是高雅這位鍍金師被殺之後,他以屍體的位勢,作出自我表白及回溯。但是,小說並不是以偵察兇手為其主軸,反而是從不同的觀點一一拼出整個歷史的圖像,先是高雅的屍體說話,他請讀者注意追究他死亡背後所隱藏的「一個駭人陰謀」,因為它「極可能瓦解我們的宗教、傳統,以及世界觀」(一一頁)。死者的記憶其實相當含糊,而且他每一段的敘事長短不一,反而是另一位敘事者,也就是出國十二年浪子回頭,剛從東方返回伊斯坦堡的布拉克,提供了較詳細且立足於個人成長經歷的集體記憶與心理認同戲劇。除此之外,有趣的是:狗、馬、樹、小孩也都來講述所見所聞,一幅一幅由遠而近,個人與群體、公共與私下彼此交織的史詩圖畫長軸於焉展開。值得注意的是:眾多敘事者中有個小孩,也就是原配丈夫一去不回的莎庫兒她的第二個兒子,名字也叫奧罕,據帕慕克在訪談中供稱,莎庫兒的孤獨及她與兒子的關係大致是他本身的親身經歷,兄弟之間的爭吵、打鬥,他們與母親的不斷妥協、和好,其實頗具自傳色彩,這在某一意義上加深了此一小說將歷史與個人傳記交織的面向。但是歷史與魔幻的面向並不出現於歷史、帝王、人物、畫師,乃至作者本人的童年往事彼此糾纏而已。年代紀(如布拉克是於一五九一年回到伊斯坦堡)往往與更重要或隱而不彰的事件連結而在無意識中產生其意義,尤其這些畫師正在奧斯曼的引領之下,紛紛由邊飾、畫馬、著色、鍍金去呈現《慶典之書》的各種面貌。他們是在伊斯蘭教派之間對政教偶像、宗教儀式、繪畫再現的詮釋衝突、族群暴力,乃至伊斯蘭面對基督教勢力,細密畫傳統與威尼斯藝術、東方時間與西方時鐘(伊莉莎白女王所贈)彼此角力的背景之下展現個人的創意及侷限,同時四位畫師與師父、同事、宮廷、行政長官之間也充滿了矛盾,高雅被謀殺之後,他所遭謀殺的原因,不斷在各種敘事聲音中呈現出不同的緣由:貪人錢財、同行相嫉、愛情三角、宗教迫害等,似乎莫衷一是,很難下定論。這些歷史、文化上無法輕易釐清的衝突、變化、暴力、掠奪及協議,扣緊了公共與私人的大小事件,從內到外,由遠而近,或以大型敘事(如布拉克的歷史回憶)及其國家轉型敘事,或以細節(如奧罕、莎庫兒及死者本身的枝節敘事),彼此交會、紋飾、掩蓋,構成了各種交互肯定、指涉或質疑的存在。什麼是主?何者是客?而真相又如何彰顯?這些議題在中古或文藝復興早期的繪畫,尤其一些插圖本(illuminated text)中,其實並非日後的空氣遠近法,以觀賞者之主體位置為準所統合的視域及其世界觀所能比擬。在伊斯蘭的繪畫美學中,畫與隱藏的世界秩序,賞畫者的精神狀態及其宗教情操之間,存在著多重神祕的聯繫,誠如布拉克指出:
趁著每一段寂靜,我研究面前的圖畫,想像畫紙上的顏色分別出自熱情的橄欖、美麗的蝴蝶與亡故的鍍金師之手。我忍不住想學學恩尼須帖對著圖畫大喊:「撒旦!」或「死亡!」,但恐懼阻止了我。不僅如此,這些插畫讓我心煩意亂,因為儘管我的恩尼須帖再三堅持,我卻實在寫不出一則可以配合它們的適當故事。而且,慢慢地,我愈來愈肯定他的死亡與這些圖有關,感到焦躁不安。(一六二頁)
畫與死亡、謀殺、失序、焦躁,尤其與故事背後所隱含的線索有密切的關係。
模仿或複寫是《我的名字叫紅》非常重要的手法。其實不只是畫師做插圖,重新再現畫的意境,人物之間也不斷複製彼此,而畫師們個別講述的三個寓言故事,乃至皇室之中的家庭血腥史,都一再複述出人類的宿命。「兇手」在二十三章結束時的告白也許是個註腳,說明這部作品何以會透過繪書之細節複製畫師及其心路歷程,去鋪陳一個大時代的變化及其潛在的多元衝突、轉機:
我們兩人愛上了同一個女人。他走在我的前方,渾然不覺我的存在,我們穿越伊斯坦堡蜿蜒扭曲的街道,上坡又下坡,如兄弟般行經野狗群聚打架的荒涼巷弄,跨越邪靈徘徊的火災廢墟、天使斜倚圓頂熟睡的清真寺後院。我們沿著對死者靈魂低語的扁柏樹,繞過幽魂聚集的積雪墓園,看不見的遠方盜匪正在勒殺他們的犧牲者。我們走過數不完的商店、馬廄、苦行僧修院、蠟燭工廠、皮革工廠和石牆。隨著我們持續前進,我感覺到自己不是在跟蹤他,相反地,我其實是在模仿他。(九五頁)
踏著古人走過的足跡,穿越荒涼但又熟悉的街道,置身於廢墟與聖殿之間,主角們突然發現自己已進入虛實難分難解的敘事魔域。在這種詭異的情境中,歷史想像、現實世界、小說情節、藝術再現彼此複製,一再可被重新騰寫,此一驚悚體驗大概是這部作品最耐人尋味的面向吧。(本文作者為清大外文系教授)
〈導讀〉 故事的拼圖 廖炳惠
到過伊斯坦堡的遊客,都會被那宏偉的氣象所震懾:海天一色、紅河波光粼粼,來往船隻萬紫千紅,猶如一幅奇美無比的圖畫,而整個城市裡,寺院教堂的黃金圓頂掩映成趣,交織出迴腸蕩氣的雄渾瑰麗景觀。不過, 真正精采而值得一再玩味的卻是那蜿蜒曲折的巷弄及多重阻隔的牆面,從斷壁殘垣的歷史古蹟到細膩精緻的牆面圖案,充分顯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橫看是嶺側成峰」的百般變化。
在當代最出名的土耳其小說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筆下,「百萬個細密畫學徒眼睛的牆壁紋飾;懸掛於門和牆上的花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