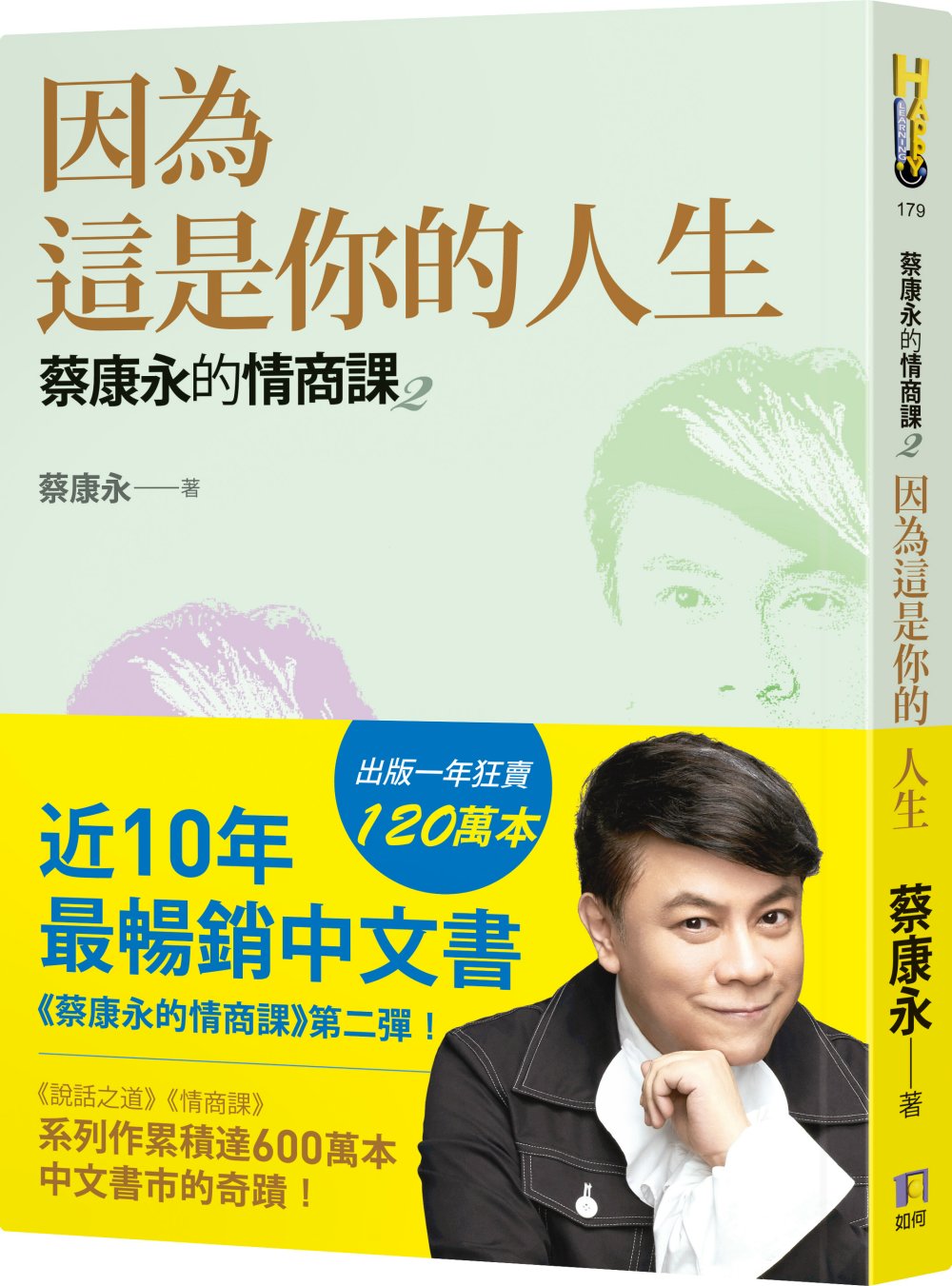(前言)從兩頭牛的哞哞聲開始
國中一年級下學期的某一堂下課,一位同學拿著報紙指著一則社會版新聞問我說:「官淑森,妳看這個偷竊不成居然搶劫的嫌犯跟妳同姓,他是不是跟你有什麼關係?你們的姓這麼少,應該是你的什麼人吧!」一聽,我嚇得冷汗直流,連忙支支吾吾反駁說:「沒、沒關係,怎麼可能有關係,我怎麼可能跟他有關係呢?就好像你不能說,我是『放牛班』的學生,你是『放牛班』的學生,所以我們的兄弟姊妹全都是『放牛班』的學生吧!」雖然我的比喻不倫不類,但她還是如一頭鬥敗的「牛」垂頭喪氣地走了。
「放牛班」這三個字──我跟她直插入心坎的痛。
其實,報紙上面的那個「罪人」是我排行最小的叔叔。而且,我也真的放過牛。像我這個年紀(出生於一九六八年)在台灣放過牛的人應該少之又少吧,更何況是女生;同樣地,像我有這樣一個家的也是寥寥可數吧。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們全家離開故鄉來到台北。表面上,我連續四年的放牛生涯已經結束,然而並沒有。我變成了一頭「牛」,一頭依舊逍遙在群山環繞、綠草如茵的「牛」。
唯一不解的是,不知是我放逐了家,還是家放逐了我。
一個每一塊磚頭都荒謬絕倫的家。
家,距離我越來越遙遠,近在咫尺的遙遠。
直到,從小是資優生最後卻罹患精神病的大妹,無心寫了一首詩:
這個世界
我未曾來過
但走過
慢慢地,慢慢地,我才一個字、一個字被這首詩拖了回來,變成了「人」。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說:「生命就是一段不斷變成的自我。」
我說:「書寫是不斷鼓勵自己長大的一種變奏。」
很慶幸,我終於變成了「人」。
變成了「人」,才能欣賞爸爸的小說、媽媽的散文……自己的詩。每當全家像吃團圓飯般圍在一起討論文學時,彷彿我渾身不停流動的血小板都與他們緊緊黏結在一起,化成一個個的文字癒合昔日的傷口。
不斷地寫,不停地寫,沒想到原來大妹無心寫的那首詩,早就存在於我們每一次的呼吸之中,甚至包括不認識字的奶奶。
於是,我也寫。從哪裡開始?從童年那兩頭牛的哞哞聲開始……
一塊熬了十三年的排骨
從去年開始,我就在報紙的大學聯考榜單上找尋小妹的名字(雖然她改了姓換了名,但她的姓比我的姓還要罕見)。找到了,找到了,我高興地拿去給媽媽看,不久之後打電話去學校的教務處詢問,發現她根本沒來註冊。第二年,我再找,同樣又找到她的名字。這一次,她有到這間學校就讀。
終於,我可以見到她的面了。
在出發之前,我不停地問自己,為什麼想要去找她,難道只有想念嗎?還是想從小妹的身上找到大妹的影子?我不知道,我的理智無法釐清如此澎湃激昂的情緒。
到了新竹的某間師範學院,我去察看課表,等待她今天最後一堂課的來臨。我在教室外緊張地來回踱步,心想第一句話到底應該跟她說什麼?是不是說「對不起,姊姊當初沒有救妳是我的不對,能不能請妳原諒我」,還是說「這幾年妳過得好嗎?不是姊姊不來看妳,而是妳的養父母規定,必須妳年滿十八歲以後我們才可以見面」……
千言萬語。
下課鈴聲響起,我告訴一位從教室走出來的同學說,我要找某某某。等待,十三年的漫長等待。終於,她緩緩走了過來,身材與體型都與大妹生病前極為相似。一時之間,我分不清到底是她還是她,先前所要說的那些話語哽在喉嚨裡,哽在她也哽在我的喉嚨裡。
千言萬語加千言萬語等於,無言。
夕陽餘暉等在一旁,兩人相視默默。不知過了多久,好像一個夢那麼久,她先開口了,﹁妳是姊姊。﹂她認出我了,那她是不是也認出我來自的那個家,一個將她拋棄的家。我記得,她離家前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姊姊,跟我們一起去玩嘛。」但這十三年來誰跟她一起玩,是不是只有回憶,我騎著玩具三輪車載著她兜風的回憶。輪子轉啊轉,轉啊轉,我的淚珠也在眼眶裡打轉,我知道,餓的是久未謀面的親情。於是我說:﹁妳在這裡等一下,我去買便當。」
她看見我哭了嗎?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們坐在校園的涼亭吃著晚餐。自她離家以來,每天我都期盼太陽快快落下,快快升起。當太陽要完全隱沒於某一棟大樓時,我把屬於我的那一塊排骨夾給了她。
一塊熬了十三年的排骨。
我們一塊熬了十三年的排骨。
小籠包裡的風景
不論在「放牛班」或「升學班」,我每天最高興的便是騎腳踏車上學和放學的那段時光(如果爸爸「忘記」來接我的話)。
某某十字路口新開了一家麵包店,某某巷子有一間牛肉麵店已經有好幾個禮拜沒有營業了,某某街上的服飾店正在大減價……有的茂盛,有的枯萎,好像那行道樹隨著季節的轉換而花開花落。
欒樹或大花紫薇有沒有「升學班」或「放牛班」?
有人擅長木工,有人專精吹玻璃,有人嗜好是雕刻……那我適合什麼?適合什麼樣的風景?
在家與學校這段路途的短暫時間中,我騎著一個人的隨堂測驗。
疑惑的青春,青春的疑惑。
答案?
在這所有的風景當中,我最喜歡駐足在一間小籠包的店鋪前面,有一對操山東腔的老夫婦總是笑臉迎人,包括對未上門消費的我。
為什麼他們每天都可以這麼高高興興?他會寫書法嗎?她會去拜拜嗎?他們的子女會覬覦他們一天的收入嗎?他會打她嗎?他們的孫女曾經是一個「賊」嗎?
疑惑的青春,青春的疑惑。
答案?
似乎是為了要獲得答案,存了大約一個禮拜的零用錢,我滿心歡喜走了進去。我點了一籠小籠包,他們送了我一碗清湯。真是美味!他們端上桌的不僅僅是他們的手藝,還有他們夫唱婦隨的秦晉之好。
他們也問我:「功課好不好?」我喝了一口湯之後答說:「不好。」他們笑著說:「沒關係,將來可以跟我們一起學做小籠包。」
一個好難回答的題目?我想起了不久前同學叫我吞進肚子的無辜蒼蠅,還有那輛殃及池魚被老師從二樓摔下的腳踏車。
那是關於我的風景,一點也不可口的風景。
我繼續吃著小籠包,想著沒有答案的答案,濃濃的香竄進鼻息。
一幅風景正看著另外一幅風景。
漸漸長大。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從放牛的小女孩到律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82 |
文學 |
$ 202 |
中文書 |
$ 202 |
職場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從放牛的小女孩到律師
【本書特點】
★動人的心靈筆記,寫出破碎家庭為何因一首詩而完整,是個人傳記,更是勵志散文。
★如詩般的散文形式,意識流的小說筆法,描繪既苦難又心酸的成長經驗、情感真摯的手足情誼。
一個出生在光怪陸離、三代同堂家庭的小女孩,為了幫忙家計而割草、放牛。總是靜靜傾聽她訴說心事的兩頭牛,大大和小小,成為她幼小心靈的最大慰藉。
這個原本父不慈子不孝、荒謬混亂的家庭,搬遷台北後,每下愈況:在國中當老師的爸爸沉迷賭博,並且有了外遇長期不回家;整天想著吞併家產、好吃懶做的叔叔,因偷竊而入獄;本是資優生的大妹,因父母即將離異而致患躁鬱症;而那個小時候放牛的小女孩,升上國中後,卻成為放牛班的叛逆少女,偷錢、說謊、翹課等無所不能……
這樣的家庭,怎麼因一首詩而凝聚力量,成為人人稱羨的文學家庭?而放牛的女孩,又怎會省悟,進而發憤苦讀成為律師?
作者以如詩般的散文形式,意識流的小說筆法,描繪既苦難又心酸的成長經驗、情感真摯的手足情誼,以及細膩的蛻變歷程,是讀來令人動容的心靈筆記,也是成長勵志的最佳作品。
作者簡介:
官淑森
1968年/ 台灣
官淑森,1968年出生。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律師高考及格,現任職於銀行法務室,並於東吳法律研究所進修,專攻金融法。曾獲台北公車暨捷運詩文獎、長榮旅行文學獎等獎項。
章節試閱
(前言)從兩頭牛的哞哞聲開始
國中一年級下學期的某一堂下課,一位同學拿著報紙指著一則社會版新聞問我說:「官淑森,妳看這個偷竊不成居然搶劫的嫌犯跟妳同姓,他是不是跟你有什麼關係?你們的姓這麼少,應該是你的什麼人吧!」一聽,我嚇得冷汗直流,連忙支支吾吾反駁說:「沒、沒關係,怎麼可能有關係,我怎麼可能跟他有關係呢?就好像你不能說,我是『放牛班』的學生,你是『放牛班』的學生,所以我們的兄弟姊妹全都是『放牛班』的學生吧!」雖然我的比喻不倫不類,但她還是如一頭鬥敗的「牛」垂頭喪氣地走了。
「放牛班」這三個字...
國中一年級下學期的某一堂下課,一位同學拿著報紙指著一則社會版新聞問我說:「官淑森,妳看這個偷竊不成居然搶劫的嫌犯跟妳同姓,他是不是跟你有什麼關係?你們的姓這麼少,應該是你的什麼人吧!」一聽,我嚇得冷汗直流,連忙支支吾吾反駁說:「沒、沒關係,怎麼可能有關係,我怎麼可能跟他有關係呢?就好像你不能說,我是『放牛班』的學生,你是『放牛班』的學生,所以我們的兄弟姊妹全都是『放牛班』的學生吧!」雖然我的比喻不倫不類,但她還是如一頭鬥敗的「牛」垂頭喪氣地走了。
「放牛班」這三個字...
»看全部
目錄
因為文學,我們被判「無罪」──寫在《從放牛的小女孩到律師》之前 003
前言:從兩頭牛的哞哞聲開始 015
第1章 故鄉的放牛女孩
嗜血的牛蠅 021
拜拜和「Bye-bye」 023
小販的便當 025
一隻拔毛的雞逃走了 027
討厭的書包 029
會長大的車子 031
向我游過來的水蛇 033
永保新鮮的碗粿 035
外遇的鞦韆 037
一撮被看不起的頭髮 039
一顆沒有心跳的花生 041
看不見眼睛的童年 043
住在墳墓堆的春發 045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龍眼樹 047
「爭氣」的汽水 049
故事老是只講一半的河伯 051
會跟爺爺吵架的毛筆 053
螢幕裡的烏龜 ...
前言:從兩頭牛的哞哞聲開始 015
第1章 故鄉的放牛女孩
嗜血的牛蠅 021
拜拜和「Bye-bye」 023
小販的便當 025
一隻拔毛的雞逃走了 027
討厭的書包 029
會長大的車子 031
向我游過來的水蛇 033
永保新鮮的碗粿 035
外遇的鞦韆 037
一撮被看不起的頭髮 039
一顆沒有心跳的花生 041
看不見眼睛的童年 043
住在墳墓堆的春發 045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龍眼樹 047
「爭氣」的汽水 049
故事老是只講一半的河伯 051
會跟爺爺吵架的毛筆 053
螢幕裡的烏龜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官淑森
- 出版社: 健行 出版日期:2006-08-10 ISBN/ISSN:9867753860
-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職場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