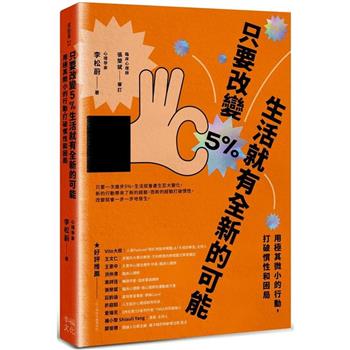三年又六週的閉關
閉關中心的硬體設施
在佛教的心靈發展體系中,研習(聞)和深思(思)在禪修(修)中獲得實踐。儘管在理論上,研習與禪修緊密連結被認為是理想的狀況,但是這兩種訓練在制度上通常是分別而獨立的:新進的學者被吸引進入佛學院;未來的禪修大師進入閉關中心──一個設計來傳授完整禪修訓練的機構。
在舊譯派(寧瑪派)和口耳傳承(噶舉派)的傳統中,基本的密集禪修訓練課程持續三年又六週。《蔣貢康楚閉關手冊》是針對這種形式的閉關所撰寫而成的指南,這些閉關中心的硬體結構並沒有標準的模型。我造訪了喜馬拉雅山區,包括西藏、印度和尼泊爾,和其他國家,包括法國、加拿大和台灣的閉關中心,以下的描述即是以這些閉關中心為基礎。
一個禪修閉關中心通常獨立於一座寺院、寺廟或公共禪修中心等主要的建築物之外,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團體,受到所隸屬的較大機構的供給和保護。
從外部來看,閉關中心是靜止的島嶼,本來就無意吸引外界的注目。進入閉關中心的人,把對家庭、生計或社會的義務和責任留在門外,等到他們所選擇的訓練時期結束後,再重新擔負起這些義務和責任。在禪修閉關期間,公眾在任何時間都不容許進入閉關中心,只有隨侍的廚師和被指派的禪修指導者是唯一能夠進出閉關中心的人員。
在閉關中心的結界內,一些建築物環繞著中庭。每一個閉關行者都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關房,禪修者在這個房間度過一天絕大部分的時間。寺廟是最大的建築物,整個團體一天在此聚集兩次:早晨和傍晚,以進行團體的祈請和禪修(在喜馬拉雅山區的閉關中心,皆會在這兩個時間供應早餐和晚膳)。另外,在閉關中心的結界內,有一個大房間供閉關行者練習瑜伽。閉關中心內的其他建築構造還包括廚房、浴室和廁所,整個閉關中心被圍牆或籬笆環繞,以杜絕公眾的窺探。
每一個閉關行者的關房只提供足夠的空間來設置一個小佛堂、一些書架、一張書桌,以及讓閉關行者在地板上做大禮拜時能夠伸展肢體的地方。每一個關房的窗戶都對著中庭敞開。關房裡面沒有床舖,取而代之的是一張「禪修座椅」;那是一個木質的支架,有著低矮的三個面,以及一個高高的靠背,可以既是一張禪修座椅,也是一張床。進行長期密集閉關的閉關行者(例如這本閉關手冊書寫的對象),必須讓自己習慣採取一種坐著的、挺直的睡姿。
閉關中心通常是一個小團體,居住其中的禪修者人數通常是十二個或十二個以下。喜馬拉雅山區的寺院和佛學院有傾向於擴張人數的一些惡名,然而閉關中心卻不是如此,在這樣的團體中,健全的師生比例一向被認為是必要的。舉例來說,在蔣貢康楚仁波切的閉關中心,只有八個人構成一個閉關團體:一位上師、五位閉關行者、一個廚師以及一個樵夫。
在一些比較次要的部分,蔣貢康楚仁波切的閉關中心脫離了慣常的模式。在這個閉關中心的結界內,有一座以上的寺廟;在一個閉關團體中,同時進行兩個禪修課程。第二個禪修課程是由一個負責第二座寺廟的閉關行者來進行,而這第二座寺廟專供護法。這個閉關中心不像現代大多數的禪修中心,閉關行者在閉關期間,必須把所有私人財物留在儲藏庫中。這種限制後來變成全面的,從宗教物品(例如佛像和唐卡)到衣物;在後來的閉關,甚至連不分尺寸大小的僧袍都由閉關中心提供。這種強制執行的一致性,似乎強調了蔣貢康楚仁波切的堅持:在他的閉關中心的閉關行者,無論他們在閉關中心外的財富或社會地位,都要把自己和他人看成是平等的,並且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
閉關的時期
蔣貢康楚仁波切的閉關中心,課程非常緊密地壓縮成為三年又六週。這種做法看起來或許既專橫又不便,然而,這遵循了遠早於蔣貢康楚仁波切時代即行之已久的一項傳統。
在佛陀入滅前的那一年,佛陀教授《時輪金剛密續》;據說,《時輪金剛密續》代表了佛陀教導的極致。在這本密續中,佛陀描述了宇宙、時間和一個人的身體之間的關係。佛陀的開示為一個禪修閉關的理想長度──三年又六週,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由。
簡單地說,在我們出生後,透過呼吸來和外在世界建立最基本的關係。我們呼吸:我們活著。此外,根據《時輪金剛密續》的說法,我們的呼吸自然而然地和宇宙、和時間連結在一起。在《佛教百科全書》中,蔣貢康楚仁波切指出:
從外部來看,在一年(三百六十天)中,有兩萬一千六百分鐘,而從內部來看,這是我們每天呼吸的次數。(《佛教百科全書》,卷2,頁639)
我們所吸進的空氣進入身體內以維持所具有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和所有眾生所擁有的生命力是一樣的,被稱為「業的能量」。根據密續的觀點,有一小部分的呼吸也供養了我們的心靈潛能,這種心靈潛能被稱為「智慧的能量」。蔣貢康楚仁波切指出:
每一個呼吸的三十二分之一,即是智慧的能量……它的本質是無可摧毀的菩提心。(《佛教百科全書》,卷2,頁639-640)
根據定義,這滋養我們心靈潛能的三十二分之一的呼吸,是正常生命中的一小部分。我們賦予「真正的生命」,也就是業的能量的注意力,削減了這三十二分之一的呼吸的影響力。投注於禪修閉關的時間,會大幅減少業的能量的力量。理想上,所有支配日常生活的事務、慾望、情緒、習慣或生活型態,都被留在閉關中心之外,並且被智慧的能量,也就是心自然的廣闊寂靜、大樂和明晰的覺受所取代。每一個呼吸用來維持業的能量的部分越來越少,相反的則提升了智慧的能量。這個過程是以「證悟」為終點,也就是把業的能量完全轉化成為智慧的能量。
在密續佛教中,據說人類目前的壽命有一百年,換句話說,我們的身體可能能夠維持那樣的時間長度。每一次呼吸的三十二分之一是智慧的能量,經過一百年的累積之後,即等同於三年又六週的呼吸次數。據說這是把業的能量完全轉化成為智慧的能量所必須的最少時間,也就是達到完全的證悟所需要的最少時間。這種狀態是以佛陀的一個身相,也就是「金剛持明」為象徵。如蔣貢康楚仁波切所說:
在一百年期間,(隨著呼吸一起)循環的所有智慧能量,等於三年又六週。當所有業的能量被轉化成為智慧的能量時,就達到了證悟。這是為什麼人們說,(透過)三年又六週的(禪修),達到了佛陀金剛持明的狀態。(《佛教百科全書》,卷2,頁640)
這本閉關手冊所描述的「三年又六週的閉關」,在英文常被說成三年又三個月的閉關。沒有使用「兩週」這個字,或許是因為在現代的英文用法中,這顯得太不合時宜,或者是因為它不是一個精確的翻譯。在藏文中,這個字特別是指月亮盈虧的半期,也就是從新月到滿月,或者從滿月到新月。
雖然本書從頭到尾都把閉關的時期指為三年又六週,但是人們可以合理地把它稱為三年又三個月的閉關。閉關課程所賴以為據的陰曆,必須定期重新調整,來彌補相對於陽曆每年最少損失五天的天數。每隔幾年,藏曆會出現十三個月份,而非十二個月份;有時候每一個月份會少於三十天,但是從不會多於三十天。在禪修課程中,這些多餘的月份會被計算進去,如此一來,閉關時間肯定至少會有三年又二個半月。舉例來說,由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都有十三個月,那麼從一九八九年一月開始的閉關,就會維持三年又三個半月。
閉關中心與性別
大多數長期而密集的禪修閉關都會實行性別隔離。在這段閉關期間,閉關行者把一段時期的獨身生活視為生活的簡單化,容許自己把全副的時間和注意力投注在靈修生活上。
蔣貢康楚仁波切的閉關中心「殊勝遍在大樂」,是一個男性的禪修中心。雖然在蔣貢康楚仁波切的親近弟子中不乏女性,例如在一些著作的末尾,他提及這些書籍是應某位女性弟子之請所撰寫,然而卻似乎不可能為女性創建一個類似的閉關中心,因為就我所知,在他的著作中從未提及這樣的閉關中心。
蔣貢康楚仁波切是一個頂尖的禪修者和作者,而不是一個機構的建造者。如接下來所要解釋的,他自己似乎飽受當時的宗教機構之苦。對於蔣貢康楚仁波切而言,這個閉關中心代表了一個心靈的家園,以及一片清明的綠洲。蔣貢康楚仁波切的生平大志,是去了解他的世界和時代的精神生活,收集過去具有價值的事物,保存瀕臨絕跡的寶藏,並且透過他的著作,讓後世有接觸這些事物和寶藏的管道。說蔣貢康楚仁波切圓滿輝煌地實現了他的雄心壯志,並不是為了漠視一個事實:他似乎遵從那個時代的規範,而沒有替女性建立閉關機構。
這是否暗示了蔣貢康楚仁波切沒有認真地看待女性對精神生活的參與和貢獻?證明這種觀點的證據少之又少,並有充裕的證據支持並非如此。尤其,蔣貢康楚仁波切可以從各式各樣的禪修中,為他的閉關課程做一些選擇,但是在他所選擇的禪修中,有將近一半源自第十世紀的兩位印度女性。另外,在整個閉關期間,每天都要修持的法門之一,即是受到一位西藏女性的啟發,並且把她做為觀修的焦點。
在現代,大多數在喜馬拉雅山區之外實行的三年閉關,都擁有為男性和女性所準備的設施,這兩個團體遵循相同的課程,並且受到指導者同等的注意。然而,在喜馬拉雅山區,情況卻截然不同,女性常常被視為佛教世界的二等公民。花費成千上萬美元去建造和運作的大規模寺院和佛學院仍持續擴增,而且幾乎沒有一年不會推動另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但是這些寺院和佛學院,容許女性加入的制度和機構幾乎不存在。就我所知,在喜馬拉雅山區,以針對女性所設立的三年閉關課程為例,只有噶舉派的泰錫度仁波切和寧瑪派的恰札仁波切這兩位上師建立並支持女性閉關中心,提供等同於男性閉關中心的標準的教導。
閉關中的禪修訓練
閉關中心所遵循的禪修課程雖然會隨著不同的上師或寺院而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某些特色仍是共通的。
閉關行者的一天被分割成為四座個別的禪修(清晨、午前、下午和傍晚),以及兩座團體共修(在早晨和黃昏前)。一天當中,最長的休息時間剛好是中午用餐的時間,所以空閒時間是很匱乏的。如果不了解閉關行者通常要花幾年的時間,積極地為投入這樣一個課程來做準備,就會認為這種訓練的密集程度會令人喘不過氣來。
每日四座的個別禪修,是專門用來從事特定的禪修,而且會不定期地更換,有一些禪修從事數天,另一些禪修則從事數個月。閉關課程是以一個特定傳統最基本的禪修做為開始,逐漸進展到所有的次第,直到最深奧的次第為止。雖然閉關行者對於閉關中心所提供的禪修種類各有偏好,但是閉關中心仍期望所有的閉關行者能夠忠實地遵循課程內容。大多數的閉關中心會讓閉關行者接觸單一一個傳承的禪修技巧。在蔣貢康楚仁波切的閉關中心,課程的負擔格外沉重:他巨細靡遺地指導閉關行者從事三種截然不同形式的密續禪修,並且在這些修持法門之外,增補源自於其他四個傳承的教授。
每日兩座的團體共修,以及定期舉行的特殊儀軌,繁忙的程度是相當可觀的:念誦祈請文、吹奏法器、持誦咒語、從事各種不同的供養,以及念誦更多、總是更多的祈請文。對於許多人而言,沒有這些繁雜瑣碎的事務,閉關的禪修課程就已經負荷很重了,然而事實上,對於那些了解法本的語言、熟悉觀想內容的閉關行者而言,共修儀式可以是具有啟發意義,並且是振奮人心的泉源。
在這段閉關期間,是什麼構成了密續禪修的訓練?如果不簡短地解釋佛教禪修的理論,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一般來說,一個人從事佛教禪修是為了調伏心性,長養洞見自心本性的智慧。這種智慧是以覺醒和證悟為最終結果,但是,覺醒不是禪修的產物──佛教不會創造證悟,如同一面鏡子不會創造一張臉。在佛教修持中,有效的教導被形容為一面可以讓人看見自己臉的鏡子,而這張臉,也就是我們本具的佛性。大多數密續佛教的禪修訓練,僅僅是由「增進心的視力」所構成。
佛教教導一切眾生最深的本質,是一個永不枯竭的智慧、慈悲和創造潛能的蓄水庫。而「四障」是阻止我們清楚地覺察到自己本質的事物。第一種障蔽使我們無法徹底覺察這種本質,即所謂的「無明障」。由於缺乏內在的自我覺察,我們不斷地為自己(一個「我」,一個「自我」)和他人創造身分和本體,此即第二種障蔽,也就是所謂的「習氣障」。我們習慣去創造一個自我和一個世界,然後去相信心的投射是真實的,例如我們在夢境中無意識地、普遍地虛構自我和他人。一旦我們創造了一個自我,無論是在清醒時還是在夢境中,都會受制於各式各樣、以我們的經驗為基礎的煩惱,這就是第三種障蔽,也就是「煩惱障」。在佛教理論中,如果一種情緒會阻礙我們的自我了解,或導致自私自利和有害的言行,那麼這種情緒就被認為是負面的,而這些有害的或自私自利的行為,便構成了最後一種障蔽,也就是「惡業障」。
密續禪修和閉關課程是設計來對治、抵銷這四種障蔽的。閉關從「前行法」開始,用佛教的術語來說,即是從事禪修來清淨惡業障,並累積功德和智慧。用稍微淺白的語言來說,這些修持法門增強並豐富了禪修者身、語、意的覺受。
第二階段的密續禪修,即所謂「生起次第」的禪修,這種修法能對治煩惱障。在修持這些法門的期間,禪修者觀想自己是男性或女性證悟者的形象,使心識覺醒的、栩栩如生的狀態擬人化、具體化。煩惱從我們認為「事物是具體的」這種凡俗見識中生起,生起次第的禪修則適當地提供一個虛構的自我和環境。虛構的事物,是的,但卻是非常善巧的虛構。有可能真的認同虛構的事物嗎?我們的心每天晚上都在回答這個問題。當我們睡著時,無論夢境是多麼古怪,我們都完全相信夢境的真實性。正如某些夢境能夠如此深刻地影響我們的心,不論我們多麼努力地告訴自己:「那只是一場夢。」因此,這些虛構的事物提供了覺醒心廣大浩瀚、充滿活力的覺受,逐漸抵銷我們的負面情緒。
密續禪修的第三個階段是「圓滿次第」,用以對治習氣障,也就是我們創造一個自我和他人的普遍習氣。不像生起次第忙碌地從事虛構,圓滿次第的禪修開啟了如實觀看心識之門,能讓禪修者直接體驗心自然的創造力,也就是我們如何不斷地從空無中創造出一些事物──自我和世界。禪修者也學習循著心的活動而回到它的來處──無邊無際、沒有中心的明光。在這個過程中,自他習氣架構不再像以往一般緊鉗著禪修者的心。
密續禪修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直接「觀照心性」,這是對治無明障的解藥。這些修持法門不會創造這種覺醒的本質。為了看見自己的臉,我們需要一面鏡子;為了看見內在的本質,我們需要上師的教導之鏡。前幾個階段的禪修,清除了心之天空的雲朵;這個最後的階段並不會創造一個太陽,而是認清太陽,也就是光芒四射、明亮照耀的覺察,一直都是存在的,並且讓這種光芒和溫暖充滿整個虛空。這樣的覺察去除了我們對自己的本質缺乏了解的任何殘跡。
在蔣貢康楚仁波切的閉關中心,這四個階段的禪修被重複三次,以三種不同的形式來教授並修持前行法、生起次第、圓滿次第以及觀照心性。形式和專門術語隨著密續佛教不同的傳統而變化,但是這四個階段則是所有傳統共有的。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蔣貢康楚閉關手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8 |
二手中文書 |
$ 187 |
宗教命理 |
$ 193 |
中文書 |
$ 194 |
佛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蔣貢康楚閉關手冊
這是一本為進入密集三年禪修訓練課程的人所寫的指南,由這扇窗口,我們得以了解在閉關中心這個心靈家園內,蘊藏著何等豐富的功德資糧和禪修能量。
在喜馬拉雅山區,三年又六週的閉關是構成密續佛教教育的重要制度之一,本書的內容架構即是以三年又六週的閉關為模型而規劃。
蔣貢康楚仁波切是十九世紀備受尊崇的禪修大師,將畢生心力投注在自己所創建的閉關中心,他關心閉關生活的每個面向,同時規劃閉關行者必須完成的禪修內容。
透過本書,蔣貢康楚仁波切巨細靡遺地描述他所設計的閉關課程之完整樣貌,包括閉關中心的歷史、閉關時的生活、必須學習的課程及禪修訓練,同時教導行者如何作好閉關的準備,以及在圓滿閉關後,如何回到世間的生活。此外,對於八大修持傳承的歷史淵源及教授重點,也有扼要清晰的說明。
章節試閱
三年又六週的閉關 閉關中心的硬體設施 在佛教的心靈發展體系中,研習(聞)和深思(思)在禪修(修)中獲得實踐。儘管在理論上,研習與禪修緊密連結被認為是理想的狀況,但是這兩種訓練在制度上通常是分別而獨立的:新進的學者被吸引進入佛學院;未來的禪修大師進入閉關中心──一個設計來傳授完整禪修訓練的機構。 在舊譯派(寧瑪派)和口耳傳承(噶舉派)的傳統中,基本的密集禪修訓練課程持續三年又六週。《蔣貢康楚閉關手冊》是針對這種形式的閉關所撰寫而成的指南,這些閉關中心的硬體結構並沒有標準的模型。我造訪了喜馬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 譯者: 項慧齡
- 出版社: 橡樹林 出版日期:2008-05-19 ISBN/ISSN:978986788481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