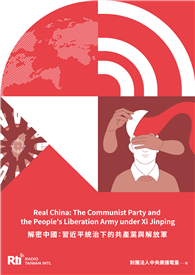米蘭‧昆德拉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作家」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
一個在廢紙收購站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打包工漢嘉,他把珍貴的書從廢紙堆中挑出來,藏在家裡、藏在腦裡,他狂飲啤酒、啃噬著書本裡的思想和詞句,他從一無所知的青年變成滿腹詩書的老人,韓波的詩文、老子的《道德經》、萊布尼茨的情史,是他信手拈來的記憶,康德的話語是他感傷喃喃的聲音。
這是一個愛情故事——老打包工漢嘉和他經歷過的情人,他的工作,他的時代,還有他當作廢紙打包的書,以及他的生命。
他打開他珍愛的書籍,翻到最動人的一段,放在層層疊疊的廢紙中間,打成一個包,外頭再裹上一幅複製的名畫。儘管擺放壓力機的地下室蒼蠅成群、老鼠橫行,這潮濕惡臭的地窖卻在他的遊戲裡,在他的微笑裡成為天堂。
老漢嘉打包著廢紙,打包著他日復一日的生命。他攥著死亡詩人諾瓦利斯的詩集,手指按在向來使他激動不已的詩句上。他幸福地微笑著望見天堂,世界兀自喧囂,擾攘。
赫拉巴爾筆下的小人物,總是通過些微的謊言,觸及了平時難以攫獲的真理。這其實是一個輕而易舉的祕密,也是一種屬於底層生活的娛樂,但卻隱隱浮現著嚴肅劇的樣貌。這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使生活沈重的負荷變得輕鬆的風格;這是赫拉巴爾的書寫,也是真正屬於捷克的氣味。
作者簡介:
Bohumil Hrabal(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捷克作家,被米蘭?昆德拉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四十九歲才出第一本小說,擁有法學博士的學位,先後從事過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廢紙收購站打包工等十多種不同的工作。多種工作經驗為他的小說創作累積了豐富的素材,也由於長期生活在一般勞動人民中,他的小說充滿了濃厚的土味,被認為是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中魔的人們》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集,他把「中魔」看成他創作實踐中的一個新嘗試,寫出了一部從形式和內容都一反傳統的作品。
生於一九一四年,卒於一九九七年。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對這些人寄予同情與愛憐,並且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發掘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刻畫出一群平凡又奇特的人物形象,小說裡充滿捷克的氣味。赫拉巴爾一生創作無數,作品經常被改編為電影,與小說《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同名的電影於一九六六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另一部由小說《售屋廣告:我已不願居住的房子》改編的電影《失翼靈雀》,於一九六九年拍攝完成,卻在捷克冰封了二十年,解禁後,隨即獲得一九九○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過於喧囂的孤獨》命運亦與《失翼靈雀》相仿,這部小說於一九七六年完稿,但遲至一九八九年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捷克《星期》周刊於世紀末選出「二十世紀捷克小說五十大」,《過於喧囂的孤獨》名列第二,僅次於哈薩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克歷險記》。
有人用利刃、沙子和石頭,分別來形容捷克文學三劍客昆德拉、克里瑪和赫拉巴爾,他們說:
昆德拉像是一把利刃,利刃刺向形而上。
克里瑪像一把沙子,將一捧碎沙灑到了詩人筆下甜膩膩的生活蛋糕上,讓人不知如何是好。
赫拉巴爾則像是一塊石頭,用石頭砸穿卑微粗糙的人性。
譯者簡介:
楊樂雲
女,1919年出生,1944年畢業於上海私立滬江大學英語系。曾先後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長期工作,對捷克文學及其歷史文化背景深有了解,數十年來在這一園地辛勤耕耘,翻譯介紹過捷克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赫拉巴爾是當代最偉大的捷克文學家。……他的作品是想像力超凡的創作,充滿幽默、詩意與悖論、荒謬,以及對於人類個體與生活極為動人的洞察觀照。我毫不懷疑,如果赫拉巴爾寫作用的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他的作品早已獲得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了。——捷克筆會前主席伊凡‧克里瑪(著有《我快樂的早晨》等書)
這確實是卡夫卡筆下的布拉格……這本書在邊緣、歡鬧的敘事方式下,自有其趣味。隨著主角漢嘉不停地閱讀、牛飲著啤酒,加上貫穿全書的語調既尖刺又讓人微醺,壓力機碾磨壓縮著廢紙,醉醺醺的漢嘉在文明的破布堆裡翻找搜尋,讀者會以為自己也身陷在那地下室的空間。——《紐約書評》雙周刊(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赫拉巴爾,他是鄉愁的作家,他屬於閃亮慧黠的布拉格,他是日常生活的詩人。——克里斯多夫‧基雅(Christophe Guias),法國《觀點周刊》(Le Point)
名人推薦:赫拉巴爾是當代最偉大的捷克文學家。……他的作品是想像力超凡的創作,充滿幽默、詩意與悖論、荒謬,以及對於人類個體與生活極為動人的洞察觀照。我毫不懷疑,如果赫拉巴爾寫作用的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他的作品早已獲得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了。——捷克筆會前主席伊凡‧克里瑪(著有《我快樂的早晨》等書)
這確實是卡夫卡筆下的布拉格……這本書在邊緣、歡鬧的敘事方式下,自有其趣味。隨著主角漢嘉不停地閱讀、牛飲著啤酒,加上貫穿全書的語調既尖刺又讓人微醺,壓力機碾磨壓縮著廢紙,醉醺醺的漢嘉在文明的破布堆裡翻找...
章節試閱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
在此期間我用壓力機處理掉的這類辭典無疑已有三噸重,我成了一只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側一側,許多蠻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我的學識是在無意中獲得的,實際上我很難分辨哪些思想屬於我本人,來自我自己的大腦,哪些來自書本,因而三十五年來,我同自己、同周圍的世界相處和諧,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裡,嘬糖果似地嘬著,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著,直到那詞句像酒精一樣溶解在我的身體裡,不僅滲透我的大腦和心靈,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騰,衝擊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每一個月,我平均用壓力機處理兩噸重的書籍,為了找到足夠的力量來從事這項神聖的勞動,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滿一個五十米長的游泳池,就是灌滿一大片養聖誕鯉魚的養魚槽,也綽綽有餘了。我在無意中有了學問,現在我確知我的大腦是一堆被壓力機擠壓得嚴嚴實實的思想,一大包觀念,我掉光了頭髮的腦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樣的時代,當一切思想都只記載在人的腦海中時必定格外美好,那時倘若有人要把書籍送進壓力機,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腦袋,然而即使這樣也無濟於事,因為真實的思想來自外界,猶如容器裡的麵條,人只是隨身攜帶著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們焚書是白費力氣,如果書上記載的言之有理,那麼焚燒的時候便只會聽到書在竊竊暗笑,因為一本地道的好書總是指著別處而溜之大吉。
我買過一個計算器,能加減乘除,還能開方,一個不比小皮夾大多少的小玩藝兒。我曾壯著膽子用起子撬開它的後蓋,不勝驚異地發現,裡面除了郵票般大、十張書頁那麼厚的一個小方塊之外,便只有空氣了,滿載著數學變化的空氣。當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價值的書上,當我一行行閱讀這些印刷的文字時,這書留下的也唯有非物質的思想而已,這些思想撲扇著翅膀在空氣中飛,在空氣中滑翔,賴空氣生存,回歸於空氣,因為歸根結柢一切都是空氣,正像教堂裡的聖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
三十五年來,我處理廢紙和書籍,而我生活在一個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居住在過去曾經是王國的地方,在這裡,人們過去和現在都有一種習慣,一種執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壓進自己的頭腦,這給他們帶來難以描述的歡樂,也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們為了一包擠壓嚴實的思想甘願獻出生命。現在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來我按動這台機器的紅色和綠色電鈕,三十五年來我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為了買醉,我憎惡醉鬼,我喝酒是為了活躍思維,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書的心臟中去,因為我讀書既不是為了娛樂,也不是消磨時光,更不是為了催眠,我,一個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的人,我喝酒是為了讓讀到的書永遠使我難以入眠,使我得了顫抖症,因為我同黑格爾的觀點是一致的:高貴的人不一定是貴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會寫作,我要寫一本論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書。
通過閱讀,我從書本中認識到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並非他不想仁慈,而是這樣做違背常情。珍貴的書籍經過我的手在我的壓力機中毀滅,我無力阻擋這源源不斷、滾滾而來的巨流。我只不過是一個軟心腸的屠夫而已。……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把這些東西壓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車開來把包運走,送到火車站,由火車運往造紙廠,在那裡工人們剪斷捆包的鐵絲,把我的勞動果實倒入鹼和酸的溶液中,其強度足以溶化那些總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臉刀。然而,正如流經工廠區的渾濁河水中偶爾會有美麗的小魚閃現一樣,在這廢紙的長河中,不時也會有珍貴書籍的書脊放出奪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發花,我朝別處望了片刻,然後才迅速把它撈出來,先在圍裙上抹抹,翻開書頁聞聞它的香味,這才像讀荷馬預言似的讀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視線,之後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裡,同我發現的其他珍貴書籍放在一起,小箱子裡鋪了許多聖像畫,是不知什麼人連同一些祈禱書誤扔進地下室的。後來,這成了我的彌撒,我的宗教儀式,這些書我不僅每一本都仔細閱讀,而且讀過之後還在我打的每個包裡放進一冊,因為每個包我都要給它裝飾打扮一番,必須讓它帶著我的個性,我的花押。
要讓每個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費腦筋的事情,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幹兩個小時,提早一個鐘點上班,有時連星期六也得賠上,把永遠堆積如山的廢紙送進機器,打包。上月,有人送來三千六百公斤繪畫大師的複製品,扔進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倫勃朗、哈爾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歐洲其他繪畫巨匠的作品,我於是在每個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畫的複製品,到了傍晚,當這些包整齊地堆放在升降梯旁邊等待運走時,它們身上裹著的美麗畫幅使我怎麼也看不夠,瞧,這張《夜巡》,這幅薩斯基亞像,這幅《草地上的早餐》,這張《縊死者之家》,這張《格爾尼卡》。
另外,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還藏著一本名著,這個包裡是翻開的《浮士德》,那包裡是《唐‧卡洛斯》,這兒裹在臭烘烘的紙張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許佩里翁》,那兒,裝在舊水泥袋裡的是《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因而,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我知道,哪個包裡躺著──猶如躺在墳墓裡──歌德、席勒,哪個包裡躺著荷爾德林,哪個包裡是尼采。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是藝術家又是觀眾,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憊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劃了口子,累得要休克,為了緩解和減輕一些這巨大的體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時候,一路上我有足夠的時間琢磨、幻想下一個包該是什麼樣。我灌下那麼多的啤酒,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為我在每一個包裡藏了一件珍貴的遺物,一口沒有蓋的兒童小棺材,撒滿了枯萎的花朵、碎錫紙角、天使的頭髮,我給書籍鋪了一張舒適的小床,它們像我一樣莫名其妙地來到了這間地下室。
因此,我幹活老是完不成任務,院子裡的廢紙堆得山一般高,都頂到天棚了,從洞口倒進我地下室的廢紙也堆積如山,同院子裡的那座山連接了起來。因此主任有時用鐵鉤扒開洞口,臉氣得通紅朝我叫嚷:漢嘉,你在哪兒?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
在此期間我用壓力機處理掉的這類辭典無疑已有三噸重,我成了一只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側一側,許多蠻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我的學識是在無意中獲得的,實際上我很難分辨哪些思想屬於我本人,來自我自己的大腦,哪些來自書本,因而三十五年來,我同自己、同周圍的世界相處和諧,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裡,嘬糖果似地嘬著,品烈酒似地一小口...


 2017/06/29
2017/06/29 2013/04/11
2013/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