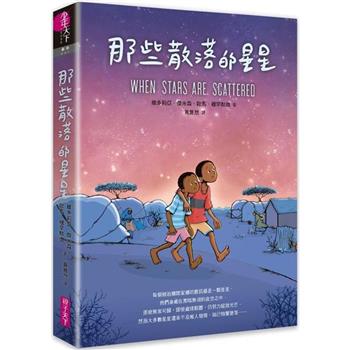普羅旺斯一直被視為神所選擇的寶地。
法國有一個傳說:上帝完成了創造世界的工作之後,手中尚存著最一塊寶石,祂在地球上選擇了一個地方放置這塊寶石,這塊寶石就是現在的普羅旺斯。而普羅旺斯地域最為耀眼的焦點,便是以風命名的風之城市──亞維儂(AVIGNON)。
亞維儂很迷你,幾個鐘頭便可以踏遍它的每一吋土地。它也很特別,前後共有七任教皇在這裡長居。而使它至今仍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年一度的亞維儂藝術節。
亞維儂之於作者孫麗翠,是個生命中最為特別的所在,她在這裡結婚、生子,居住長達十年,熟悉這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後來她的「上 默劇」團又成為台灣第一個參與亞維儂藝術節非官方活動「OFF」的表演團體,獨特的東方默劇深受外國觀眾的喜愛。
在這本書裡,她想告訴你許許多多,關於亞維儂、亞維儂藝術節、「上 默劇」團在亞維儂,台灣劇團在亞維儂,以及生命充滿戲劇性的她自己的故事……
作者簡介:
孫麗翠生長於內壢眷村,自幼習武、太極拳師鄭曼青楊式太極及張少泉孫式太極,並隨峨嵋臨濟氣功傳人傅偉中老師修習氣功多年。
1980年於國立藝專影劇科(現台灣藝術大學)完成學業後赴歐深造,旅居德、義、法、英。
1983年至1986年間在巴黎受教於賈克勒寇(Jacques Lecoq)、馬歇馬叟(Marcel Marceau)、艾田德庫(Etienne Decroux)及湯馬契夫斯基(Henryk Tomachvski)等當代戲劇大師。
1991年返台。返台後從事默劇推廣,致力表演教學。
1994年起遊歷中國,遍及黃河流域、華北平原、戈壁沙漠、青康藏高原、四川雲南,並經泰、緬等地,及澳洲大陸,旅行期間才開始了解到表演藝術的真義,便漸能融會貫通。
1997秋重返台灣後定居屏東一年,實驗所悟之表演藝術教學,教授高雄、台南、屏東及台東各大小劇團。
1998年北上尋屋,落腳陽明山平等里,開始個人演出生涯。
1999年成立「上 默劇」團,專程從行、住、坐、臥、飲食、農耕、製衣的生活中實踐劇場工作與生命主體。
創作作品有《浮世》(Floting World)、《蓮花大地》(Lotus Land)、《大風吹》(Big Wind Blow)、《山海經》(Shan Hai Jing)、《山海經—巫人演義》(Shan Hai Jing— the odyssey of a Shaman)。
◎「上 默劇團」簡介
上默劇團由台灣表演藝術家孫麗翠於2000年成立於臺灣台北,經多年的訓練課程,一步步將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表演藝術精神融匯貫通,以新的美學呈現表達生命源頭的人類普遍性。上默劇的演員肢體都具備鬆、沉、靜、簡的特質;演員在訓練過程中不但以西方表演藝術為表演架構參考,而實質生命則是奠基於東方武術及技藝中天地人的思維基礎、集雅樂舞、太極拳、中國書法及音樂的精隨為導引,化繁為簡,在今世與環境整體合一的宇宙觀,活潑的理出新的古老生命。
章節試閱
「你願意接受身邊這位女子為妻,無論命運如何安排,都能相守一生,同甘共苦嗎?」
「願意!」
「妳願意與身邊的這位男子相守一生,同甘共苦,妳願意他成為妳的丈夫嗎?」
「願意!」
我曾經寫過一齣劇本,故事大略是敘述一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女子,在街頭巧遇一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男子,兩人一見鍾情後,決議舉行婚禮,以彰明兩人誓愛彼此的決心,於是兩人便分頭在街頭路角去尋找各自的主婚人、證婚人,以及假親戚、朋友,延請為婚禮的賓客。
幾年後,我將這齣戲在自己的生命裡上演。
陽光下的婚禮
1986年8月6日,週六,上午10點半,我在亞維儂市政府和英國威爾斯籍的小提琴手公證結婚。
我倆在巴黎街頭結識。當我心飛揚地在龐畢度中心前廣場飄舞著那三丈長的白絲帶時,他入神地用心靈隨著我的腳步翩然起舞,一雙明亮如藍天的眸子有如米開朗基羅壁畫上的天使孩子,把我從十里紅塵拉上雲外,迷失了人間的道路,更糟的是當他打開提琴箱,整弓調弦,將小提琴扣在腮邊開始演奏,我的心乃漸漸地消失……經過許多挫折,我們決定在夏天離開巴黎,前往亞維儂登記結婚,了結來去不定的閃躲與猜疑。
證婚人是當時亞維儂的女市長,當時她那約莫6歲的小女兒靜靜地 依偎在她的身旁觀禮,也許是看了多婚事進行,對於我們的典禮顯得十分無動於衷,這也可能是繼承她母親的安閑容顏,也許她正在為自己將來的婚禮暗自安排,對愛情的憧憬在小小女孩兒的夢裡有如天堂樂園般地美好。
婚禮上,方思旺先生是我的主婚人,新郎那邊則是請方思旺的女伴阿和擔任。方思旺是亞維儂附近的人,住在城裡,是一名手藝很好的鐘錶師,是我的朋友,他臉上洋溢著一種愉快的凝重。婚禮上出席的賓客人數不多,都是在當地所結識的朋友,大多為過客,國籍紛雜,大部分是流浪的音樂家、不得志的作家,也有一位自命不凡的畫匠、一群街頭擺地攤的南美洲人,初遇即知再難相見的應屆畢業的遊歷大學生。
市政府大門口,蘇格蘭風笛手,等著為我們這對新婚燕偶吹奏克爾特婚禮樂曲,他女伴陪在旁邊,擊打著克爾特手鼓,倆人守在市政府大門口,守著新人出來,一切如舊,好像又回到從前部落民族的傳統儀式,莊重深情,充滿了草原生野,山林的幽遠,海浪拍擊岸岩澎湃,禁不住,我帶著羞澀的新郎在廣場上快樂地隨著音樂起舞,停在一旁圍觀的路人都面帶微笑,每張臉龐都被早晨溫柔的陽光染得異常明亮,那一團帶著無語的祝褔空氣載著我們飄飄然地飛翔,劃過廣場,落在旁邊的旋轉木馬上,從克爾特原始情懷,我們坐在旅轉木馬上隨著街頭遊樂音樂旋轉,旋轉,旋轉……
婚禮那天一早,我一個人奔到花卉市場上挑選了一捧白劍蘭,我覺得白劍蘭長得純美又英氣煥然,有如自己想養成的風範,我摘下一串戴在耳邊髮際,當成髮飾。我的禮服是一件淡綠色五○年代的二手及膝紗裙,外罩一件乳色絲質手工小夾克,腳上還是照樣穿著在跳蚤市場買的原皮夾腳舊涼鞋,異國窮途,這樣穿著當新娘也算是慎重了;新郎身著白色西裝,臉上的表情因為興奮而顯得緊張。
那時,我們是那麼的年輕,除了對生命與愛情有著滿腔熱情,義無反顧地選擇自己所認定的真摰外,還能看到些其他的什麼呢?孤獨流浪的靈魂,往往在相遇時發生,不知如何終止的幻變進行曲?那蘇格蘭風笛手的音樂似乎還縈繞在耳際,我再也沒有再見過這演奏音樂的人及他的女伴,連地址都不曾互留,畢竟我們當時都沒有留下地址。
三口人家
結婚那年,我還是巴黎默劇學校的學生,暑假在亞維儂公證結婚後,又北上巴黎繼續學習。後來,懷孕生子,在威爾斯中部的山野湖泊間靜靜地與孩子及家人極簡地生活在一起,在每天的日出日落交會時,我心中總是不停地嚮往再回到普羅旺斯,嚮往那夏日的極藍天空,以及那古城、白牆、灰石小巷……
1989年,普羅旺斯的天空延續著之前的澄藍,我們一家三口在隆河邊的營區紮營住了下來,晚上,三人擠在帳篷的小小空間裡,緊緊地貼著睡在一起。兒子當時一歲半,第一天到營區,看到陽光下的那一片草地,就忍不住開始走起路來,這是第一次,他終於自己決定可以站起來走路,放棄了爬行動物的生涯。
清早他往往是頭一個醒來,自然而然地往帳篷外跑,營區的土地總是散發著令人心神振奮愉悅的氣味,我想那芳香刺激著這小小生命的鼻孔深處,連接到他心腦的底層,喚醒他強碩的靈魂。
睡在地上,毛細孔呼吸著這氣息。每片皮膚都被柔柔的空氣輕彈過,每個當下都好像在聆聽至上的美聲,我們是被這至美包裹住的。
兒子帶領著我結交了一群群的新朋友,每早他那雙小腳便是要踏遍附近所有的營帳,等我伸展身體,勉強睜開惺忪的眼往外找他,他總會笑咪咪地抱著一些食物回來,此刻,他也至少吃過三頓不同的早餐。
這裡有很多樹,尤其是果樹,每個營帳都靠樹來分隔區塊。住在這裡的整個夏天,我們似乎吃完了整樹的杏桃。九月,無花果正紛紛地垂墜在大葉間,我也練就了爬樹攀枝的功夫,吃著新摘下的無花果,彷彿生命就是這樣地美甜。矮灌木叢裡紅紅紫紫的漿果子,讓我們的衣服上時常留有洗不掉的果色印記,豐盛地滿足我們的肉體需要。孩子奔跑在這藍天綠地之間,在樹草花鳥的簇擁下漸漸壯碩起來,至於我這個母親,也不斷地在學習如何在自然的天地間簡單地過日子,享受這世界原有的美善。
我們有一張用門板搭成的長桌,時常會有朋友來一齊吃飯,烹飪器具都是露營必備的。我在廣場畫畫謀生,除了畫畫,照顧兒子、買菜做飯,在亞維儂長長的夏日,我有許多時間得以徜徉於營區的開展空間裡,午後的艷陽讓眾人躲在屋內蔭處,卻成全了我往鄉下探幽的閒情。午後的鄉村路上,無人無車,連蜂、鳥都躲著,空間靜謐得即使一片葉子落地也能被聽到。有時,我帶著孩子一起漫步,也有時孩子午睡,我單獨一人遊蕩,白楊樹在風中竦舞的沙沙聲,銜接著無際藍空,讓亞維儂夏日的節慶都被包裹在城內。城外,則是另一個國度,我可以走上很長的一段路,也可以去臨近的農莊買一箱水蜜桃或黑蜜棗。
九點以後,太陽漸漸西沈,殷紅的天際在轉接暮色時分,會有人彈起吉他。亞維儂四處有西班牙人、吉普賽人,營區也住了許多人家,有些是住在旅行車裡,也有住帳篷,他們都喜歡聚會,一起吃飯,一起玩樂。時間是無需去計較的。營區的生活幾乎是自然的公社制度,每家都沒有秘密,任何用具都可以被借用,買來的食物也大都與人分享,離去的人會將一些物品用具留下來給其他需要的人,儘管每人彼此都不知何時再見,但是,也有每年都在夏天回到亞維儂藝術節工作的人,少見任何衝突發生,大家都是好聚好散,情淡義深。
我在這片綠蔭繁茂的空間裡居住了整個夏天,眼見朋友、遊人一群群,一個個的陸續離開,整個營區變得空曠異常,當無花果季節結束,樹上的葉子開始轉紅,我們也稍稍地在亞維儂城內找到了一間座落在小巷中二樓的舊房子。這幢只有一間客廳與臥室的屋子暫時成為我們過冬的居所。房子裡的傢俱是簡單典型的六○年代風格,一定是房東不捨丟去,放著給房客使用,一張橢圓型大桌,幾張椅子,設計誇張的桌燈,這對於我們這家剛從露營地搬進的房客而言,真是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特別是那張橫跨整間臥室的大床軟得讓身子躺下即不覺去向,營區草地的芳香遺失在隆河對岸,風被牆擋在房外,光總也漸成暗色,我們三人坐在方方的桌前,在角落與角度之間衡量生活人事物,在這方方的屋內,牆壁是白泥抹出的刺粒子,有時不小心一磨擦到皮膚就會受傷,不解當初設計的初衷,也許是要訓練警覺性?不知露營區的冬季真是冷到無可忍受的程度?蒙古人是住在帳蓬裡的!
「房子」也給予了我們這三口人家必要的蔽障,我們的隱私感漸漸重回,在暗色的臥室內,我們可以重新體會晚睡晚起的慵懶,我們可以關門、鎖門,可以對熟人或陌生人說:「對不起,今天比較忙,不方便一起用餐。」
小小的衛浴間裡,我買一個水桶讓兒子在洗澡的時候,可以蹲擠在裡面泡水,孩子和水真是一灘相屬的元素。在這個名叫「房子」的空間內,我們的生活狀態改變了,與他人相處的方式改變了,空氣也改變了。
人總是要找到各種情況轉換時的善意生活,有了一些,也失去了一些,失去的會被另外的取代,「房子」與「帳篷」顯然是兩種生活狀態,孩子不在乎,我們大人也漸漸習慣每種必要的轉換。
這間二樓的「房子」,座落於安靜的巷道裡,神奇的是在於那兩扇老舊不堪的窗,只要一打開,便會與那亙古的天空相遇。
房子旁邊有個小Pilats廣場,廣場中央有棵老榛樹,樹旁的麵包店每天早晨用烘焙的香味告知眾人,招引了絡繹不絕的客人。有不絕於耳的腳步聲,單車鍊條的磨擦聲、人聲、鳥聲、風聲……
亞維儂的老鼠傳承自羅馬帝國時代,在靜靜的街角,突然有一兩隻肥碩的老鼠自下水道的鐵檻竄跑出來,顯得相當驚人,當時我的懼鼠症尚未痊癒,曾經有一隻小老鼠成為我家的常客,讓我徹夜難眠。
兒子在這個「家」安定了下來。隔年春天我們搬到另外一幢較大的公寓房子。
房子是六、七○年代的現代建築,有兩間寬敞的臥室,其中一間可以提供給朋友們過夜。光滑的磨石子地面,擦乾淨後便能夠反映出落地窗外的藍空,窗外陽台上花盆裡的細枝黃蟬時常有小鳥停腳,風大的時候,細枝孤單地瘋狂亂舞,沒一絲保留,讓人覺得她是如此沈醉大風的肆虐。
我常常靜靜地坐在窗前,觀看玻璃窗外的雲影浮動,尤其是當風吹起時,那種風與植物相遇時的戲劇效果,在我內心昇起幽默的快感,脆弱的樹與強烈的風,總是不停地在演戲,直到有一天樹枝被砰然折斷,在她奮鬥不斷的生命中默默接受考驗,一輩子在風前謙卑。
新家離教皇宮不遠,越過聖母院旁的修士公園就到了,每天早上我都去教皇宮廣場賣畫,這段日子,我的心繫於畫畫養家、打拳養生與養育兒子,是多麼如天賜之福。
「你願意接受身邊這位女子為妻,無論命運如何安排,都能相守一生,同甘共苦嗎?」「願意!」「妳願意與身邊的這位男子相守一生,同甘共苦,妳願意他成為妳的丈夫嗎?」「願意!」我曾經寫過一齣劇本,故事大略是敘述一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女子,在街頭巧遇一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男子,兩人一見鍾情後,決議舉行婚禮,以彰明兩人誓愛彼此的決心,於是兩人便分頭在街頭路角去尋找各自的主婚人、證婚人,以及假親戚、朋友,延請為婚禮的賓客。幾年後,我將這齣戲在自己的生命裡上演。陽光下的婚禮1986年8月6日,週六,上午10點半,我在亞維儂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