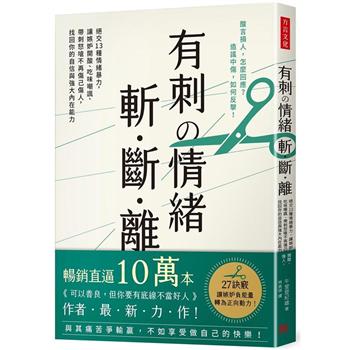哈維爾《獄中書》中文版序
貝嶺
這本書將會不朽。
卡夫卡曾經寫下過一段令人匪夷所思卻發人深省的話﹐他說:「受難是這個世界的積極因素﹐是的﹐它是這個世界和積極因素之間的唯一聯繫。」這段話用在哈維爾身上極其合適﹐是受難催生了這本書信集。
嚴肅﹑從容﹑凝重﹐那是絕對意志力下的精神勞作。有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字品質和深刻的思想質量。哈維爾的這些信件寫于1979年至1983年﹐在他43 歲到47歲的入獄期間。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幅畫面﹕一個中年男人﹐政治犯﹐一個純粹的作家型知識分子﹐性情中人。在暴政的刑罰下﹐他低著頭﹐沉思著﹐抽煙﹐ 目光專注﹐帶著我們已熟悉的哈維爾式微笑。
這本書共由一百四十多封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構成﹐在書中﹐哈維爾不是用對上帝的祈禱﹐而是用對自己的嚴苛要求﹐在一個只有內心生活而不能正常生活的地方 ﹐用在獄中唯一被允許的書寫行為──寫信﹐寫啊寫﹐對自已﹑對他人﹑對人類「存有」(being)的狀況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探究。
監獄和囚禁﹐作為一種無法迴避的人類現象和人類經驗﹐深刻反映著所處時代的人類生活和人類的精神狀況。正如哈維爾在寫給妻子的第17封信中所說﹕「只有監 獄環境才能成為人類普遍境遇的隱喻」。對於政治犯來說﹐監獄是你或早或晚總會踏入的一所考驗意志力的偉大學校﹐除非你瘋了﹐否則﹐它最終會使你學會沉思﹐ 並迫使你審視自已。
準確地說﹐不是哈維爾擔任捷克總統時期對當今世界或對捷克現狀予以審視及剖析的那些演講﹐也不盡是他在共產黨專制時代充滿異議勇氣和公民責任感的文字和行 動﹐而是他在監獄這一嚴酷環境下給妻子寫的這些信件﹐讓我讀出了哈維爾與絕大部份從事政治的人物微妙但卻是本質的不同。從性格上講﹐他有著被政治人物視為 致命缺陷的個性﹕不自信──他甚至從不掩飾這種不自信。這使得他不倦地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分析﹐如同他在第13封信中所說:「過多的反躬自省是我的『死腦 筋』的另一面。」然而﹐恰恰是這種不自信和由此而來的反躬自省﹐成為哈維爾個性中最為迷人﹑也最為珍貴的特質。就像哈維爾對自已的描述﹕「忠貞和不屈不撓 是我最重視的品格﹐時間一年年過去﹐我越來越看重這些。我並不是保守﹑喜歡現狀﹐而是尊重人的一致性和延續性。無論如何﹐我的所有劇本都圍繞著一致性與延 續性崩潰的主題打轉﹐我想絕非偶然。」
了解哈維爾最好的方式莫過於閱讀這些寫自獄中的信﹐許多信件中有著對身體狀況和個人心境極其細節化的描述﹐從茶對於身心益處的論述﹐到在獄中偶爾得以獨處 的興奮﹐從疾病──他在信中不斷描述的痔瘡──到牙痛﹑炎症或發燒等症狀對於他的折磨。他那一板一眼的生活要求﹐他對友人的掛念和對友情的緬懷﹐他那與生 俱來的腆﹐他感嘆著自己「基本上是一個社交型的人﹐而寫作是一件最孤獨的事……」﹐他那喜歡朋友﹑充滿對朋友的惦念﹑渴望和友人們相聚的天性﹐都使我們 如晤其人般地感受到一個真性情的哈維爾﹐一個看似隨和﹑實則固執──擇善固執的哈維爾﹔一個有著凡人的習性(如對瑣事的嘮嘮叨叨)﹑凡人的怪癖(如對小事 的一絲不□)﹑凡人的七情六欲﹑凡人的喜怒哀樂﹑乃至凡人的痼疾(痔瘡)的哈維爾。一個通過監獄生涯最終學會了怎樣和妻子交談的哈維爾﹔一個執著但絕不自 以為是的哈維爾﹔一個注重外表和他人觀感的哈維爾﹔一個即使在噩運中仍舊保持優雅和良好品味的哈維爾﹔一個將精神生活視為人生最高樂趣的哈維爾。
通過這些信件﹐我也深切感受到﹐對於一個身陷囹圄的人﹐家人的信件﹑妻子的探監﹑友人片言只語的問候﹐甚至輾轉抵達的遙遠喜訊﹐都不可或缺﹐這一切是多麼的重要。
從第37封信開始﹐也就是在他入獄一年之後﹐哈維爾開始有意識地寫「深思熟慮的信」﹐而不像之前那些雖然嚴謹和一絲不□﹐但是充滿對親人吹毛求疵的抱怨﹐ 指示奧爾嘉來探監時要帶什麼﹑要買什麼﹐羅列得清清楚楚。因為在獄中不能寫劇本﹐他只能對自己以往的劇作展開深入的思考﹐「我的所有劇本處理的都是人類身 份這個主題﹐以及意識到的危機狀態……」﹐他甚至警句式地強調他在思考“所有主題中最重要的主題﹕「身份與不朽」。他在隨後的許多信件中對戲劇形式﹑戲劇 觀念﹑劇場的意義﹑劇作家和劇場﹑劇場和觀眾的關係﹐以及他在不同的劇作中究竟想表達什麼﹐作了持續而專注的探討。
哈維爾也在信件中對他和神的關係作了深刻的論述﹐他在第41封信中曾說﹕「他有時是我的良心﹐有時是我的希冀﹐有時是我的自由﹐有時是世界之謎。……我的 上帝的另一個典型之處﹕他是一個等候的大師……」。哈維爾並不是一個教徒﹐但他也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在信中詳盡闡述了他的內在信仰﹐最重要的是﹐他對這 個他稱之為“秘密的永世的他”充滿了崇奉。哈維爾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深刻思辯寫下了這些思考。
他在囚禁後期所寫的信幾乎完全是他與現代哲學的一場虛擬對話﹐哈維爾曾在第108封信中大量使用哲學術語對人的存有進行了連篇累牘的表述﹐並且滔滔不絕﹐ 我在這封信的最後一段突然發現了這一切表達的潛背景﹐哈維爾說﹕「我終於熬過了這個獄中的聖誕節﹐我的憂鬱已經消失﹐我的肚子也漸漸大了。」
其實﹐他此刻對哲學式「存有」的思考﹐就是對他在牢獄中受難的“存有”現實的挑戰﹐這使他在45歲時戰勝了囚禁生活中那致命的憂鬱。他在這些用數字編碼的 ﹑看似可以無窮無盡寫下去的後期信件中孜孜以求地探討精神秩序﹑視界﹑存有秩序﹑存有的地平線等帶著我們所處時代深刻烙印的哲學概念﹐反復闡述著人的責任 ﹑人的信念及信仰的必要性和意義﹐其思想的純度之高﹑思路之嚴謹和思緒之縝密﹐令人震撼﹐不僅是人類受難史上﹑也是人類思想和人類精神進程中不朽的文獻。
我的建議是﹐將哈維爾的這本書信集放在床頭﹐就像在床頭擱放詩集﹐可蘭經或福音書一樣﹐每天在睡前讀上一頁或一封信﹐它可以成為我們精神的校正器﹐在狂躁或沮喪狀況下按時服用的「藥」。
我甚至冒昧地建議哈維爾先生﹐他二十年前寫出的這些獄中書信也應該作為他此時此刻「後總統生涯」中的床頭書﹐在他今天仍舊活躍的退休生涯中﹐或許可以通過重讀自己早年寫就的書信﹐重拾當年他在政治和文學那巨大的鴻溝間達至驚人平衡的偉大技藝。
書名﹕《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
作者﹕瓦茨拉夫‧哈維爾
譯者﹕王一梁等
出版﹕傾向出版社
(傾向版權所有 , 轉載或轉貼請注明出處)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1979.6~1983.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6 |
其他各國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1979.6~1983.2
《獄中書 -- 致妻子奧爾嘉》,蒐錄了哈維爾1980年代在捷克獄中寫給妻子的146 封書信。
正如貝嶺在中文版序中所說︰「了解哈維爾最好的方式莫過於閱讀這些寫獄中的信,許多信件中有著對身體狀況和個人心境極其細節化的細緻描述。他那一板 一眼的生活要求, 那種「死腦筋」般的哲學性思辯思路,他對友人的掛念和對友情的緬懷,他那與生俱來的靦腆,他感嘆著自己「基本上是一個社交型的人,而寫作是一件最孤獨的事..」,他那喜歡朋友、充滿對朋友的惦念、渴望和友人相聚的天性,都使我們如晤其人地感受到一個真性情的哈維爾,一個看似隨和、實則固執 ── 擇善固執的哈維爾。通過這些信件,我們將深切感受到,對於一個身陷囹圄的人,家人的信件、妻子的探監、友人片言隻語的問候,甚至輾轉抵達的遙遠喜訊,都不可或缺,這一切是多麼的重要。」 傾向持有全球中文版版權。
作者簡介: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世界舞台上的一位獨特政治人物,兼有詩人、劇作家、異議份子及思想家多重身分:捷克1989年底推翻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天鵝絨革命」之靈魂人物,曾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譯者簡介:
李永輝、張勇進、陳生洛、王一樑、張桂華 等
章節試閱
哈維爾《獄中書》中文版序
貝嶺
這本書將會不朽。
卡夫卡曾經寫下過一段令人匪夷所思卻發人深省的話﹐他說:「受難是這個世界的積極因素﹐是的﹐它是這個世界和積極因素之間的唯一聯繫。」這段話用在哈維爾身上極其合適﹐是受難催生了這本書信集。
嚴肅﹑從容﹑凝重﹐那是絕對意志力下的精神勞作。有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字品質和深刻的思想質量。哈維爾的這些信件寫于1979年至1983年﹐在他43 歲到47歲的入獄期間。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幅畫面﹕一個中年男人﹐政治犯﹐一個純粹的作家型知識分子﹐性情中人。在暴政...
貝嶺
這本書將會不朽。
卡夫卡曾經寫下過一段令人匪夷所思卻發人深省的話﹐他說:「受難是這個世界的積極因素﹐是的﹐它是這個世界和積極因素之間的唯一聯繫。」這段話用在哈維爾身上極其合適﹐是受難催生了這本書信集。
嚴肅﹑從容﹑凝重﹐那是絕對意志力下的精神勞作。有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字品質和深刻的思想質量。哈維爾的這些信件寫于1979年至1983年﹐在他43 歲到47歲的入獄期間。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幅畫面﹕一個中年男人﹐政治犯﹐一個純粹的作家型知識分子﹐性情中人。在暴政...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瓦茨拉夫‧哈維爾 譯者: 李永輝、張勇進、陳生洛、王一樑、張桂華
- 出版社: 傾向 出版日期:2011-12-18 ISBN/ISSN:978986856173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