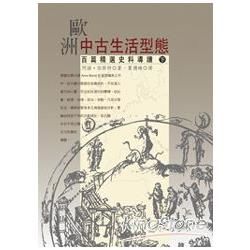作者後語
我們這樣理所當然地談論著中古,很容易會把這個名詞所背負的不佳聲譽置若罔聞、或是錯誤解讀。它並不像摩登、現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浪漫思潮那些字眼,是由一些想要凸顯其特色之人所作的自我見證;中古一詞的發明者們把它塑造成為與今日相對的另一種世界之化身:黑暗中古——這就是當時的狀況。佩脫拉克即為始作俑者;他把當代稱作是介乎成功的上古與熱盼的文藝復興之間,一個尚未跨越黑暗的過渡時期。這仍是中古形式的一種感受,畢竟這個時期從未把自身理解為歷史的中期階段,而是從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到最後審判日的重返之間的一個過渡;就如貝達,人人都把基督誕生之後的歲月都算成是他們的年代。在這個當下,切口還不深。羅馬的佔領與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雖然讓奧古斯丁和艾尼亞‧希爾菲歐驚惶失措,卻沒有讓他們感受到這就是一個歷史斷代的起點。貝達與奧利維可能會把公元2000年的人們看成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庫斯的尼可勞斯則期待這個世界將在十八世紀就告終結。直至我們現代,中古才被追認成為一個斷代。
因此現代人對於中古不斷有所爭議:這個斷代從未取決於起始與終結的年份,而是一直以這個自身無法劃清界線的時代之實際內容而定。如果我們必須把中古的定義加以事後追補,便應該抓住這個詞的現代根源,掌握住那種想要讓自己與這個條理不清、缺乏理智、尚不成熟的世界相互對照的願望。現代人對中古感到陌生之處,在十六世紀就已經由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人士針對他們的前代人批評過了。他們當時仍把中古定義為缺乏學養,憤而加以否定。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
這位信仰基督教的人文主義者輕視歷史的發展,因為對他來說,教會的那些生活型態仍是日日要求助的對象,就像一個來自晦澀過往的笨拙物體,擋住了通向未來的路徑。伊拉斯莫斯為基督教個人主義的自決而奮戰。就像西賽羅和奧古斯丁,他也零星利用生活型態這個詞語,亦即Vitae forma;在1501年發表的《基督教鬥士手冊》中,就拿它來指涉正派基督徒的教育,而按照他的觀點,就是向基督看齊。他轉而在所有的生活處境中面對同類,但是社會行為的外在俗套卻是他的眼中釘……
宗教界與學界早在中古時代就已是最為活躍與最富批判力的生活圈,協助大部分的人去動搖因襲的生活型態;這具有歷史的一貫性,就像伊拉斯莫斯和路德便是來自這些圈子的人,而成為瓦解中古生活型態的先鋒。在耶穌會和特倫多宗教會議的那個時代,天主教會把許多人文主義者與宗教改革家的要求收納進來,擺脫了許多中古的形式慣例,其幅度比現代教徒所知道的更大。現代人樂於把與教會相關的一切都以中古名之,而把兩者弄混了。就像大多數的教會規章一樣,教士這個詞源自上古的希臘,並且留存於中古;在教會史中,中古屬於一個虔誠的時代,而非教會的時代。中古只是偏重教會中的儀式,另外還伴隨著各種現象,如伊拉斯莫斯所忘記提及的本篤會修院學校,以及約翰尼特會的醫院;位階制度所帶來的虛榮感和愚昧的信賴,無疑也屬於這種伴隨現象。沉迷於信仰的修士住在迴廊曲折的修院裡——這在伊拉斯莫斯與伏爾泰之間的那段時期內,被斥之為黑暗中古的代表——只代表著一種特殊的團體形式,亦即教團,卻也真實地反映出一部份的中古,也就是生活型態中的專制。
在歐洲歷史的下一個回轉中,人們向遠方的藍天投射嚮往的目光,使中古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艾德蒙.柏克於1790年在倫敦寫下他的《法國革命之省思》;巴黎的革命份子於1789年十月六日羞辱法國王后瑪麗–安東妮特的消息,讓他深為震驚……
這位保守的政治學家誇張地描寫歷史的連續性,因為對他來說,革命具有破壞一切國家秩序維繫的危險。柏克把國家當成藝術品,為維護它而奮鬥。當生活型態這個詞自伊拉斯莫斯之後喪失其複數表列,柏克便不再言及這些生活型態,而是談到社會生活的各種行為方式,亦即 habits of life。這個字眼並非單單指社交而言,而是遠超過特魯瓦的克里斯提亞所指出的一切,甚至包括了歐洲的政府形式與憲法……
古代政體的辯護者們援引貴族–諸侯的生活型態,乃是合乎邏輯的,畢竟貴族和諸侯的生活圈早在中古時代就已經為了鞏固社會的行為方式而作了最多的付出。而且貴族之家能以三百年之久去形塑公眾的生活,比沒有生養兒女的宗教人士還要堅持不懈。就一人一地而言,人們完全可以把路易十四凡爾賽宮的宮廷社會稱為中古生活型態的外在極致。進行革命的市民把這種基於特權的生活以中古名之,並非沒有道理,而他們更愛用封建這個字眼來表示。這個字就如封建制度和貴族社會一般,有其中古的源頭;雖然如此,在革命之後,它並沒有像klerikal這個意指教會相關一切的字眼帶有貶意。畢竟,精打細算的市民就像1180年的倫敦市民一樣,無法放棄許多上流的行為方式;時至今日,在封建城堡改建的旅館內用餐,其滋味仍是比在正派市民所開設的餐廳裡來得好。當我們在社交領域中重視有教養的舉止和社交禮儀時,就代表我們身處柏克的那種傳統中。柏克忘記說明,中古的貴族與諸侯之所以能彬彬有禮,靠的是農夫與市民的勞動,才聽憑他們選擇優雅的社交;不過,信實和體面、濟弱扶傾與節慶歡樂,無疑都屬於這種生活型態。自柏克以降,直到今日,皆被讚揚為浪漫中古之代表的,就是位於堅固城堡中的尊貴騎士;他們另外也代表教團這種特別的團體型態,卻也真實地反映出一部份的中古,也就是生活型態中的恩典。
嘲諷與激情各自描繪中古的片面圖像,因為伊拉斯莫斯和柏克這些文人並未研究歷史,而是想要說明一個能獨立自主的基督徒,或是一個有身分層級意識的歐洲人應有的行為。就個別而言,他們的偏好有所扭曲;但就整體而言,他們仍準確描繪了中古的命脈。畢竟,中古的各種生活型態同樣能夠創造出充滿活力和具體的歷史。這段歷史主要關係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行為,而非人類概念的抽象運用。自此之後,重心業已轉移,因為個人和國家被抽象化,雖然仍是體現在人的身上,然而不再是一群,而是單一個體。從法國大革命之後,在精於計算者的世紀裡,業已徹底轉變。
在法國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抽象與客觀被建立起來了,而喪失對古今生活型態的興趣。這個現象值得注意,畢竟這段時期正是歷史研究的重要世紀,不但以特別的熱情轉向中古的研究,而且有最多的史料提供給廣大的讀者。這也是市民階層的世紀,他們有意識地培養其成功的生活型態,例如在1855年所嘲笑的畢德麥亞風格;當時的德國仍在陰涼處舒適地吃著醃包心菜,剩下的事情則交給上帝和國會來處理。然而實情正是如此:當國家與社會、社會與團體分道揚鑣,生活型態就成為私人之事;不論新舊,都無法對歷史再起積極作用。當現在與過往、世故與智慧相互脫節,歷史就不再是生活的導師,而只能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中古生活型態的遺緒安在,似乎成為這個時期內三位最受歡迎的歷史學家論證的題目。
古斯塔夫.弗萊塔克於1867年出版的《德國歷史圖像》一書中,根據所挑選、翻譯的史料,把中古描繪成市民階層的早期發展時代。弗萊塔克明知十八世紀的德國人仍有三分之二是農民,但是他不寫農民的社區、鄉間的風俗,甚至不提農村與城市的緊張關係。翦徑賊漢貝希特想要開始過著騎士般的生活,但注定會觸礁,畢竟未來將屬於市民與農民的聯盟,一起對抗貴族的剝削者。法國大革命把農民從封建的依附關係中拯救出來,並讓他們成為其國家中的自由公民;工業革命則帶來播種機與歌德的詩集,使他們擺脫技術、智識落後的困境。農民的生活型態並未衰亡,而是轉而融入市民的生活型態。……
在1860年,雅科伯‧布克哈特的《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為此提供了例證;對於現代的大型國家和其無上權力、經濟的生產幹勁和其忙碌操勞、城市的芸芸眾生和其個人孤寂,這位巴塞爾的市民滿腹狐疑。因此,他著手描寫這個發展的開端,也就是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如同藝術品的理性國家,以及從鄉間的生活圈過渡到文化人優雅的社交界、從懵懂孩童到個體的全然開展。在介乎諸侯、貴族和市民的平衡中,發展出自覺、俏皮、美善等各種型態的存在。然而這並非生活型態,而且布克哈特也沒有這樣加以稱呼;畢竟,日常的生活條件、農民的艱辛困苦,以及工業和資本經濟的起源,都被排除在外。
針對布克哈特的圖像,約翰.惠欽格這位荷蘭人則在1919年於《中古之秋》一書中補上了十四、十五世紀的勃艮第與法蘭西。他描繪了政治與經濟現實的深沉陰影;而且不同於布克哈特的是,對他而言,中古晚期並非預示著未來,而是走向著衰敗。他樂意稱呼這種衰敗為生活型態與精神型態;他在1941 年再度表述——這種感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伴隨著他——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歷史都不再具有可當做戲劇或繪畫來表現、或是能讓人牢記於心的型態。此乃當代的對照;而這種對照誘使惠欽格去尋找主要置身於繪畫和詩詞中的生活型態,並且理解成與混亂之現實相反的風格化手法。
弗萊塔克、布克哈特、惠欽格這三人的書可以為至今知識界的中古圖像定調,因為縱使研究的當下與描述的對象皆有所差異,卻把他們那個世紀對時間與群體的基本概念帶進了中古。他們都各自觀察了中古時代德意志、義大利,以及法蘭西的核心地區,也就是說與現代的民族國家接軌;他們將這些邦盟投入發展的洪流中觀察,也就是在詢問:我們的過往提供了多少他們尚未擁有、以及我們不再擁有的未來?這種國家和年代的窄化,讓中古的生活型態於研究時就被扼殺,畢竟這是以截然不同的時間感與群體建構作為基礎。
法國人馬克.布洛克於1939/ 40年間在他的《封建社會》一書中,首先把這個基礎發掘了出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反抗軍與德國人戰鬥、民族國家與發展計畫破滅的影響下,布洛克重新把歷史理解為有關當代人類共同生活的一門科學。他粉碎了歷史應按照年代順序編排的主導思想。他引述了一句似乎但丁也會援引的阿拉伯諺語:「人皆類乎當代,而勝於類乎其父。」在時間上,他為歷史片段的挑選劃定了嚴格的界限,幾乎沒有把目光投向九世紀以前,而且對十三世紀以後的歷史只有驚鴻一□。相反的是,他果斷地把空間的視野向整個歐洲擴展,甚至與中古的日本進行類型上的比較。由於布洛克想要研究人類如何在他們的生存條件與生活圈中共處,他容忍在歷史的同時性之中匯入許多不同時期發生的事情。對他而言,生活條件關係到壽命、疾病、人口密度,以及行旅的速度;他也注意到精神狀態、時間感、情緒,以及之於習俗、文字的關係。然而布洛克只重視貴族這個生活圈,認為這是唯一具有完整性的社會階級。他們已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所有的團體都與貴族脫不了關係。尤其是宗教人士還擁有許多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農民並非同質性的團體,而市民的同質性則是後來才形成的。
較新的中古結構分析已證實,布洛克的時間範圍過於狹隘,而且讓自己過於片面地侷限於貴族。鄂圖.波納在1958年指出,歐洲的社會體制已創立於中古早期,而主要部分直到十八世紀都還保持著完整無缺。貴族雖然參與建構,卻從未僅以一己之力加以控制;尤其是農民與諸侯,讓社會體制保持了平衡。赫伯特.古德曼則在1965年揭露宗教與思想運動的力度;它們從一開始就出於堅定的渴望而催迫著中古,讓它超越自身,而向現代挺進。同時,宗教界與學界人士操縱著文字,只不過其中也有許多門外漢;他們也透過拜占庭和伊斯蘭世界的當代人士,突顯中古的歐洲。因此,研究的領域必須在時間、空間,以及社會方面加以擴展,超過布洛克的所願。同時,人們不應該以力學的思維模式來探討,畢竟歷史的時光並非一種動力學的運轉,而人類的團體也並非一種靜力學的結構。就像布洛克所做的,只有在抽象概念於人類的應對進退中得到相當的回應,這些概念才保有其具體意涵。
對此,我堅持從生物學的行為研究中求得人類生活型態的詮釋模型——包括面對今日的嘗試。有時,人類的行為似乎類似於植物和動物,讓自己適應著環境;然而在中古,人類的環境就是他人,其生活型態並不能被簡化為刺激與反應。他們的基本姿勢就是交談;我們這些證詞中的對話領域如此廣泛,並非意外之事。於相互交談間,社會行為的規範被訓練得駕輕就熟,並且受到檢驗;歷史就以這種方式直接締造,既非在中古之前,也非在中古之後。我不會宣稱生活型態構成整個中古社會;我只是堅持,它使這個整體的關聯清晰可辨。我也並不認為生活型態會決定一切時空下的人類歷史;然而我相信,它讓歷史的成功條件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