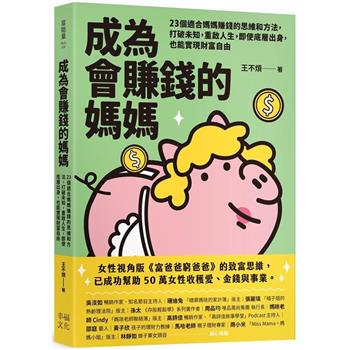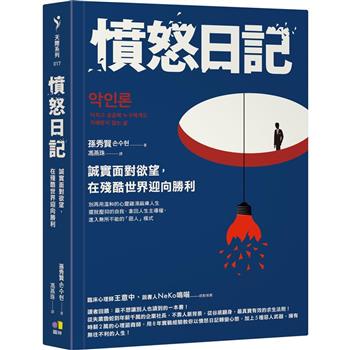名人推薦:
在這部經典裡,作者討論演員於詮釋角色過程中常會遇到的關卡,以及突破瓶頸的一一步驟。有別於舊派「視野向內」的方式,唐諾倫建議演員「視野向外」,從角色的立場尋找具體目標。它這不僅是一本演員手冊,且關乎人的心理狀態:演員面對舞台的關卡其實就是一般人面對人生的關卡。
──紀蔚然 知名劇作家,台大戲劇系教授
唐諾倫將帶領你越過重重的表演關卡,教導你如何放棄內在的「專注」,「關注」於外在的「標靶」,了解自己所面臨的「賭注」;如何透過角色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變成角色!對表演來說,「演員與標靶」書中所提示的「標靶」,非常紮實,非常管用。許多曾經有點矇有點虛的表演,突然醒覺,不但看清那會兒為什麼虛為什麼矇,也悟出該怎麼調怎麼作。
──金士傑 國寶級演員,北藝大戲劇系副教授
『演員與標靶』以最靠近表演實務的角度出發,描繪了戲劇表演者內外在狀態與處境,並有系統地提供對應的思考方式。具備豐富導、表演及教學經驗的馬汀尼教授選擇把這本書引介給華語世界,等於給了關注戲劇表演的人一件神兵利器,也讓我們不致於困在「雖然這是個舊世界,但許多東西都還沒有命名,想要述說還得用手去指…」的窘境中。我則暗自慶幸這書當年尚未寫就,否則被這種份量的書擲在腦門上,可會讓人暈上好些時日。
──戴立忍 知名演員、導演
相信每個演員探索表演的過程,總會遇到許多瓶頸和質疑,解決了一個問題,然後又得面對新生出來的矛盾,來回在顛覆與重整之間,時而自信時而挫折,手忙腳亂的程度跟搬家後無法決定傢俱該如何擺置一般。這本書很實際地提出了表演者在不同進程必須面對思考的問題,並且用淺顯的論說釐清困擾已久的迷知。對於「我這輩子並不打算當演員」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就像一扇窗,打開它,就可以看見一個你不曾看見過的演員的內心世界。
──桂綸鎂 知名演員
我大學時期的表演啟蒙老師——潘妮‧歐文女士(Penny Owen)曾經對我們說:「劇場是一個探索人性的地方。」經過這十多年來經年累月的劇場表演訓練後,我更是深切地體認到了她這句至理名言。表演訓練,除了讓我越來越瞭解自己、覺察自己身心靈上的優劣勢之外,「察言觀色」也已經成為我日常生活中的本能,由於對周遭人的行為舉止以同理心出發的「職業病」,我甚至還常常能像半仙一般準確預知他人未來的選擇與反應。
這本書的問世,對於「探索人性」有興趣的讀者,同樣是一個彌足珍貴的禮物。如果這本書對於演員來說是一本難得的練功書,那麼對所有的人來說,這又何嘗不是一本洞察人情的人間工具書呢?
──姚坤君 知名劇場演員
專書介紹: http://soundspacestudio.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