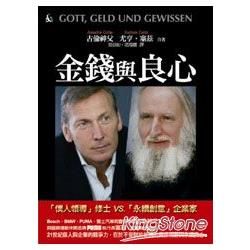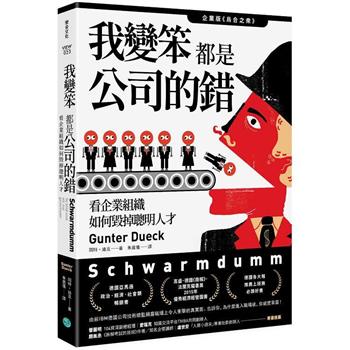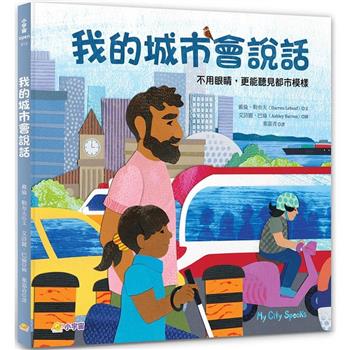第一章 永續性
主筆:塞茲
關於人與恐龍
一億五千萬年前!在未來的一億五千萬年的時間裡?就在最近我參觀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時,腦海裡不自覺地對比了這長得令人難以想像的時間。在館裡所展示的恐龍骨骸旁的牌子上,向參觀者說明了這個物種已經在約一億五千萬年前絕種了。
我問自己,在未來的一億五千萬年裡是否還會有生物存在?如果有,他們會怎麼描述我們呢?他們在證明我們存在過的基礎上,會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呢?——他們會問,有多少在21世紀仍為人所熟知的物種已經絕種了嗎?我們也有可能就屬於那已經滅絕的物種?若只從基因學的觀點來看,未來那無疑是已經高度發展的聰明的生命形式會跟我們很像嗎?我們被他們看作是讓生命之船翻覆的那個麻煩的物種嗎?或者被認為是最後終於重新恢復理智,還能用力將舵轉向的時代?
這些問題的答案一定也取決於我們現今這個世代做了什麼。這要看我們在21世紀的二〇年代,對一〇年代那些怵目驚心的數據如何反應。我想起了以下的這些記錄;那來自一部紀錄片《Home——搶救家園計畫》,這部影片是亞祖‧貝彤(Yann Artrus Betrand)出於對地球及對這星球上居民的關懷之情,在公元2009年所拍攝完成的。由Puma佔多數股份的法國PPR集團出資贊助這部紀錄片的拍攝,且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大約兩億人看過這部影片。
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消耗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資源。
全世界的軍備支出比發展援助支出還多出十二倍之多。
每一天有5000人因為喝了被污染的飲用水而死亡。
有十億人缺乏乾淨的飲用水。
約有將近十億人飽受飢餓之苦。
百分之四十的可耕地長期遭到破壞。
每年有一千三百萬公頃的森林消失。
四分之一的哺乳類動物、八分之一的鳥類以及三分之一的兩棲類瀕臨絕種。
現今物種絕種的速度進行得比因自然的進化而絕種的速度快上一千倍。
四分之三的漁場已經過度開發,不是過度捕撈就是魚量急遽減少。
南北極的冰冠已經比四十年前薄了百分之四十。
因為生活空間遭受氣候改變的影響而必須遷移的人口,可能在2050年時增加到至少兩億人之多。
這些只是少數幾個指標,有可能未來的生命形式會根據這些指標問道:「明明知道再這樣下去就是自殺了,為什麼他們不採取些措施來防止呢?」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那些恐龍並無法阻止們自己絕種,也無法預知會發生這樣的事。相反地,未來的生命形式想必可以確定,人類這個物種列出了上述的那些數據,並且將之公諸於世——但卻沒有即時採取行動,挽救自己免遭滅亡。
若有一位從遙遠的銀河系來的觀察家來研究人類,難道他不會發出疑問:為什麼人類不停止對這個星球所做的那些使自己深陷死亡威脅的剝削行為呢?這個問題雖然很難回答,但或許休摩(Ed Hume)在他的一齣關於核戰的電視劇「那日過後」(The Day After)給了我們一個答案:我們當中很多人都生活得很像他們根本就不願意承認有發生這些事。我們人或許基本上對死亡也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我們經常都是等到我們自己本身或是我們的親朋好友突然面臨死亡時,才會去思考死後的生命到底會是什麼樣子;才會打電話給我們的親人;才會想起我們的信仰根源或是寫下遺囑。就像經濟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譯註: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與政治理論家)所說的,比起痛苦我們更喜歡感覺到快樂。電影導演伍迪艾倫也確信:「比起我自己的葬禮,我更喜歡別人的。」
雖然如此,我們人類也很清楚,我們的文明正處於危險之中。人口爆炸、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南北經濟落差、區域性的饑荒、戰爭、地下資源的過度開採以及生物圈遭受嚴重破壞,這些都是人類遭受重擊、無力回天的跡象。
諷刺的是,人類這個致力於去收集各種資料的物種非常清楚知道這些危機。如果我們因為科學家和對政府及國會施壓的團體對於預測、數據及對這些數據的闡釋有所爭議,就一直枯等下去,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專家們的意見是從來不會一致的。我們的環境處於危險之中,現在已經到了我們該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未來不斷地會有新的發現,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地調整我們所採取的措施。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上,人們會使用嘗試錯誤的方法(Trial and Error)。在環境保護方面,我們也必須認真負責地容許用這樣的方法,當某個地方發生變化,就要想辦法改善。重要的是,在已經獲得一些正面成果的地方要特別採取一些措施,從那裡開始著手進行。
為什麼我們面對所有議題最終的這個問題時,並沒有將其列在第一順位竭盡心力去處理呢?不管原因為何,至少近幾年來已經掀起一波浪潮,喚醒人們那些遺忘的記憶。對永續性這個觀念的思索就是其中之一:有很多人、環境保護的先鋒和集團已經察覺到,他們必須要保存,更確切地說,必須要增加有價值的資源和社會成果。
將眼光轉向前看
「永續性」被歸為一種新的範例——新到這世上大部分企業的作法至今仍與其背道而馳。關於這個語詞的意思一直還是引起許多的討論。
「永續性」的觀念可以應用在生活中的許多領域;例如:在經濟、社會方面、在與環境相關的及在政治方面的領域。它的意思一直都是要求人們要採取一些作法,而且是長期性的維護,而非短期性的措施,也就是要將那些有價值的資源和成果保存到未來。而最近當人們在積極討論這個觀念時,對永續性的要求首先指的都是在環境保護的領域,目標是要為我們的後代子孫保存大自然與環境。
對我個人而言,在經濟、環境保護和社會方面的永續性這個議題關係到的並不是可以無限制地做我們在做的事。我認為「永續性」的意思其實是按照一種方式來轉變某些事物,目的是讓這世界能看起來比以前更好。
但事實上,「永續性」的計畫也是一種回歸到北美和其他地區古老民族和原住民族群意識的作法,這些族群現今自稱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舉例來說,根據出身美國紐約州的北美印第安人萊恩斯酋長(Chief Oren Lyons)的說法,去思考他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將會對他們之後的四個世代子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樣的問題,對有像他這樣出身背景的人來說是很平常的事。他們同樣也會自問,這些決定將會對整個更大的生態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對他們來說,永續性並不是一個選項,而單純是大自然能正常運作的方式。整個大自然是為了要長久存在而設計的——死了的事物回歸塵土,轉變成未來生物的一部分。樹葉發芽、長大、變色、掉落,肥沃了土地,之後下一個植物生長週期的一部分。只是後來的人類創造了一些東西,污染了水、空氣和土地這些最基本的自然物質,消耗了資源,瓦解了生命循環的和諧,阻礙了自然的進化。
我們已經不再跟有機的反應過程一致了,這樣的認識興起了許多群眾運動,如自然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以及前述的永續性運動。有許多人擷取了如美洲原住民這些古老民族的智慧。
幸運的是,在所有的文化裡都有預言者,他們會提醒我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彼此連結的。在西方社會裡,超驗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努力不懈地寫下自然法則的意義。博物學家繆爾(John Muir)察覺到:「如果人處於大自然的任何一個角落,就會發覺,他跟這世上所有的一切是有所連結的。」而在2009年四月,自然研究學家洪博(Alexander von Humboldt)逝世一百五十週年時,《非洲時代》雜誌(The African Times)寫道:「身為一個科學家和研究學者,他是(西方世界)第一個注意到這世界是一個整體的作家:他發現這世界各方面都是彼此連結、環環相扣的,且生態學和永續性是我們這個現代世界要存活的基本議題。」
還有很多人——從撰寫《整全與演化》(Holismus und Evolution)的史馬茲將軍(Jan C. Smuts)到創立蓋亞理論(Gaia Theorie,譯註:「蓋亞」在希臘文中的意思是大地,蓋亞理論主張大自然的生息替換自有定則,將地球系統是為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整體)的英國科學家洛夫洛克(J. Lovelock)——指出了一種整全的思考方式的意義,甚至認為這個地球是活的。永續經營是嘗試恢復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而這種和諧關係是科學界的先知和原住民族的領導者長久以來所大聲疾呼的。
既是建築師也是設計師的麥多諾(William McDonough)在1991年站在傑弗遜紀念堂的圓形大廳發表了一份新的宣言:那並不是一份新的獨立宣言,而是一份彼此依存的宣言。美國暢銷書作家霍肯(Paul Hawken)對他大加讚揚。麥多諾也像總統華勒士(Henry Wallace)一樣,強調一份彼此依存的宣言可能可以教導及指引人民,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好的國家、更好的區域和更好的世界共同體。霍肯說明:經濟上的獨立和他們發展上的並存應該要被揚棄,而以經濟、環境和社會彼此之間的所有元素是互相影響的意識取而代之。對他而言,永續發展也包含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它會顧慮到,經濟方面的近部會對大自然與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提出彼此依存主張的霍肯、麥多諾和華勒士並非異數。在古老的宗教文獻中早已談及「所有生命的一致性」;中古世紀的思想家,如薩爾茲伯利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思考的「存在的巨大鏈結」模型,這個模型指的就是在一個完整的系統裡,這個社會的所有部分共同發揮作用,就像一個人的身體裡的各個器官一樣。
這個互相依存的現代性眼光呈現在洛夫洛克的蓋亞理論和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主張;蓋亞理論將地球理解為一個生命體,而德日進則是從這個合一的世界超越個別的國家,且由此產生一種持續發展的人性意識。
羅素(Peter Russel)的著作《全球腦》(The Global Brain)、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口號和出自福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地球號太空船」觀點都是針對使得地球和它的住民能發揮作用的有機和不可分的反應過程的比喻。甚至還有哲學家,如兩千三百多年前伊索克拉提斯(Isokrates)或是至今仍十分著名的康德(Immanuel Kant),他們將社會與全球發展過程的共同作用,與人類身體的功能發揮作對比。許多研究學者在微觀和巨觀的層面上,針對差異性極大的生命型態,公開了有機的模式。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的科學家威示肯(John Waskom)、宇宙再進化研究專家傑尼(Hans Jenny)、哲學家布朗(David Brown)和作家布萊爾(Lawrence Blair)就是其中幾位。
儘管是市場經濟,也要合作
如果我們的政府和跨國企業集團接受了彼此依存這個看法的意義,並且堅持不懈地去付諸實行,那將會發生什麼事呢?在德國,我們應該可以從社會的市場經濟過渡到永續的市場經濟,除了社會的利益之外,更加關心環境的重要性。在許多國家和企業集團,我們應該要進展成不只是尋求如何由紅翻「黑」,得到利潤,而是也要成為「綠色」國家和「綠色」企業。我們終究也沒有遲疑,投資了數千億去挽救全世界的財政體系及希臘的財政,使歐洲共同體得以穩定。如果我們也花費同樣多的錢在挽救我們地球,我們可以做多少事呢?在產生了這麼多令人緊張的環境問題之後,這個假設為什麼在今天還是不能成為一個常見、可行的目標呢?
我認為,一個全面性的假設在今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不管是金融界菁英,還是一個政黨,或是一個科學思想家,都無法對所有的問題給出答案。因此,那些記得過往的歷史中原有的解答的人,例如,那些原始民族的耆老、智者、偉大世界宗教的代言人或是人類早期歷史中的生態專家們所得到的結論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共同發起必要的,且是在各個層面的改變,已防止「人類恐龍」時代的來臨。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9年的聖誕子夜彌撒講道中說:「一個作夢的人和警醒的人之間的區別,就在於作夢的人處在一個單獨的世界中,與他的自我關在那個夢的世界裡。那個世界就只是他的世界,與其他人並沒有連結。警醒意味著:從那個自我的世界裡走出來,進入大家共有的實境中,進入那唯一能使我們合一的真理之中。…這世界上的衝突、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都是由於我們把自己關在自己的私利與意見中,關在小小的個人世界裡。不管是團體或是個人的自私心態,都會把我們囚禁在我們的利益與想望之中,這些都違反真理,也使我們彼此分裂。」
由於意識到促使大家去認識全世界彼此依存有多麼重要,我們在PUMA企業裡發起一種Puma使命感,重視我們身為人與做為一個企業與我們全球這個現存物種的大家庭之間的關係。第一步就是促進與他人的對話,接著是從他們身上得到激勵與啟發。
從世界的中心出發
「鳳宮劫美錄」(Camelot)是根據亞瑟王的傳奇故事編寫而成的音樂劇。作者雷爾納(Alan Jay Lerner)和洛依(Frederick Loewe)在這齣劇中頗富詩意地改寫了魔法師教育亞瑟的故事。梅林在教導亞瑟每一個課題的時候,都會將他變成一種不一樣的動物。有一天梅林將年少的亞瑟變成了一隻鳥,亞瑟毫不費力地將在天空中飛了起來。當他變回人的時候,他的老師問他學到了什麼。亞瑟回答:「我從那高高的天上學到了,在那裡是沒有界限的,沒有城牆、沒有圍籬。」觀眾們從劇的這個段落感受到,亞瑟就像一個太空人或像一個飛行員一樣,因為高度和靈活度的提高,看事情的方式也完全改變。在我看來,為了讓這個世界能夠回歸到他最原本的生態平衡的狀態,這樣的一種看事情的方式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能用像鳥的眼光來看一切的事物,我們就能夠設想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會多了更多的互助合作,少了不必要的對立競爭;會更加地以整體,而非以小地區為依據來做考量;會對整個變化過程的維護比對可以替換的個別的小部分來得感興趣。
這個時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故事,是居住在南美哥倫比亞的聖瑪爾塔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的科吉人(Kogi)的故事。根據BBC的紀錄片《來自世界的中心——長兄警言》(From the Heart of the World:The Eldern Brothers’ Warning),科吉這個原住民族在他們的族人被歐洲殖民南美洲的入侵者凌辱與殺害時,移居至寒冷的高山上。因此,科吉族在四百年前西班牙佔領的那段期間的傳說,就都集中發生在內華達山最高的那些地方。這段故事非常引人入勝,因為跟絕大部分民族不一樣的地方是,科吉人可以離群索居,又能保存他們原始的文化。當他們在1990年決定打破沉默,向「弟弟」說話,這或許是他們歷史上最令人訝異的一件事了。「弟弟」是他們對那些不請自來,且將他們趕走的歐洲訪客的稱呼。在與世隔絕了數百年之後,「兄長」,也就是科吉族人,邀請BBC電視台的一個工作團隊去訪問,因為那是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向世人傳達的時候了。這對那些長久以來想接觸科吉人,卻不得其門而入的人類學者和記者們來說,自然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故事,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為什麼科吉人要打破沉默?他們要說些什麼呢?數十年來,他們在高山頂附近觀察到在他們周圍天然的植被開始變得愈來愈稀疏,也愈來愈不青翠了。他們斷言,如果山頂變得貧瘠,海拔低一些地方的植被可能會消失。他們控訴,有一間發電廠就建在他們的聖地上,而且他們非常清楚在他們的周遭發生的那些採礦、砍伐森林和耗盡其他資源的事。下面節錄一段他們對「弟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其餘的世界」——所發出的警告:「弟弟啊,停止吧!你已經拿走那麼多東西了。我們需要水,才能活下去。母親告訴我們,要如何真正地生活,要如何好好地思考。我們一直都還在這裡,完全沒有忘記。土地漸漸衰竭,喪失了它們的力量,因為人們從它們身上奪走太多的石油、煤礦和太多的礦物了。弟弟說:『喂,我在這裡!關於宇宙的事,我懂很多!』但這些知識卻是學習如何摧毀這個世界,摧毀所有的一切,摧毀整個人類……母親在受苦……她病了。如果我們砍斷我們的手臂,我們就無法工作;如果我們砍斷我們的腿,我們就無法行走。母親現在也就是在遭受這樣的痛苦,她在受苦,什麼都沒有了。弟弟啊,他明白他做了什麼樣的事嗎?」
這份兄長的警言最特跌的地方在於,科吉人並非是受到危害的四隻腳的動物或是兩隻翅膀的鳥類。他們跟我們一樣,是人。他們察覺到,如果「弟弟再不改變他的習慣跟行為方式」的話,「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這個訊息的另一種解讀早就已經在科學的基礎上被提出來了,例如: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羅馬俱樂部,以及在東京、哥本哈根和無數的國際會議上。但差別在於,科吉人親身經歷到,人類為何正身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
公元2009年,在阿拉斯加舉行了一次大型的原住民族首領會議。在會中,許多部族將他們所觀察到的現象加以比較,並且確定:不久的將來,將不再只是白頭鷹和鯨的存活受到威脅,受到威脅的將會是人類全體。再過不久,這些部族可能就無法在再吃到他們世世代代所獵得的動物了。許多居住在河岸邊的部族愈來愈常受到淹水之苦。有的則失去他們早期得以在其中狩獵及得到保護的森林。許多人身患隨著文明最終階段而產生的慢性疾病。
在《來自世界的中心——長兄警言》的結尾,代表科吉族人發言的耆老也向我們只出了一道希望之光,他說:「這世界不一定會結束——如果我們立刻做必要的改變。」
決定權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從日益增加的轉變強度來看,悲觀是太晚了——而像恐龍一樣滅絕,卻又太早。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金錢與良心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經營管理 |
$ 270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金錢與良心
當代最知名的本篤會修士與頂尖企業管理人,針對目前全球化的世界裡,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卻苦思難解的基本議題,進行充滿智慧與創意的對話:成功與責任、經濟與幸福、文化與價值,也就是關於價值、金錢與良心。他們對世界都抱持著願景,希望人類能在公平正義的價值裡獲得幸福,建立一個符合生命尊嚴與價值的世界。他們也正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此而努力。他們也深信,如果每個人都能用這樣的終極價值來做個人事業與生涯規劃的基本信念,你就能看見你個人的成就同時也是人類幸福之路的地磚。
Bosch,BMW,PUMA,賓士汽車的靈性導師-古倫神父與國際運動休閒品牌PUMA執行長塞茲,從實務中證明:21世紀個人與企業的競爭力,在於不受制於逆境的責任視野與永續良心
作者簡介:
古倫神父(Anselm Grün)
1945年生於德國Junkershausen,自19歲起就是聖本篤修會位於烏茲堡的「Münsterschwarzach修道院」的修士,之後獲得神學博士、哲學與企管碩士。已在聖本篤修道院擔任經營主管30年之久,他是德國Münsterschwarzach聖本篤修道院的經濟管理人,負責管理修道院所屬二十多家公司行號與三百多名員工。他並且負責該修道院對外開設的人性領導課程。他的著作超過三百多種,目前已有30幾國的語言翻譯,所有銷售冊數已高達1800萬冊。是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宗教與心靈作家,也屬於當代最重要的基督宗教作家之一。中文翻譯的著作包括:《天天經歷復活喜悅》、《活像耶穌》、《活出十誡的真自由》、《領導就是喚醒生命》、《家庭是人生的冒險》、《擁抱老年心生活》、《歡慶一個新的開始》、《32堂聖經人物的生命課程》、《受難、愛與新生》、《生命終點的盼望》(以上皆由南與北文化出版社出版)。
古倫神父另一項被歐洲神職與諮商專業人士肯定的專長就是「心靈關顧者的靈修輔導」。古倫神父20年的神職人員輔導經驗,不但是對第一線的心靈關顧者有心靈上的滋養,對於心靈關顧的領域也有造就啟發的效果。
尤亨‧塞茲(Jochen Zeitz)
擔任德國國際運動休閒品牌PUMA公司十七年的董事長,目前是PUMA的執行長。他以30歲任PUMA董事長之初,成為當時德國企業界最年輕的董事長,靠著堅定的毅力並結合企業倫理的永續性的美學創意,將PUMA從破產邊緣重建為目前世界三大運動休閒品牌之一,可以說是全球運動休閒品牌界的賈柏斯。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永續性
主筆:塞茲
關於人與恐龍
一億五千萬年前!在未來的一億五千萬年的時間裡?就在最近我參觀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時,腦海裡不自覺地對比了這長得令人難以想像的時間。在館裡所展示的恐龍骨骸旁的牌子上,向參觀者說明了這個物種已經在約一億五千萬年前絕種了。
我問自己,在未來的一億五千萬年裡是否還會有生物存在?如果有,他們會怎麼描述我們呢?他們在證明我們存在過的基礎上,會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呢?——他們會問,有多少在21世紀仍為人所熟知的物種已經絕種了嗎?我們也有可能就屬於那已經滅絕的物種?若只從基因學...
主筆:塞茲
關於人與恐龍
一億五千萬年前!在未來的一億五千萬年的時間裡?就在最近我參觀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時,腦海裡不自覺地對比了這長得令人難以想像的時間。在館裡所展示的恐龍骨骸旁的牌子上,向參觀者說明了這個物種已經在約一億五千萬年前絕種了。
我問自己,在未來的一億五千萬年裡是否還會有生物存在?如果有,他們會怎麼描述我們呢?他們在證明我們存在過的基礎上,會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呢?——他們會問,有多少在21世紀仍為人所熟知的物種已經絕種了嗎?我們也有可能就屬於那已經滅絕的物種?若只從基因學...
»看全部
作者序
前言
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親愛的讀者,
感謝您們認同我們的想法,並且對我們想法上的交流感興趣,想要繼續閱讀下去。我們的身分一個是修士,一個是高階經理人,我們會互相討論、交換意見,這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這樣的對話是開始於兩年前在紐倫堡舉行的一次公開討論會,在那次的討論會中,我們面對面坐著,並且提出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像是:「價值」在經濟中還有立足之地嗎?在一位修士身上可以發現多少經理人的角色?一位經理人需要顧及到多少層面?而金錢與利潤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當時我們並無法針對這所有的問題進...
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親愛的讀者,
感謝您們認同我們的想法,並且對我們想法上的交流感興趣,想要繼續閱讀下去。我們的身分一個是修士,一個是高階經理人,我們會互相討論、交換意見,這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這樣的對話是開始於兩年前在紐倫堡舉行的一次公開討論會,在那次的討論會中,我們面對面坐著,並且提出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像是:「價值」在經濟中還有立足之地嗎?在一位修士身上可以發現多少經理人的角色?一位經理人需要顧及到多少層面?而金錢與利潤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當時我們並無法針對這所有的問題進...
»看全部
目錄
前言───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永續性與企業責任───塞茲
尊嚴的人與生活的環境───古倫神父
企業的經濟任務───塞茲
企業與人類福祉───古倫神父
文化的深度影響──塞茲
價值創造利潤──古倫神父
符合倫理的行動───塞茲
訓練與教育──古倫神父
成就與幸福──塞茲
長處與弱點──古倫神父
企業責任───塞茲
個人意識───古倫神父
永續性與企業責任───塞茲
尊嚴的人與生活的環境───古倫神父
企業的經濟任務───塞茲
企業與人類福祉───古倫神父
文化的深度影響──塞茲
價值創造利潤──古倫神父
符合倫理的行動───塞茲
訓練與教育──古倫神父
成就與幸福──塞茲
長處與弱點──古倫神父
企業責任───塞茲
個人意識───古倫神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古倫神父、尤亨‧塞茲 譯者: 吳信如、范瑞薇
- 出版社: 南與北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1-15 ISBN/ISSN:97898686633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類別: 中文書> 商業> 經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