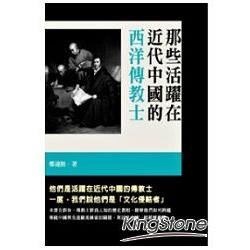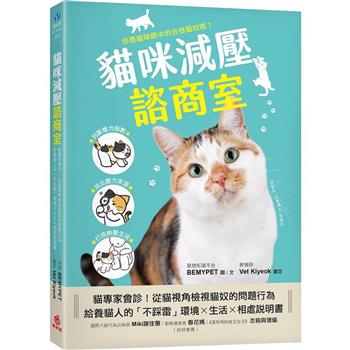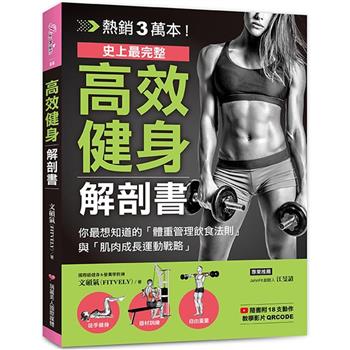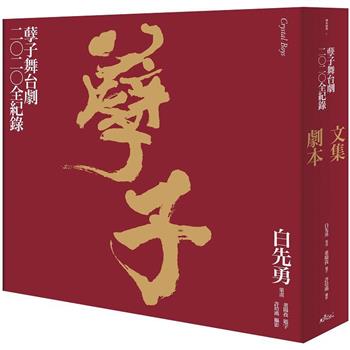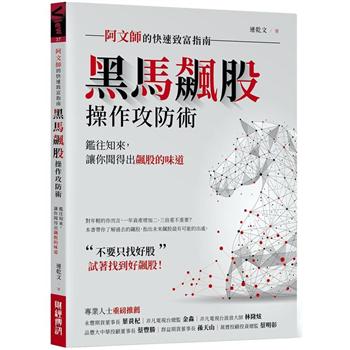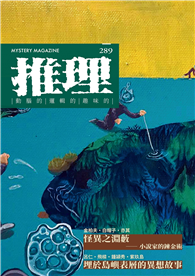本書告訴你,傳教士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瞭解他們如何跨越傳統中國與先進歐美國家的隔閡,與近代中國一起經歷劇變。 隨著時光將情緒化的泥沙沉澱,我們發現傳教士們在近代中國幹過很多有益的事情,除了傳播基督教之外,他們搞慈善、開醫院、辦教育、辦報紙、翻譯西學書籍,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文明的傳播者。 因此,我們不可簡單地把西洋傳教士來華視為純宗教活動,他們的活動始終與政治、經濟同步並進。他們還與中國名流交往,交往中發生過許多趣事,這些細節為我們解讀那段歷史提供了可感可觸的鮮活場景。 他們還對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他們中的某些人還成了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 他們當然也有他們的偏見和局限,但這些不應該成為我們有意「遮罩」他們的理由。 且讓我們正視他們,正視一段近代史中不該忽略的篇章……
作者簡介
鄭連根
資深傳媒人,文史學者。畢業於中國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國古代小說名句賞析》、《濟南老街老巷》(與張繼平合著)、《塵埃尚未落定》、《前事今識》(繁體字版)、《故紙眉批》、《新聞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