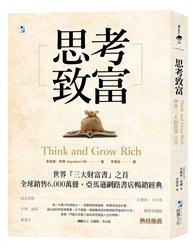作者簡介
零雨
臺北人,臺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碩士。
1991年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現代詩》主編,並為《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
1993年她以〈特技家族〉一詩,獲得年度詩獎。2004年她應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以及2011年由北島主持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任教於宜蘭大學。
1983年開始現代詩創作
1990年出版《城的連作》
1992年出版《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
1996年出版《特技家族》
1999年出版《木冬詠歌集》
2006年出版《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
2010年出版《我正前往你》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2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序
自序
樹,蟲子,方塊字
A在冬天和春天交界的地方出生,那裏有一棵樹。
他摘了一個果子放進嘴裏。河水在流動。他往前爬。
一些蟲子張開細小的翅膀。周圍會飛的還有雲,還有冰霜和雨。
風也飛得很快。飛過河灣的時候,漣漪向四方漫開。涮洗著一些草的根莖。
一個人走過來,牽著A的手。他們走進一個深山的村落,更深處有一個家。這是你的兄弟。你的姊妹。父母。祖父母。你的親族。散佈在這座山,那座山。你的耳朵,你的眼睛,你的鼻子,嘴巴,身體所及之處。
A向前迎接,幾個遠處的人影,舉著火把,從最高的那座山下來。帶來一些熱氣、搖晃,和有陰影的圖象。大家圍住他們,寒暄、喝茶。大廳的桌子擺開了,木頭椅條,馬上坐滿一些人。棋子出現了,獵物出現了。女人重新撥開灰燼,柴火重新入灶,熱食出現了。
煙霧在燈泡下繞著。
綁在桌腳的小猴子不見了。
有人吃著猴腦。
被蛇叮過的大腿,用牛糞敷著。
A站在廳堂大鐘的前面。此時時間最寂寞。秒針跑到哪裏呢,分針和時針心機深沉,按兵不動。那裏面有字。他們告訴A字很好玩。字怎麼寫呢。沒有人回答。A的親族,包括最機靈最滋補的黑腳羌,都不認識字。
A摘了一個果子放進嘴裏,細細嘗著那滋味。春天過了。他的臉黑了一些。他走到柚子園,看見樹枝上冒出白色的花朵。彷彿有一個人教他寫字。
此時恰好有個模糊的影子,從竹林那頭靠近。
秋天要到了——長老說——蓋一間避寒的屋子。修補衣物。小心火種。還有,把一些字收藏起來。
如此而已嗎?把方塊字冰結。堆高。想像著春天時它們將被飲用。
然而,字要怎麼成形呢?
A跟在長老旁邊——
劈柴。起灶——
明天跟我入山——長老說。
長老,他是一個大地的雲遊者。總是遊蹤不定。但他承諾,想到他時,他就會出現。現在他雲遊到宇宙深處——該是字很多的地方嗎。A每天都知道他在。
A拿出一些字獻給他。就這麼多。
後記1
詩的耕耘,就像田園的耕耘,為人類造就生存的美學。
草屋、籬落、田疇,至今看來,仍是富含邏輯與深意。
人類無法脫離這種基本的耕耘。
我重新對這種生存美學感到心動。或者說,它一直在我心動處。
後記2
窸窣。窸窣。你在門外。
窸窣。窸窣。你在樓頂。
窸窣。窸窣。窸窣。
你看到我的心。窸窣。窸
窣。窸窣。遠方的旗子
在飄。窸窣。窸窣。窸
窣。更遠的海。在我的心
後記3
我不想獨自活著。
我只想獨自一個房間。
知道你在隔壁,穿著髒衣服。我也沒有去洗滌。知道你在隔壁開著音響,我也嘴裏哼著歌。知道你們在隔壁馬路飆車打架,我也把飽蘸油彩的筆投向牆壁。除了紅色,還有黑色、棕色、黃色、白色。
知道你們在隔壁工地施工,架鋼條,開水泥攪拌車。把房子推倒,把房子建起。我也在建築,打字,取消,複製,貼上。
每天到陽台的鳥會告訴我,每天鑽進紗窗的蚊蟲會告訴我,風雲變色,風聲鶴唳,風吹草動。風也是靈敏的,雨也會坐在窗檯上。我也會出門,像雨一樣在城市行走。走在你的後面,走在你們的後面,和你們一起進餐館,吃進去,吐出來。如果你們不好吃。
後記4
基於一種深情,我也會發出聲音。從鳥的嘴巴裏,從田塍的水影裏,從泥土的氣味裏。從老人、舊屋、朽木、颱風。從陌生的街道,破敗的夕色;從饑餓的皮囊,腐臭的肛門。
基於一種深情,我不想分清美與醜,善與惡,天使與魔鬼。黑色白色,高低貴賤,裏面外面,生與死。我走在異鄉,安份如一個生了根的鄉民。我一個人,熱鬧如帶領一整個家庭。
基於一種深情,每天都看到,新的好奇誕生,新的思維轉換。更多不知道來臨。我從前並不知道,它們數量眾多。我想再往裏走,我想看看生命的長相。仔細瞧瞧它。雖然它可能並無長相。基於一種深情。
後記5
不再有那些聲腔了,我只能是個無能的歌者。
漫遊。漫遊。輕聲吟哦。
我沒有鬧鐘。時常忘了眼淚。
輕如草芥的試探││空氣的溫度,人類的仁慈。
輕如心臟在器皿中,在身體的器皿中,搏動。
此時,我身處群山,環山如堵,堅固如岩穴。寂靜鋪蓋,如宇宙最偉大的發明。
我沒有放大鏡。望遠鏡。但我能看到空中細微的浮游物,在飛起,在散播。牠們的翅翼,唾液,速度。我能看到,是因為有一種東西誕生,維持了平衡。
我看到那胎衣,透明,薄膜,剝裂。一個赤子走出,又一個赤子走出。勇敢,堅毅,眼神凝亮。他遊戲,他飛。此時,他來到懸崖,如履平地。他隨時轉換維度。他的心變換,在不同的空間。
他隱形,他在戒指的反面。他飛起,他借來姑獲鳥的外衣。他縮小,在空中平穩飛翔。
我喚他棉絮,喚他蒲公英,蜻蜓,初夏黃昏的蠛蠓。
我是多麼高興能與他們同行。
樹,蟲子,方塊字
A在冬天和春天交界的地方出生,那裏有一棵樹。
他摘了一個果子放進嘴裏。河水在流動。他往前爬。
一些蟲子張開細小的翅膀。周圍會飛的還有雲,還有冰霜和雨。
風也飛得很快。飛過河灣的時候,漣漪向四方漫開。涮洗著一些草的根莖。
一個人走過來,牽著A的手。他們走進一個深山的村落,更深處有一個家。這是你的兄弟。你的姊妹。父母。祖父母。你的親族。散佈在這座山,那座山。你的耳朵,你的眼睛,你的鼻子,嘴巴,身體所及之處。
A向前迎接,幾個遠處的人影,舉著火把,從最高的那座山下來。帶來一些熱氣、搖晃,和有陰影的圖象。大家圍住他們,寒暄、喝茶。大廳的桌子擺開了,木頭椅條,馬上坐滿一些人。棋子出現了,獵物出現了。女人重新撥開灰燼,柴火重新入灶,熱食出現了。
煙霧在燈泡下繞著。
綁在桌腳的小猴子不見了。
有人吃著猴腦。
被蛇叮過的大腿,用牛糞敷著。
A站在廳堂大鐘的前面。此時時間最寂寞。秒針跑到哪裏呢,分針和時針心機深沉,按兵不動。那裏面有字。他們告訴A字很好玩。字怎麼寫呢。沒有人回答。A的親族,包括最機靈最滋補的黑腳羌,都不認識字。
A摘了一個果子放進嘴裏,細細嘗著那滋味。春天過了。他的臉黑了一些。他走到柚子園,看見樹枝上冒出白色的花朵。彷彿有一個人教他寫字。
此時恰好有個模糊的影子,從竹林那頭靠近。
秋天要到了——長老說——蓋一間避寒的屋子。修補衣物。小心火種。還有,把一些字收藏起來。
如此而已嗎?把方塊字冰結。堆高。想像著春天時它們將被飲用。
然而,字要怎麼成形呢?
A跟在長老旁邊——
劈柴。起灶——
明天跟我入山——長老說。
長老,他是一個大地的雲遊者。總是遊蹤不定。但他承諾,想到他時,他就會出現。現在他雲遊到宇宙深處——該是字很多的地方嗎。A每天都知道他在。
A拿出一些字獻給他。就這麼多。
後記1
詩的耕耘,就像田園的耕耘,為人類造就生存的美學。
草屋、籬落、田疇,至今看來,仍是富含邏輯與深意。
人類無法脫離這種基本的耕耘。
我重新對這種生存美學感到心動。或者說,它一直在我心動處。
後記2
窸窣。窸窣。你在門外。
窸窣。窸窣。你在樓頂。
窸窣。窸窣。窸窣。
你看到我的心。窸窣。窸
窣。窸窣。遠方的旗子
在飄。窸窣。窸窣。窸
窣。更遠的海。在我的心
後記3
我不想獨自活著。
我只想獨自一個房間。
知道你在隔壁,穿著髒衣服。我也沒有去洗滌。知道你在隔壁開著音響,我也嘴裏哼著歌。知道你們在隔壁馬路飆車打架,我也把飽蘸油彩的筆投向牆壁。除了紅色,還有黑色、棕色、黃色、白色。
知道你們在隔壁工地施工,架鋼條,開水泥攪拌車。把房子推倒,把房子建起。我也在建築,打字,取消,複製,貼上。
每天到陽台的鳥會告訴我,每天鑽進紗窗的蚊蟲會告訴我,風雲變色,風聲鶴唳,風吹草動。風也是靈敏的,雨也會坐在窗檯上。我也會出門,像雨一樣在城市行走。走在你的後面,走在你們的後面,和你們一起進餐館,吃進去,吐出來。如果你們不好吃。
後記4
基於一種深情,我也會發出聲音。從鳥的嘴巴裏,從田塍的水影裏,從泥土的氣味裏。從老人、舊屋、朽木、颱風。從陌生的街道,破敗的夕色;從饑餓的皮囊,腐臭的肛門。
基於一種深情,我不想分清美與醜,善與惡,天使與魔鬼。黑色白色,高低貴賤,裏面外面,生與死。我走在異鄉,安份如一個生了根的鄉民。我一個人,熱鬧如帶領一整個家庭。
基於一種深情,每天都看到,新的好奇誕生,新的思維轉換。更多不知道來臨。我從前並不知道,它們數量眾多。我想再往裏走,我想看看生命的長相。仔細瞧瞧它。雖然它可能並無長相。基於一種深情。
後記5
不再有那些聲腔了,我只能是個無能的歌者。
漫遊。漫遊。輕聲吟哦。
我沒有鬧鐘。時常忘了眼淚。
輕如草芥的試探││空氣的溫度,人類的仁慈。
輕如心臟在器皿中,在身體的器皿中,搏動。
此時,我身處群山,環山如堵,堅固如岩穴。寂靜鋪蓋,如宇宙最偉大的發明。
我沒有放大鏡。望遠鏡。但我能看到空中細微的浮游物,在飛起,在散播。牠們的翅翼,唾液,速度。我能看到,是因為有一種東西誕生,維持了平衡。
我看到那胎衣,透明,薄膜,剝裂。一個赤子走出,又一個赤子走出。勇敢,堅毅,眼神凝亮。他遊戲,他飛。此時,他來到懸崖,如履平地。他隨時轉換維度。他的心變換,在不同的空間。
他隱形,他在戒指的反面。他飛起,他借來姑獲鳥的外衣。他縮小,在空中平穩飛翔。
我喚他棉絮,喚他蒲公英,蜻蜓,初夏黃昏的蠛蠓。
我是多麼高興能與他們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