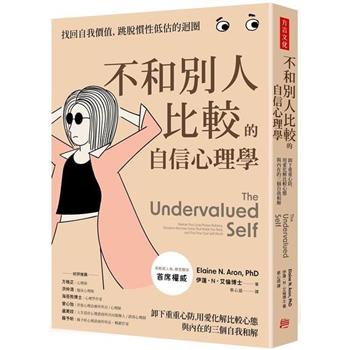這是我妻子外遇的故事,我非親口說出不可。
三個男孩,一個丈夫,她卻還要另一個愛慕她的男人。
儘管在我懷裡,她卻比這輩子的任何時刻都要更孤寂。
我們盡力了,身為丈夫和父親的我們,真的很盡力……十八世紀,英國最富盛名的女演員朵拉‧喬登,擅長演活莎士比亞劇中的女人而聞名於世,她一生戀人不斷,是十三個孩子的母親,最轟動是與英王威廉四世的戀情。
二十一世紀,三個男孩的母親喬琪,40歲,美麗動人,是因婚姻退出舞台的女演員;婚後的再次登台,就是飾演二百年前的喬登夫人。
相隔二百多年的二個女人,遭遇同樣的人生掙扎與難題,也都因為身為女人對愛情與舞台的熱情,讓事情轉向無法挽救的毀滅。由喬琪的丈夫所敘述,《妻子離開我的理由》是一部聰明又性感的小說,關於得到妳所想要的──但仍想要更多。
****喬琪看來擁有一切:一個愛她的丈夫、三個稚齡兒子,與寧靜的郊區生活。直到丈夫彼得因工作升遷,他們收拾行囊,舉家遠渡重洋到陌生的倫敦。
因為一次機緣,喬琪當初因為生養小孩而拋下、沉寂的舞台生涯逐漸復甦。她得到畢生難得一遇的角色:朵拉.喬登,一個真實人物,十八世紀最著名的女演員、英王威廉四世的情婦,也是十三名私生子的母親。
就在喬琪似乎擁有她所想要的一切時,一段外遇讓她甘願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結果卻造成無人能預期的悲劇……
喬琪與喬登夫人,二個女人如出一轍。在婚外情與孩子們之間徘徊;同時都是享有盛名與偉大成就的女演員,也奮力掙扎於工作與愛情之間。從一個由丈夫敘述的外遇故事,窺視一段不欲人知的外遇,反映情感危機中掙扎的人心,不僅挑戰每個人心中的婚姻與愛情價值觀,也看見數百年來女人們都會面臨的難題,其實一直未變。
作者簡介:
南西.伍德拉芙
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獲得藝術碩士(MFA),並在那裡贏得韓菲爾德/大西洋評論獎(Henfield /Transatlantic Review Award)。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帕切斯分校(SUNY Purchase)教授寫作,之後於1997年遷居倫敦,在里奇蒙(Richmond)的美國國際大學(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任教八年。她目前居住於布魯克林(Brooklyn),並任教於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譯者簡介:
楊雅婷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碩士,現從事翻譯工作。譯作有《歷史大口吃》、《關於美之必要》、《巧克力時尚之旅》、《馬戲團之夜》、《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下長大的孩童 》、《啥都瞭了》、《阿茲海默症》等,以及多篇學術論文。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我發現自己站著讀《妻子離開我的理由》。我會從化妝台或走廊上的桌子拿起它,然後開始閱讀,完全沒想到要坐下。這顯示我多麼急切地想讀到下一頁、下一章。一旦讀完,我又開始重讀它。它真是神奇。」
──安.達比(Ann Darby),The Orphan Game的作者
「《妻子離開我的理由》具有經典小說的那種罕見魅力:閃耀而獨特的書寫之美,以及動人而令人心碎的故事本身。南西.伍德拉芙(Nancy Woodruff)以智慧和一顆狂放的心記錄了家庭生活。」
──瑪莉.歐康納(Mary O’Connell),Living with Saints的作者
「從我拿起《妻子離開我的理由》──講述一個女人在倫敦舞台上尋找她之前的自我的故事──的那一刻起,就發現自己徹底被迷住了。充滿智慧、動人心弦、生動犀利,遣詞用句簡約得幾乎令人誤以為是簡單;作者用以闡明這部小說的目光,有如劇院的聚光燈一般明亮而具穿透力。燦爛耀眼。」
──碧翠絲.柯林(Beatrice Colin),The Glimmer Palace的作者
「《妻子離開我的理由》同時具備西區戲劇的舞台風華,以及傑出推理小說的緊湊情節和緊張懸疑;它以這兩種特質將你拉進這齣現代悲劇──其中的人物被刻畫得如此豐富──而且拒絕放你走。」
──海倫娜.史黛品斯基(Helene Stapinski),
Baby Plays Around: A Love Affair, with Music的作者
「《妻子離開我的理由》的樸質之美不僅令我心碎,也讓我心醉神迷。隨著她追述彼得與喬琪的婚姻、直至其最具毀滅性的結局,南西.伍德拉芙檢視了愛的各種不同化身──肉慾的愛、浪漫的愛,以及也許最深刻的,母愛。這個故事循其必然的方式開展,無所遁逃於作者誠實的凝視之下。」
──琴恩.雷諾茲.珮琪(Jean Reynolds Page),
The Last Summer of Her Other Life的作者
「這部小說是一首扣人心弦的頌歌,歌頌著戲劇,以及戲劇所能博得──同時也能摧毀──的愛;伍德拉芙令所有的人感動落淚……它殘酷而優美。」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重點書評)
名人推薦:「我發現自己站著讀《妻子離開我的理由》。我會從化妝台或走廊上的桌子拿起它,然後開始閱讀,完全沒想到要坐下。這顯示我多麼急切地想讀到下一頁、下一章。一旦讀完,我又開始重讀它。它真是神奇。」
──安.達比(Ann Darby),The Orphan Game的作者
「《妻子離開我的理由》具有經典小說的那種罕見魅力:閃耀而獨特的書寫之美,以及動人而令人心碎的故事本身。南西.伍德拉芙(Nancy Woodruff)以智慧和一顆狂放的心記錄了家庭生活。」
──瑪莉.歐康納(Mary O’Connell),Living with Saints的作者
「從我拿起《妻子...
章節試閱
「我想不通。」喬琪說:「她為什麼要退休?」
「他要求她退休。他是個男人,而且他是皇室成員。」皮爾斯說:「在攝政時期的英國,這是兩個非常好的理由。」
「但她很痛苦。她受不了待在家裡。」喬琪皺起眉頭:「『弗列多斯的新靴子的確棒透了!』」她模仿著。「她快活不下去了,她快瘋了。」
「你掌握得分毫不差。」皮爾斯說。
「相信我,我是過來人。」喬琪說:「都過了兩百年,情況還是一點都沒變。你想把每分每秒都花在孩子身上,同時在工作上擁有充實的人生。」
喬琪和皮爾斯花了整個下午排演有關布許莊園的場景。距離這齣戲的首演不到三星期了,妮可拉卻有一天半的排練不能到,於是由皮爾斯接手。這不是正規的作法,也許還會讓人看出妮可拉有多崇拜皮爾斯,以至於願意讓他涉足她的導演角色,但妮可拉不想要喬琪落後進度。
「完美極了。」他說:「完美得我想建議我們明天翹練一天,做一點時代背景研究。」
「像是?」
「肯伍德館有幅畫妳真的一定得去看。」皮爾斯說:「喬登夫人扮成薇奧拉的畫像。肯伍德館。妳去過嗎?」
「沒有。我一直想去,但是──」
「噢,那是個迷人的地方,座落在漢普斯德石南公園的坡頂。我明天中午在那兒跟妳碰面,我們可以一起去看,好嗎?」他注視她的眼神平和而沉穩,他給她的微笑如此溫暖,致使她有一瞬間覺得他們彷彿是朋友,而他邀她到某處是世上再自然不過的事。
「當然。」她緩緩說:「怎麼會不好呢?」
到目前為止,皮爾斯一直保持著帶有距離的和善,喬琪則恭敬而略帶羞怯。他這個提議──將是他們的首次約會嗎?她當時肯定不這麼想,否則她絕不會跟我提這件事,還扮鬼臉、轉眼珠子:「他要我去看這幅畫。」
她像要去約會般地打扮自己:搽口紅,使勁梳一頭長髮,讓它自然披散下來,穿上棕色的麂皮裙子、紫紅色襯衫,搭配一雙麂皮長靴,不僅可以炫燿她優美的小腿曲線,又剛好露出她的圓潤膝頭。
肯伍德館是一座宏偉莊嚴的白色宅邸,收藏許多荷蘭大師與英國肖像畫家的畫作。它位於倫敦非常近似村郊的地區,喬琪覺得恍若置身鄉間。他們沿石子路走向宅邸,在屋裡靜靜穿梭,看過每一個房間,直到找到皮爾斯要喬琪看的那幅畫。它尺寸不大,並不特別出色,只是一幅肖像,描繪喬登夫人扮成喬裝男孩的薇奧拉。喬琪比較喜歡她在其他地方看過的全身像──藝術家對這個女性的整體描繪,能幫助喬琪從肢體上暸解喬登夫人。而這只是一幅漂亮的圖畫,她這麼告訴皮爾斯。
「沒錯,但那是她最著名的角色之一。」他反駁:「我認為看過這幅畫對妳來說應該很重要。」
「我認為你只是今天不想幹活兒。」她調侃道:「可又不想惹毛妮可拉。」
他沒有否認,於是他們同時開始大笑。
「來吧。」他說:「我們去浪費更多時間吧!」
他們離開房子,在庭園中漫步,走上一條通往池塘的小路。那時剛過正午不久,但十二月中的白天如此短暫,感覺上天色已漸漸暗了。喬琪閉上雙眼,試著假裝自己身在布許。布許的屋齡和此處相當,風格也類似。喬琪曾試圖造訪布許──它依舊矗立在倫敦南邊的漢普頓宮附近,但如今被當作某種科學研究設施使用,不對公眾開放。即使她秉持紐約人鍥而不捨的精神,仍不得其門而入。試過幾次後,她打消了念頭,反正,她心想,她也不想看到喬登夫人鍾愛的布許到處充斥著書桌和電腦。
最後,他們在肯伍德館的茶舖一起喝咖啡,結束這一天的行程。這是喬琪第一次與皮爾斯對桌而坐──單獨地──當她緊張兮兮地擺弄桌上的餐具時,她發現自己感到非常脆弱,就像在台上為了他排練、努力演好這個角色的時候一樣。為了他:她以前從未演出過任何像這樣劇作家總是在場的戲。她覺得創作者和創作完完全全混融在一起,也感到一種瘋狂、強烈、想要取悅他的需求。
「你究竟是怎麼對喬登夫人產生興趣的?」她決定問他。
他微笑著攪拌咖啡,雖然他既沒加牛奶也沒放糖。「妳可以說是為了多愁善感的理由。妳也知道,我們算起來是遠親嘛。」
「不,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呢?難道是你沒告訴我嗎?」她微笑,嘲弄著他。她是否笑得太過?她覺得自己笑得太過了。
「她是我母系的親戚。小時候,當我們很激動或舉止誇張時,我母親總會說:『噢,那是你心裡的喬登夫人跑出來了。』我從未真正明白喬登夫人是個真人。我以為她是我母親掰出來的。『那是你心裡的喬登夫人』,我以為這只是一種說法,好比『魔鬼要我這麼做』或『貓兒吃了你的舌頭』之類。」
「或是『那只是酒在說話』。」喬琪說。這句話一直都是她父親的最愛。
「完全正確。沒有人會為這種親族關係自豪。身為某國王庶出的曾曾曾曾姪孫,並不是件值得吹噓、以贏取別人重視的事。直到我在準備歷史高級課程考試時,才碰巧看見一條朵拉.喬登的資料,發現她原來是個真人。又過了很久,我才有足夠的學識,了解她不只是個來淘金的無腦尤物。我得到的結論是,老威廉能遇見她大概是八輩子修來的福氣。他是個花花公子,揮霍無度,重點是腦袋不太靈光。她的人格顯然高尚許多:仁慈、富同情心,非常慷慨大方。她像狗一樣地辛勤工作,賺錢養他,但我相信她真心愛著他,妳不認為嗎?」
「我相信。」喬琪說,因為他詢問她的意見而愚蠢地沾沾自喜。
「我知道事情從表面看來是什麼樣子──他在她變老變胖、看來失去那種具生殖力的外貌時,拋棄了她──」
「那種具生殖力的外貌?」喬琪尖銳地問。
皮爾斯朝她微微一笑。「對不起。我的意思是,從外表看來,事情總是顯得醜惡,充滿陳腔濫調,然而,一旦妳進入核心,就會發現真相極少是如此。情況絕不是像『男人遺棄女人』那樣簡單。還有更多內情,而我想發掘真正的故事。」
她注視著他覆在她雙手上的手。移開它幾乎好像比讓它留在那兒更違反常軌。之前,她從來沒有在肢體上如此接近過他,只是縱容自己奔湧的欲望。歡愉,而拘束。這會造成什麼傷害呢?她沒有把手抽開。
她清了清喉嚨。「我猜你可以說,他只不過想跟明星有一腿,而她,我不曉得,想跟皇室有一腿──」
「從這個角度看這件事是很容易,但果真如此,他們的關係會維持二十年嗎?每個跡象都顯示,他們有非常快樂的家庭,深愛著彼此和子女。我深切地渴望為他們的愛情賦予靈魂。」
「你的確這麼做了。」她說。
「有嗎?我曾經希望如此,喬琪,但我不那麼確定自己成功了。」喬琪發現自己因為他說出她的名字而臉紅,感覺好像在中學時,發現自己心儀的男孩居然知道她是誰一樣。我必須停止,她想。我表現得像個白癡。
皮爾斯繼續說:「這齣戲對我最大的挑戰在於,儘管我有她寫給他的信,數以百計的信,至今卻沒有一封他寫給她的信存留。他離開她後,她迫於情勢,覺得這些信必須交還給公爵的律師和顧問,而它們很可能全被銷毀了。我無法百分之百確知他是否愛她、他為何離開她、他後來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何感受,這著實令人惱怒不已啊!」
「他保留了所有她寫的信,難道這事實不足以告訴你他一定愛著她嗎?」
皮爾斯點頭微笑:「我是這麼推斷的,但到頭來,一個人所能擁有的,終究只是自己盡可能合理的猜測而已。」
「沒錯。」喬琪說,微笑著。
皮爾斯終於把他的手從她手上移開,恰如他之前放上來一般地若無其事。
他已經在試圖勾引她了嗎?他安排這次短程出遊,一次安全的會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國民信託組織所經管的莊園上──也許是他為了達到目的所採取的第一個溫和的策略。然而,當我好好思索那天的事,想像當時的情景時,卻不敢十分確定。我想,情況可能朝任何一個方向發展,而真正令我嫉妒的,也許並不是他的手暫放在她手上,而是他們關於那齣戲的談話。我也是個作家啊,我想這麼說,把自己安插進肯伍德館那個天色漸暗的十二月下午。喬琪,妳可以跟我談那些事啊!
「這是個什麼樣的歷程啊!」喬琪說:「有個活在兩百年前的女子,你得發掘她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寫下這齣戲,而現在我又得重新再發掘她是什麼樣的人,才能演出這個角色。」
「這個嘛,沒錯。終究說來,戲劇便是這麼回事。」
「不。」喬琪說:「我說的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一切都是重新創造的結果。沒有一件事是真的。全部都是……」她無法向他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於是再度陷入沈默。
「妳的意思是沒有真相,只有各種不同的版本嗎?」
「一點都不是。」她說:「她的人生是有真相的。只是你我各有不同的版本。」
「非常溫柔的想法,喬琪。非常純淨。但是,看一段人生的方式有好幾十種。她是個複雜的女人。她愛公爵嗎?她不愛公爵嗎?她是否真如自己所說的那麼想念兒女?這全都是詮釋的問題。」
「完全正確。」喬琪說:「你的詮釋和我的詮釋。但她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妮可拉並不這麼想。」皮爾斯說。
「顯然,妮可拉錯了。」喬琪說:「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必須站在主導地位,堅持以某種觀點來詮釋她的人生。如果你要描寫她,如果我要扮演她,我們就需要堅守各自的版本。但這一切背後,是我們全都不認識的、真正的朵拉.喬登。」
皮爾斯點頭:「我想,任何人在嘗試書寫另一個人的人生時,都必須在書寫過程中承認這點事實。當然,若妳懷著大量盲目的傲慢,那就另當別論了。但我確實相信,如果妳能掌握核心的衝突──」
「她人生的主要動機──」喬琪再次打斷他。
「──那麼妳便對這個人生做了公平的處置。」皮爾斯說完他的話:「那是我們每個人所追求的,我們這些作家所追求的。」
「但是,你難道不希望自己可以回到過去嗎?」喬琪問,變得激動起來:「回到過去,跟她談,直接拿那些事問她?」
「想死了。」
喬琪沒來由地開始笑。
「怎麼了?」他問。
「沒事。」她說:「我不曉得。」但她還在笑,於是他追問:
「什麼嘛?」
「我只是覺得,我不曉得,對我來說,你突然變成了一個立體的人物。」
「對劇作家來說,這是件幸運的事吧,我想。」
「噢,不不不。」喬琪說:「劇作家可以理直氣壯地當個平面人物。我所認識的劇作家大多如此。」
「妳可真是宅心仁厚!」
「不,我是說真的。重點在那個過程。角色人物要求演員賦予他們生命,劇作家幾乎也有同樣的要求。」
「那不會是你,對不對?」皮爾斯問,他帶有調侃意味的反諷語氣,與他的眼神格格不入。她羞怯地微笑,低頭望著他幾分鐘前才放在她手上的手。
「嗯。」過了一會兒,她低聲說:「我得回家了。」回到我丈夫身旁。回到我的人生。她已經縱容自己沉浸在這幻想中一時半刻;現在該是放手的時候。
「妳確定?」他問。
「我確定。」她說著起身。皮爾斯也站了起來。他挽著她的手臂領她走到戶外。午後的天空已順利結束邁向黑暗的旅程。雖然她拒絕承認,但他已經開始侵入她心中。
…………
首演夜。
第一夜,這是倫敦人的說法。
如果是在紐約,我們所有的朋友、喬琪的母親、兄長和他們的妻子,一大票人都會一起來慶祝。但才剛在倫敦待滿四個月的我們,幾乎不認識半個人,而且喬琪十分謹慎;她不要我邀請工作上的新同事,或是任何一個她稱不上認識的鄰居。對街的琴恩一直都非常友善,但喬琪跟她並非深交,有天琴恩拿著幾個變壓器出現在我家門口,才說道,她丈夫突然被調回紐約了。
所有的座位都坐滿了──製作人確認了這一點──而在空間如此親密的劇院裡,第一排觀眾簡直就緊貼著帷幕。我在後排與葛拉罕坐一塊,因為喬琪比較關切我們對觀眾的觀察,而不是對她的看法。
她出場時戴著一頂當時流行的假髮,假髮稍稍撲了粉,身上穿著黃綢連身裙;雖然在戲一開始,她應該是個五十四歲的老婦人,臃腫、病弱、深受絕望折磨,但他們並沒有為她畫上老妝。她能夠藉由臉部表情、姿勢,以及微微喘不過氣的說話方式(暗示講話對她來說有多困難),來傳達她所需要表現的年齡。
我立刻回想起她初遇喬登夫人的那晚,當時她身穿白背心和牛仔褲,在我們的小客廳裡為我一個人表演。
當她開始倒溯喬登夫人的人生,返回其青春年華時,她的動作中注入了一股令人迷醉的活力;她的姿勢和呼吸改變了,從貧窮的愛爾蘭私生女,變成著名的倫敦女伶、皇家公爵的情婦、十三個孩子的母親,台詞的音節也時而延長,時而縮短。她接連化身為蘿莎琳德、薇奧拉、海倫娜 、《美麗的懺悔者》裡的可憐女孩,以及某個叫提佐夫人 的女人──每個角色只持續片刻,卻引起觀眾震耳欲聾的歡呼,直到她神奇地轉換心境,營造出下個場景的感染力。
只不過加戴一頂飾有羽毛的帽子,或換上尖頭靴,或調整一下假髮,就完全改變了她的形貌氣息──其間轉變如此微妙,除了整體的轉化之外,什麼也察覺不到。
她演得很好,好到我為這個從沒聽說過的女子的人生故事熱淚盈眶。
八十五分鐘的戲,沒有中場休息,她唯一坐下的時候,幾乎只有整場戲的最後幾分鐘,她躺在沙發上,詢問女僕有沒有來自兒女的消息。
一直令她苦惱的結尾,就像這齣戲的其餘部分一樣順暢,激動人心。我看得恍然出神,下一秒把我驚醒、並讓我不由自主站起來的,是純粹的掌聲。其他人也都起立鼓掌。
葛拉罕緊抓著我的肩膀。「了不起的成功演出!我認為這麼說一點都不嫌太早。」他說。
激昂的叫喊與歡呼四起;掌聲持續不歇。當喬琪回到舞臺上謝幕時,她的目光立刻朝我的方向射來。她大概一開始就找到我的位置,但她是經驗如此豐富的演員,不會讓我知道。我注意到她眼眸下方閃閃發亮的兩片肌膚──那是她為喬登夫人流下的淚水,不是在觀眾面前,而是她在後台獨處時所流下的。
喬琪在舞台上向我微笑,那令人迷眩的瞬間,我幾乎無法相信自己是那個娶了她、夜夜與她同床共枕、跟她一起生了那些小孩的人。今夜,我只是另一個戲迷,深深陶醉在她的演出中。
演出結束後有一場宴會,我們擠進計程車,前往諾丁丘的一家餐廳。葛拉罕對我保證,餐廳時髦到不行,時髦到幾乎完全沒裝璜的程度。牆上沒掛畫,沒有盆景,也沒有花紋地毯,除了最低限度的照明之外,什麼都沒有。巧克力色的牆面,黑皮椅,白桌巾。我們一群人填滿了整個空間,一襲乳白色洋裝的喬琪穿梭在室內,像她掌控舞台般地吸引所有工作人員的注意。她為每個人準備了小禮物,一枝接著一枝地遞送紅玫瑰。她到處分贈禮物和花朵,我在那些與她共事的人臉上,看出真誠的喜愛。她似乎在未曾樹敵的情況下通過了這場考驗。
理所當然地,我站在外圍,喝著蘇格蘭威士忌,羨慕他們所有的人──羨慕他們共同創造的作品,以及他們在創作期間建立的情誼。我懷念的並不是創作過程,因為,即使當寫作還占據我生命的核心時,我也從未有過這樣的體驗。寫作是一種單獨進行的技藝。我們總是置身局外,朝裡望,滿懷渴望地看著,但從不屬於其中;也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會成為作家,獻身於某種受到認可的人生,站在自己永恆的昏暮中,凝視別人燈火通明的落地窗。
喬琪出現在我身旁,在我耳畔輕語:「你跟他們見面了嗎?」我搖頭,她立刻將我拉到妮克拉旁邊,我發現她遠比喬琪所暗示的漂亮許多。就我的品味而言,她稍嫌樸素,整潔俐落,身形嬌小,散發一種過度沉穩的氣息,我覺得不是很吸引人。但我所遇見的許多英國女性,似乎看起來都是這樣:她們對待男人的方式有一點像《小飛俠》裡的溫蒂,不知怎地帶有褓姆的味道,彷彿她們的工作就是要讓男人表現得宜,而達到此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責備他們。在她們身上,我看不到那種少有的自信與脆弱的組合──那是我一直很喜歡的特質,但之前從未把它稱做美國女性的特質。
一開始,妮可拉和我的交談好像在開親師座談會:除了喬琪──她的演出,她當晚的風光成就──我們沒什麼好聊的;但過了一會兒,我們找到共同話題:凡妮.柏尼 的日記,因而真正談了點東西。我請妮可拉介紹我給皮爾斯認識,憑喬琪的描述,我立刻便認出他。他並沒有跟大家打成一片,而是站在房間中央,等著人們前來跟他說話。
而每個人確實都這麼做,我也不例外。
「喬琪的先生。」他說著伸出手:「當然。幸會。」
「彼此彼此。」我說,我相當確定以前從未大聲說過這個詞。
我明白喬琪在描述他的微笑時,是什麼意思了。他微笑的溫暖掩飾了他大體上漠不關心的態度,使你想要努力再贏得一次他的青睞。遇見名人、甚或準名人的時候,我的習慣是說些最不著邊際的閒話,儘管我心裡極想問他們關於其音樂、其藝術、其寫作的問題。如果是在他家裡,我會尋找透露他嗜好的線索──也許是他的帆船黑白照,或是他所蒐集的爵士唱片──但在這兒,沒有任何道具,我更是難以施展,淨說著最不著邊際的閒話:劇院的水準,優秀的觀眾等。他沒有提出任何挑戰,我們緩慢而彬彬有禮地交談。
很難說我對他究竟有什麼看法。他談吐文雅,親切和善,懷著英雄氣度,用心進行我們枯燥的談話。倘若我當初知道我現在所知的,我會衡量每個字、每個音節、每個朝她的方向送出的微笑或瞥視,我會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拿自己和他相比,以便找出他的弱點,確定我自己相對的強項,準備應戰。他不曾問我任何關於我的問題,但我不在意。我假設,正如我一向對名人做的假設,即使我們再相遇──或一再地相遇──依舊會保持同樣的距離,我們不可能變得更親近。
現在,令我難以置信的是,我那時竟然跟這個幾星期後要幹我老婆的人站在同一個房間裡──我們談話時,他大概滿腦子想的都是那回事──卻一無所知。
有人在敲玻璃杯,到了喬琪致詞的時刻。她穿著象牙白的洋裝站在房間前方──像個新娘,我突然想到──雙頰因為那晚的興奮而泛紅。她的演說經過精心設計,有溫馨的部分,也有很多讚揚,但不能太過頭,惹得大家對她的美式多愁善感翻白眼。這似乎是美國人在英國所能犯下最愚蠢的罪過──公然表現感情用事的罪過。
喬琪的致詞與我在家裡聽她練習的內容一樣──當時她穿著兩件式睡衣,盤腿坐在床上,我則在旁邊啜飲葡萄酒,手擱在她的大腿上。現在聽她講話,我再度感受到剛剛在劇院裡的感覺。這個女人是誰啊?這真的是喬琪嗎?她還是那個我當初在夜晚搭火車回紐澤西的家時,有時會害怕面對的女人嗎?是那個用連珠炮般的控訴──她數落著種種加諸她身上的不公平待遇,包括三個男孩,以及那幢地下室墊高、有三間臥室的平房住宅,同時怒目瞪視我,彷彿我是一陣超級狂風,把一棵樹颳倒在我家房屋上──攻擊我的女人嗎?她是那個跟我一起度過一個又一個冗長的夜晚,一起為嬰兒洗澡、換尿片、努力餵他們吃東西、幫嘔吐的娃兒重新洗一次澡的女人嗎?是那個跟疲憊不堪的我做愛(就像所有有了孩子的父母一樣)、那個把內褲勾在腳踝上──因為她完事後絕不會有精力到床底下翻找──的女人嗎?
我已經忘記這可能是什麼景況了,因為她已經很久沒演出這樣的角色:一個讓她充滿熱情、同時也改變了她的角色。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一個新的人,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人──這個女演員,她掌控聲音和肢體的方式,不僅感動了我,也感動了在場的每個人。
她兩者皆是;如今我明白了。新的身分與舊的身分同時存在,是熟悉也是驚奇,我們內在的陌生人總是遇見別人心裡的陌生人,即使那個別人,是我們的所愛。
…………
星期天早晨,她搭早班火車回家,然後轉乘計程車;她急急走向房子,她的腳步渴望著我們。連恩從窗戶發現了她,於是打開前門──那是他被禁止做的事,但她根本不想責備他。
他在那裡。
我們都還在那裡。
藍色的地毯衝擊著她的感官,她的雙臂盡可能把我們全兜進懷裡。
「媽媽,妳好快就到家了。」弗格斯說:「比光速還快得多。」
「我們租了一部電影。」連恩說。
「靈犬萊西!」傑克大叫。
「我本來要說的!」連恩說:「應該是我來說的!」他用手肘頂傑克的肋骨,傑克開始哭。
「連恩。」我說:「跟你弟弟說對不起。」
連恩緊閉上眼睛,手指塞進耳朵。「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他低聲說,同時傑克扮演受害者,蜷曲在喬琪平放於地板的大腿上,她連外套都還來不及脫。
「老天,我好愛這些小孩。」她對我說,抬起眼越過傑克倚偎的頭,試著與我的目光相會。我在幹什麼,她想著,我到底在幹什麼。
「歡迎回家。」我說,一面親吻她。
她會結束這段插曲。她不會讓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個才剛剛開始的狀況。有許多人發覺自己婚姻不愉快,無法跟丈夫談心,被充滿敵意的牆壁和家具包圍,喃喃對自己說:這不是我的人生;喬琪跟她們是不同的,她安撫自己,擁抱著人生,滿懷感激地說:是的,這是我的人生。她會在任何人發現她讓人生陷入險境之前,就把它要回來。
下午,男孩們看影片時,她沖了澡,然後我們做愛。那是她的衝動──不抽離她的身體,而是進一步要求占有我的身體。她只跟皮爾斯睡過兩次,但跟我分享過數千個夜晚,十二年的夜晚,而且,直到現在,我們都只有彼此。
她對我的身體瞭若指掌,無論是觸感或味道。我胸前的那顆痣,總是讓她誤以為是左乳頭,從無例外,直到她的手繼續向左移,才會發現錯誤。我左上臂背面的小圓凹,是注射天花疫苗留下的痕跡。我胸膛上的凹陷,位於肋骨中央,大小正足以安放她的手掌。
她偎著我睡著了,隨後倒抽一口氣醒來。
「怎麼了?」我問:「妳做了一個『日間公馬』嗎?」
這個詞組令她莞爾;那是弗格斯發明的說法──他認為,如果晚上做的惡夢叫『夜間母馬』(nightmare),那麼白天做的惡夢就一定是『日間公馬』(day stallion)了。」
「老天。」她說:「彼得,他們已經自己在樓下待了將近兩小時。」
「妳覺得我們應該去察看一下有誰生還嗎?」
「我去。」她說。
她穿上罩袍,快步走開,到客廳門口才放慢腳步。她想要嚇他們一跳,想要在他們看見她之前,讓自己為了他們真摯的小腦袋瓜而心碎。
到處靜悄悄,非常安靜,但在沙發上,傑克的肩膀顫抖著,她讓自己的腳步聲變大,準備扯開嗓門責罵另外兩個男孩把他弄哭。在她什麼都還沒說之前,弗格斯起身摟住他,說:「別哭,傑克。你從音樂就聽得出萊西會好好的。」
她偷偷溜開,沒被他們瞧見,回到樓上找我。床很溫暖,床單散發著我們的氣味,我在床上伸手迎接她。她的臉龐綴著圓滾滾的熱淚,一顆顆宛如擋風玻璃上的雨珠。
「我愛你。」她輕聲說,而在我明白真相之前,那個下午一直伴著我,成為這段期間以來我們所度過最美好的時光。
噢,喬琪,有我們戀慕妳難道還不夠嗎?為什麼妳還需要再多一個?
…………
至於男孩兒們,他們很高興媽媽回家,高興得決心忘記她四天之後就得再度離開。喬琪在回多塞特的前一晚哄弗格斯入睡,他淚水盈眶,拼命揉眼睛。「我不想要妳去。」他說:「我要妳留下來陪我。」
「寶貝,我不能留下來。」她溫柔地對他微笑,撫平他頭頂那幾根刺蝟般的頭髮──那幾根總是不肯躺下來的頭髮。她懷疑,這離別的場景有可能變得愈來愈容易嗎?她懷疑,日後兒子們懇求她不要走時,她還會感覺自己的心被撕成碎片嗎?我是他們的母親,她想,他們需要我。但她也同時記起她一離開後,所感受到的輕鬆,以及那輕鬆所帶來的純粹喜悅。
「那我要跟妳一起去。」弗格斯說。
「你必須上學呀!」
「笨蛋老學校。」他轉開臉,她在他的枕頭上看見兩顆淚珠。
「不過,我告訴妳我可以做什麼。」喬琪說,在她的聲音裡注入興奮和共謀的成分──這是他倆之間的秘密:「我可以帶個東西回來給你。一份禮物。你想要我帶什麼給你?」
他停下來思索,似乎暫時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如果妳看到一些好看的襯衫,就幫我買一件。」他開懷地說,隨即又崩潰成可憐的細微啜泣:「我的──尺──寸。」
她陪了他一會兒,揉揉他的背,等他睡著。他的焦躁不安終於平息,她聽到規律的呼吸聲,於是輕輕起身離開他的床。
「不要,媽咪,不要。」他說。
「我還不能走嗎?」她問。
「不行。」他說:「永遠都不行。」然後:「回來看看我。要一直回來看看我。每分鐘都要。」
「好。」她說。靜靜地離開房間。
「每分鐘喔。」
她一出來到走廊,他便叫道:「我改變主意了。我改變主意了,媽咪。」他聽起來如此驚慌,所以她趕緊回到房裡。
「噓。」她說,怕他吵醒其他兩個孩子。她試著跟他打商量:「那我坐在門外的地板上好不好?」
「好。」
「直到你睡著。」
「好。」
她盤腿坐在地板上,靠著牆,因為無事可做,也沒有她想思考的事,所以她開始數數。緩慢地,數著自己的每一回呼吸,她數到三百,確定他睡著了,卻聽到他突然說:「媽咪,對不起我這樣說,可是我愛妳比愛爸爸多一點點。只有多一點點。因為有時候我覺得我是個可愛的小傢伙,可是爸爸認為不對,你不能是可愛的小傢伙,你是哥哥。可是你讓我當一個可愛的小傢伙。那就是為什麼我愛妳比愛爸爸多一點點。」
「做媽媽的都很會讓她們的小男孩當可愛的小傢伙。」喬琪說。
「我愛妳。」他說。
「我也愛你。」
「可是還不可以離開,媽咪。」
「我不會。」
「每次妳離開,我都以為再也見不到媽咪了。」
「弗格斯。」她說:「媽咪每次都會回來啊!媽咪總是會回來的。」
她在地板上睡著了,稍晚,當弗格斯終於睡著後,她才又醒來。她感到一陣寒意,於是回我們房間,很快地換上睡衣,鑽進被窩。她在黑暗中依偎在我身邊,親吻我的臉頰。我只微微動了一下,她對著我的肩膀做了一小段祈禱。
我們沒講話,直到早晨,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彼得,情況不會一直像這樣的。」
她當時所說的每個字,如今都因為我不久即將發現的事實而改變了意涵,彷彿染上無法磨滅的色調。她指的是我們缺少相處的時間,為她忙碌的行程道歉。再過幾星期就是她的生日,她的四十歲生日,而我們連討論要怎麼慶祝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在倫敦算是新來乍到,這在某種程度上讓我鬆了口氣,因為不用考慮辦生日宴。我四十歲生日時,她為我開了一場精采的派對,邀請四十位朋友,每個人都在她秘密燒錄的特製CD上獻唱一首歌,她還將這張CD分送給所有的賓客。我是絕不可能比過她的。
我一面打領帶一面問她:「妳生日快到了。」
她把臉深深埋進床裡:「別提醒我。」
「妳想怎麼過呢?」
「跟大家一樣啊。時光倒流。回到一九九九年應該不錯,我想。」
「我來想辦法。」我說。那時是清晨六點三十分,天還沒亮。她躺在床上,眼睛因為我著裝所需的燈光而閉著,半睡半醒,而且想維持這種狀態,因為當我在六點五十分離去後,她會再睡半小時,直到該叫兒子們起床的時刻,然後開始晨間公事:餵他們吃早餐,幫他們穿衣服,找到他們的書包,放進他們的家庭作業、運動服和泳具,然後送他們上學。
傑克儘管十分喜愛他的學校制服,卻總是先換了便服──還倒著穿──於是喬琪得幫他換衣服。一向早起的弗格斯,會在她進房間時玩玩具,抬頭問:「今天要上學啊?」他全然無辜的語氣讓你很難對他發火,但喬琪每次都會生氣。連恩是最難搞的,不管她怎麼努力,他每個步驟都頑強抵抗。他的襪子太緊。他的襯衫感覺好蠢。他的長褲太寬。即使當她趕他們下樓、嘴裡唸著「鞋子和外套!鞋子和外套」時,連恩還在找藉口跑回樓上換一條不同的皮帶。
我彎下身親吻她道別。
「會漸入佳境的。」她說,伸出溫暖的手貼著我的臉頰:「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但一定會的。」
「我不是不知道妳的工作很辛苦。」我說。
她貼著枕頭微微頷首,但心中想著,辛苦──不。興奮。欣喜若狂。再過幾小時她就上路了,再度奔向多塞特,奔向戲院,奔向喬登夫人,奔向他。對喬琪來說,辛苦的是回到她自己的生活。在爭吵中擔任仲裁。拿衣服去乾洗。每餐後清掃廚房地板。每個早晨讓他們穿上那些鞋子。
…………
小而陰暗的大廳裡無人可詢問,所以我自己找路,穿過狹窄錯綜的走廊和樓梯,來到妮可拉說喬琪住的二樓房間。
我敲門,一開始沒人回應,如果我可以重寫人生中的這一刻,我會希望永遠不會有任何回應。我會轉身離開旅館;找家酒館喝杯啤酒,接著吃晚餐;演出結束後再去找喬琪。但情況並非如此,我等待,傾聽,再敲一次門,敲得更大聲一點。
當她打開門時,她的眉毛因疑問而揚起,彷彿以為我是某個服務生──是的,我可以為您服務嗎?您想要什麼嗎?
我遞出方才買的玫瑰。
「彼得。」她說。她的眉毛塌下來,客氣的微笑瞬間瓦解。「我──我──我……」她撲向我,彷彿我們在一輛失控疾駛的車子裡,正朝一棵樹撞去,而這是唯一能救我的辦法。
「沒事的。」我說:「什麼事也沒發生。我──」
就在此刻我看見了他。他所在的場景,從那時起便一直沒完沒了地在我腦中盤旋:他坐在一扇凹嵌式窗戶的深色木頭窗台上,既沒看著我也沒看著喬琪,而是非常冷靜、非常刻意地望向一片凌亂的床。
沒有人急著解釋情況並不如表面看起來的那樣。喬琪緊抓著我,不停地顫抖。
沒什麼好說的,也沒人開口說話。我的雙手原本反射性地要伸出去抱住喬琪,但現在我讓它們軟軟地垂在兩側。我的旅行袋從肩膀滑落,玫瑰掉在地上。
我該說自己震驚?憤怒?還是不能置信?這些都有,但最主要的感覺,像是有一枚手榴彈已將我的身體炸成碎片,而我必須──完全只憑意志力──讓這些碎片繼續黏合在一起,保持身體完整,足以穿過這個房間。
「妳做了什麼?」我沙啞低語:「妳做了什麼?」
我想用雙手掐住她的脖子。但我沒有,我轉而攻擊他。
「聽我說,」他站起身:「這是很糟的情況。但讓我們都理智一點。」
打鬥從那裡開始,就在他站立的窗戶邊,然後橫越房間移向喬琪。
「你這個混蛋,你這個去他媽的混蛋,你這個去他媽的混蛋。」我說。我連連出拳痛擊他,喬琪尖叫要我住手。我不肯停下來,我沒辦法。他巧妙地讓我的拳頭打偏。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繼續追擊他,他的臉和頸部。他重重打中我的胃。我以為自己會殺了他,我滿腦子都是殺死他的念頭。我嘴巴裡充滿金屬和腐肉的味道,憤怒的味道。
當他逮到機會,他就推開我走向門口。
「我還是走吧。」他說:「喬琪,如果妳可以的話?」
喬琪──站在房間中央,掌心朝上,哭泣著──只能微弱地點頭。我靠著桌子,沉重地喘氣。皮爾斯在門口停下腳步,似乎要把整個場景納入眼底。
他是個劇作家;搞不好他很欣賞這個舞台設計。
「三十分鐘,喬琪。」他低聲說,指的是開演時間。
我衝過去踢那扇在他背後關上的門。我想再揍他,我想揍她。這些衝動像作嘔一般襲捲我的腦海,我把拳頭握得更緊,緊貼在身體兩側。
喬琪睜大的雙眼充滿驚懼,聚焦在我身上。「我沒辦法相信。」她說:「我沒辦法相信這種事真的發生了。」她走向我。
「別碰我。」我咆哮著,害怕我自己的程度不下於她。
她的臉孔扭曲,雙頰泛紅,愈來愈紅。她的頭上覆滿捲髮器,以上百支髮夾固定著,她穿著一件我不記得看過的藍色條紋襯衫,皺巴巴的,太大的,男用襯衫。
他的襯衫。
「這件事現在就結束了。」喬琪說:「就在此時此刻。絕對不會再發生。我跟你保證。噢,彼得。」她語不成聲:「真的很對不起。」
她終於不再試圖觸碰我,只是站在房間中央,帶著醜陋扭曲的面容,被鼻涕眼淚糊得閃閃發亮。
「多久了?」我問。
「只有從我們到多塞特之後。」她說:「在倫敦完全沒有。只有過去這三個週末。」
三個週末。
用一輩子來看,三個週末算什麼?
三個週末能否以某種方式抹滅、矯正?還是它們足以永遠改變好幾個人生的結局?
「我不是故意讓這件事發生的。」喬琪說:「你相信我,不是嗎?」
「我相信妳嗎?」我問:「妳他媽的認為呢?」我顫抖著,雙手緊抓住自己的肩膀,試圖停止顫抖。
之後,我會想要知道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在他們之間發生的片刻,但現在,我只希望時間能倒轉,好讓我錯過火車,或是決定根本不要來,永遠不必發現真相。
我因為自己這樣希望而厭惡自己,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我渴望的竟然只是單純軟弱的無知。因為我不想做我必須做的──朝她推回去,懲罰她,傷她再傷她再傷她以為報復。我希望自己從來不曾知道真相。
「妳跟我走。」我說。
「噢,彼得。」她說:「謝謝你。」謝謝你──彷彿這已經結束了,彷彿我已經原諒她做了這件我還沒開始理解是什麼的事。
「現在。」我說。
「是。」她說:「當然。今晚。」
「現在。」
她鬆一口氣的表情開始改變。「這裡沒有後補演員。」她緩緩地說:「我得演完這齣戲。但之後──」
「把它取消。」我說。
「我不能這麼做。請你諒解。求求你。只要兩個小時就好。只要等到演出結束就好。等我。有個製作人要來,記得嗎,那個倫敦西區的傢伙。我們必須──」
「去妳的。」我說,走出房間。
我已經說了,現在──假如妳還相信有任何轉圜餘地,現在就立刻跟我走──而她卻說,有個製作人──
而我知道。我知道:如果她那時沒跟我走,如果她選擇留下來扮演她的角色,那麼,無論她最後以何種方式回來,都不會是永久的,也不會是為了我。
是有這樣的可能:所有需要在我們之間發生的一切,都在那裡發生了,在那個旅館房間裡。
要是我當初讓事情在那裡完結就好了。
「我想不通。」喬琪說:「她為什麼要退休?」 「他要求她退休。他是個男人,而且他是皇室成員。」皮爾斯說:「在攝政時期的英國,這是兩個非常好的理由。」 「但她很痛苦。她受不了待在家裡。」喬琪皺起眉頭:「『弗列多斯的新靴子的確棒透了!』」她模仿著。「她快活不下去了,她快瘋了。」 「你掌握得分毫不差。」皮爾斯說。 「相信我,我是過來人。」喬琪說:「都過了兩百年,情況還是一點都沒變。你想把每分每秒都花在孩子身上,同時在工作上擁有充實的人生。」 喬琪和皮爾斯花了整個下午排演有關布許莊園的場景。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