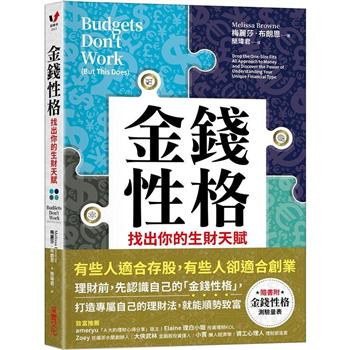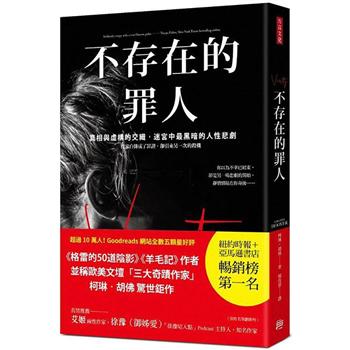總評
當代台灣青年的愛台方法論
林秀幸(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這個標題是我在太陽花運動一週年研討會時用來說明這個運動的日常伏流。換言之,我認為這一代年輕人「以農之名」回返「地方」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面向的表達,而是鑲嵌在台灣的歷史長流與地緣政治間的政治經濟行動。或許我們將這一波青年的「回」鄉「復」耕(其實包含多個面向)和一九九○年代台灣的社區運動做個比較,我們會比較清楚這波運動的特殊性。
九○年代的青年返鄉(大部份真的是回到他們的家鄉),是台灣社會本土化的一環。那是解嚴之後李登輝前總統當政,一個掙扎於中國認同和台灣認同的時代。前者透過國家機制製造的文本和其他作品,不斷地藉由文本的再增生而生產一個脫離於大部分人生活經驗的「真實」。包括教育內容,官方說法,文學,戲劇,藝術……甚至包括憲法。這樣的文本與日常經驗的脫離,令文本本身缺乏周遭生活的補給回饋與再創造,因此也令真誠的生命力難以注入文本得以擴大共感的範圍,終至淪為少數人的資源與資本。另一方面,由於「地方」生活無法協助建構中國認同,也在政府施政的藍圖中被忽略,甚至犧牲。九○年代本土化的意義即在於重新連接文本與生活的關係,那個時代重新被尋找的經驗包括地方文化、地方歷史,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文史工作。讓台灣的認同政治的拼圖從地方開始進行建構,換言之,這一階段的社區工作和文化歷史是鑲嵌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地方的生態環境與產業也開始被關注,前者獲得護溪護河與步道的修建,後者則是以觀光農業的方式被實踐。我們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認同政治是台灣v.s.中國的二元對立,這樣的二元性所推展出的回鄉內涵比較接近「愛護」鄉土母親的「疼惜」之心,不管是文史工作或是護溪護河。而彼時的觀光農業是以當時既存的務農者為對象來改變經營方向。因此地方社區的改變分作兩群人為實踐者。回鄉青年主要以文化歷史的追尋為任務,後者則限於原來在地務農者。
然而二○一○年之後的回鄉青年又是在什麼脈絡之下,來接近「地方」的呢?時至二○一○年,台灣已經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加上中國因素,製造了幾個明顯的困境:產銷鏈過長造成的食安危機,農業遭受進口糧食的威脅,工廠大舉西進中國與東南亞出現的失業率,紅色供應鏈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替代性以及產業升級的壓力。換言之,這一代青年是在全球化與地方(中間還穿越了國家)的辯證脈絡下,尋找一個立足點。因此一邊是全球化資本帶來的抽象性、不確定性與權力極度傾斜的遊戲規則,讓年輕人被排除在外或是被當作短暫的生產工具。表現在金融產業的買空賣空和少數壟斷,或是高度資本集中的高科技產業,或是隨時被併購的跨國公司。這樣的高度抽象和難以掌握的產業環境,等於是把年輕人提前排除在外的不對等遊戲。
另一邊則是非常具體而親近的地方空間。台灣的地方社群獲得二十年前社區營造的遺產,包括地方文史資料的累積,老街新生,觀光農業等。這樣的社區成果有它時代的局限性,嘎然停止在千篇一律的老街名產以及景觀工程。這一代的年輕人回到地方體驗農事和土地並非單純的「你農我農」,有他的全球化帶來的壓力和脈絡。因此這樣的回返地方社群有他潛在的深層因素和外在推力。分述如下:
親近性:借用Michael Herzfeld 的理論,親近性空間是相對於大結構的、物化的概念。這個大結構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全球化。二十年前的那一波運動是相對於錯置的國家認同,二十年後的今天,卻是對立於全球化難以制衡的權力。地方小尺度的空間,允許人與人親近的接觸,這樣的空間性質不受制於太嚴謹的規則,個人得以隨興、隨時間韻律和當場的人際動力進行非常個人的創作。這樣的創作摻在聊天的話語、手勢、語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隨著這樣的創作進行微妙的調整。這樣的可近性的門檻,免除資本的排除性,允諾了參與度高的創造性活動。而這樣的創造動力是反抗更大結構的權力的基礎。也是某種「創造性的抵抗」。
空間詩意:根據空間現象學家Gaston Bachlard所言,空間是內、外倒轉的。我們尋求多麼寬闊的外在,也會企圖挖掘多深刻的內在,來容納外在的景致。外在是無限的,內在也同樣是無限的。外在的無限表現在空間上的廣袤,內在的無限體現在微細與深沈的刻畫。一如我們內心對所有事物的劃分:廣度與深度。前者講求範圍的擴大,後者講求感受的細緻。兩者是互為裏外,互相調配的。過多的外在會使心靈枯竭,過多的內在也會造成缺乏動力。我們不斷地變換內與外,以避免僵化。所謂的僵化不是指範圍的限定,無限制地擴展範圍也會造成認識論的僵化與停滯。心靈的活躍需要靈活調配內與外的認識論。所謂的詩意指的也就是這樣的自由穿梭內、外的能力與再創造。這樣的詩意不受限於文學的詩,任何不同認識論與空間的自由調配都是詩意的展現,可以展現在閒聊、文學或行動。而詩意並非無關痛癢的創作形式,她可以對既有的結構產生撞擊與更動,改變結構,也改變人們認知事物的方式與觀看的角度。因此詩意即政治,也是政治的前身。
回過頭來看這一代年輕人回返地方,貼身於土地、投身于農事。這是對立於全球化的廣袤所創生出的對內邊深沈的認識論的追求。一種親近的、體感的的空間美學。這樣的空間感可以激發出一種揉摻著同理和對立的互動方式,就在這樣的拿捏當中進行創造。也就是這樣的鬆散而允許相對自由的空間可以培養個人的能動性和對更大層次的權力的抵抗。
因此,回返地方的親土近農,不是一種自我的退縮,也不是挫敗的求援。它更是一種創造性,一種對全球化的抽象與暴力的反動,和太陽花運動的空間佔領有著近緣的關聯,也是前者的日常表徵,互為完整化政治與詩意的表裏互動。年輕人不是浪漫的懷舊和耽溺,他們不僅體會土地,浸身農事,他們也同時關切組織檢討政策。並在這樣的近身空間裡感受地方人的行動力對空間與政治的碰撞與改造。這是一種對自我能動性的鼓舞與催生。在大結構的空間裏,譬如全球尺度,個人的存在感與動力幾乎被結構所限定,對自由空間的限縮,皆造成某種抑鬱與無力。回到地方(不見得是家鄉),是對自由性較大,對個人創造性較為友善的環境的追求。而這樣的創造性不限於地方尺度,也對國家制度探索,在兩種空間認識論之中自由互動與創造出體現個人性的一種「論述」和「行動」。
這樣的創造性不是打掉重練,而是在地方的關係中體會,並在即有的脈絡中匍伏前進,進行修補中的創造。入身其中的介入,必須不斷地把既有關係當作行動的脈絡,在某種紋理中進行創造。因此是一種浸潤的創新與脈絡的挪動。年輕人在其中感受自我的動力之外也發展了自我存在的各種面向:感知的、情感的、理性的和行動的。
這是一種新的,切合時代的「生產」觀,帶著空間與美學,詩意與政治的面向與動力。台灣,作為國家,必須在此時作為中介,調節地方與全球化,庇蔭地方的空間價值,也必須有能力加持個人往全球探索不同的動力。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用行動開啟了這個方法論的想像,國家必須不負期待幫助開展這個新政治的框架,提供更有利於自由創造的空間。
是的,他們以農展開認同之旅,這樣的行跡動力卻不限於農,而是一個更為深沈與廣闊的空間政治的想像與開端。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農人教我們的事:2015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230 |
Others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台灣研究 |
$ 282 |
Social Science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農人教我們的事:2015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
作者簡介:
台灣農村陣線除了積極的投入各樣農業議題的探索,也展開了與國際連結的活動,並且也積極的引領年輕學子投入農村工作。台灣的各地農地徵收自救會,農村陣線都盼望可以建立聯絡窗口,隨時給於法律、學術、媒體...上的協助,我們也嘗試參與農民之路的活動,學習各國的農業運動經驗與農法,並且積極的舉辦「夏耘」活動,讓更多的年輕學子進入農村,作田野工作,關心農村。
台灣農村陣線期望以更寬廣的視野,更深入的在地了解,將更多的知識、科技與人力,謙卑的參與農村、農業,使台灣農村可以走出內部殖民的地位,同時也要捍衛台灣的糧食主權與環境永續。
TOP
章節試閱
總評
當代台灣青年的愛台方法論
林秀幸(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這個標題是我在太陽花運動一週年研討會時用來說明這個運動的日常伏流。換言之,我認為這一代年輕人「以農之名」回返「地方」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面向的表達,而是鑲嵌在台灣的歷史長流與地緣政治間的政治經濟行動。或許我們將這一波青年的「回」鄉「復」耕(其實包含多個面向)和一九九○年代台灣的社區運動做個比較,我們會比較清楚這波運動的特殊性。
九○年代的青年返鄉(大部份真的是回到他們的家鄉),是台灣社會本土化的一環。那是解嚴之...
當代台灣青年的愛台方法論
林秀幸(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這個標題是我在太陽花運動一週年研討會時用來說明這個運動的日常伏流。換言之,我認為這一代年輕人「以農之名」回返「地方」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面向的表達,而是鑲嵌在台灣的歷史長流與地緣政治間的政治經濟行動。或許我們將這一波青年的「回」鄉「復」耕(其實包含多個面向)和一九九○年代台灣的社區運動做個比較,我們會比較清楚這波運動的特殊性。
九○年代的青年返鄉(大部份真的是回到他們的家鄉),是台灣社會本土化的一環。那是解嚴之...
»看全部
TOP
目錄
4 導讀
下個階段的農陣……/吳音寧
9 關於夏耘
10 屏東潮州東港溪
【訪調】WATER LEGEND ——翻轉東港溪豬屎命運
【評論】台灣河流的故事/江昺崙
32 高雄桃源勤和部落
【訪調】風災過後,我們的選擇?——桃源勤和部落的生活一隅
【評論】桃源香梅,香自何處來?——訪調作為一個說故事的實踐/施聖文
60 高雄美濃
【訪調】「很慢的」生活百態——關於美濃市場的二三事
【評論】「有質、有量、有多聞」的期許/董時叡
74 台南東山
【訪調】龍眼的故事——記...
下個階段的農陣……/吳音寧
9 關於夏耘
10 屏東潮州東港溪
【訪調】WATER LEGEND ——翻轉東港溪豬屎命運
【評論】台灣河流的故事/江昺崙
32 高雄桃源勤和部落
【訪調】風災過後,我們的選擇?——桃源勤和部落的生活一隅
【評論】桃源香梅,香自何處來?——訪調作為一個說故事的實踐/施聖文
60 高雄美濃
【訪調】「很慢的」生活百態——關於美濃市場的二三事
【評論】「有質、有量、有多聞」的期許/董時叡
74 台南東山
【訪調】龍眼的故事——記...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吳音寧等作
- 出版社: 台灣農村陣線 出版日期:2016-06-01 ISBN/ISSN:97898687363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商品尺寸:長:230mm \ 寬:170mm \ 高:15mm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台灣研究
體內針灸:第一冊(國際英文版)
幸齡人生的80個樂活慢老生活提案:「80歲之壁」實踐篇!活出自在、康養又長壽的黃金人生
2024年臺灣IT Spending 調查:醫療業
今天遇見第三人生:長照醫師在診療時記錄生老病死每一刻,讓你學會照護長輩、從容迎接晚年生活(附:選擇長照機構須知)
青光眼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眼科名醫教你有效降眼壓,99%預防青光眼失明
圖解人體病理學:揭開身體異常與疾病成因的真相
眼科及視光儀器學【含彩圖】
幸孕而生:試管嬰兒全程指南,寫給每位在備孕路上奮戰的妳與你
中醫小兒體質學,體質辨識與育兒調理之道:九大偏頗體質×八大易感病徵×四法對症調理……中醫理論與現代兒科研究,打造專屬孩子的體質辨識與調養指南
學習植物療法的50堂課:從文化、歷史、園藝到香草精油,探究如何用植物治癒我們的身心
幸齡人生的80個樂活慢老生活提案:「80歲之壁」實踐篇!活出自在、康養又長壽的黃金人生
2024年臺灣IT Spending 調查:醫療業
今天遇見第三人生:長照醫師在診療時記錄生老病死每一刻,讓你學會照護長輩、從容迎接晚年生活(附:選擇長照機構須知)
青光眼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眼科名醫教你有效降眼壓,99%預防青光眼失明
圖解人體病理學:揭開身體異常與疾病成因的真相
眼科及視光儀器學【含彩圖】
幸孕而生:試管嬰兒全程指南,寫給每位在備孕路上奮戰的妳與你
中醫小兒體質學,體質辨識與育兒調理之道:九大偏頗體質×八大易感病徵×四法對症調理……中醫理論與現代兒科研究,打造專屬孩子的體質辨識與調養指南
學習植物療法的50堂課:從文化、歷史、園藝到香草精油,探究如何用植物治癒我們的身心
|